
在我小时候,有一句话很流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很契合当时年轻人想追求个性自我,“潇洒走一回”的心态,因而许多人把它抄在笔记本上,极有可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也最烂大街的)座右铭。
等过了些年,我发现,虽然更年轻的一代同样追求个性,但氛围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句格言也演化出了戏谑与霸气夹杂的新版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种赢家通吃的气概不仅是一种开挂人生的自我幻想,而且常常也用在对国家的认知上,所谓“中必最赢”。
现在,整个社会的气氛看来再一次发生转变,
这一次的宣言似乎是:“走自己的路,不让别人说话!”
——或者,就像这些年来官方发言中更强有力表达的,是“不容他人说三道四”,也因此,“妄议”一词俨然成了近些年来相当流行的外交措辞。
我之所以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近期以来举报文化文化盛行,越来越多借助权力去打压自己看不惯的言论,甚至连
科普团队“回形针”也被指控“辱华”
,不断设下敏感的高压电网,网络的言论生态正变得日益单一化。
不仅如此,过去的一个月可以说见证了国家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深厚基底。“韬光养晦”已成往事,
现在的中国像是一个“杠精国家”,在“不吹就是黑”的心态之下,以零容忍的姿态和旺盛的精力与所有人对战
。如果说一百年前美国初兴时还能“手持大棒,温柔说话”,那么现在中国好像在拿到大棒后,恨不得像打地鼠一样逐个敲打此起彼伏的异议。这不仅表现为许多民众对海外疫情的幸灾乐祸、对国内外批评声音的攻击性回应(所谓“战狼”),还有一种对不同声音日益不能容忍的焦躁情绪。

周围的很多朋友都感叹现在环境“倒退”了,这或许是基于一种直观的感受,从舆论尺度的收紧而言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从另一面来说,
那种“从前的好时光”,我也怀疑只是在回溯时产生的一个幻象
。
那时确实会宽松一点,但那是因为当时的管理本身还比较粗放,在网络言论与现在相比也更像是某种小圈子的精英活动。也许真相是:十年前的中国人不见得就更开放宽容,而是那时好多人还只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与其说是“倒退”,不如说是“膨胀”,是一种伴随着集体强盛幻觉的权力欲。融入整个整体,可以带来归属感和力量感
。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经典叙述中,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e曾说:“……从表面上看,战斗的是公鸡,事实上是男人。”人们斗鸡不但赌钱,而且赌他们的自尊、沉着和男性气概。在16世纪,当亚齐苏丹们最喜爱的斗鸡被斗败时,他们就暴跳如雷,部分原因在于“斗鸡斗败就是对国王本人的威胁或侮辱”(《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一卷)。这是一种社会群体之间敌意的戏剧化表现,在这个残酷的舞台上,被人击垮是一件可怕的事;而当你与这个集体“合体”时,就把它的成败当成了自己的成败。
有些人觉得这种国族情绪幼稚如巨婴,意在指出其心智不成熟、以自我为中心打压别人;但民族主义者其实也反过来指责对方是“以自私为乐趣、以利己为荣”,是个人主义飞速膨胀的产物。在我看来,
其真正的问题是“尚情而无我”,正是与对象“合体”的产物,所谓“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粉圈文化产生了潜在的相通之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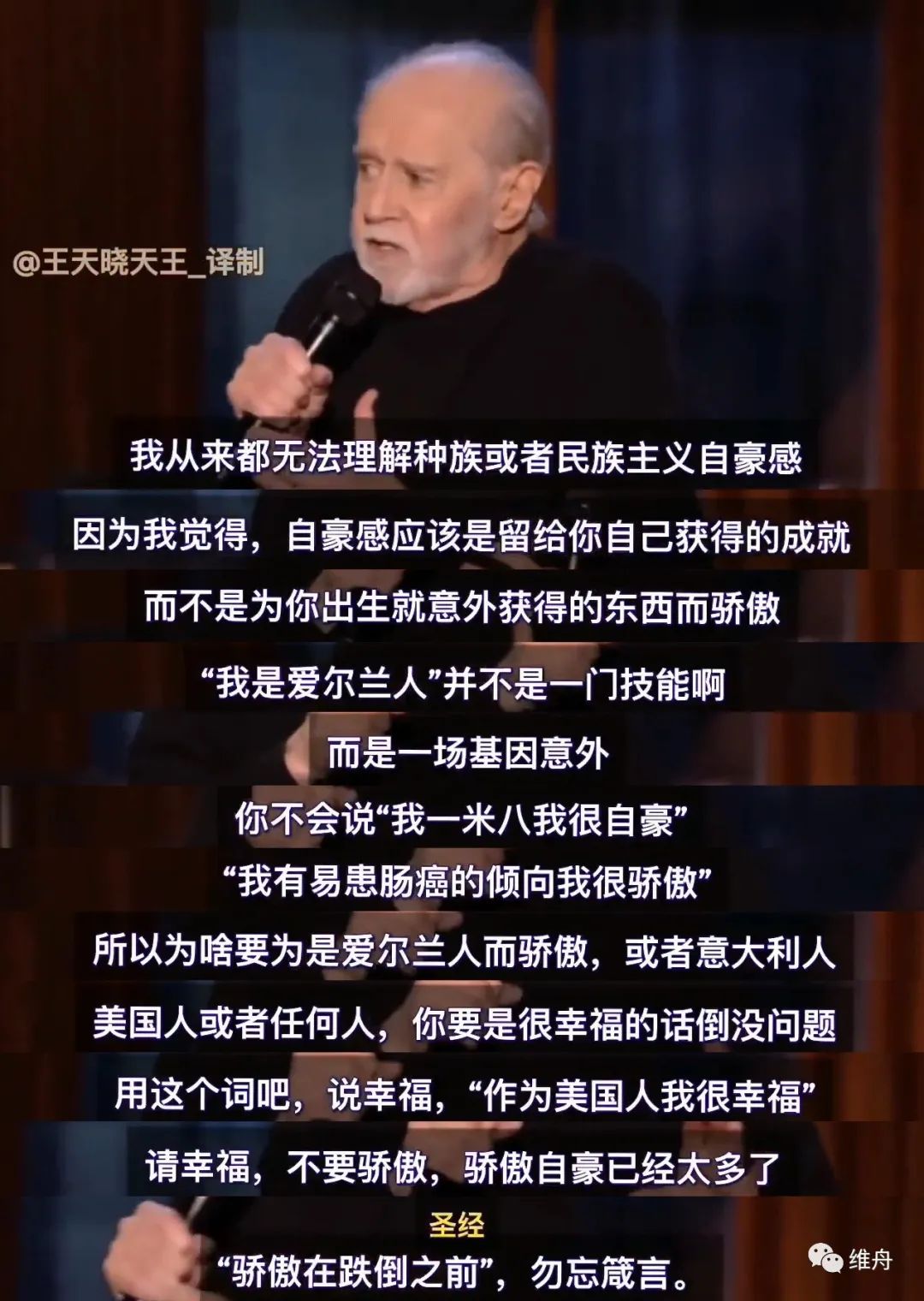
中国社会历来有一种特殊的话语,那就是:没有“我们”,就没有“我”,所谓“没有国哪有家”
。这就是许多人自觉维护所在团体、指责那些脱嵌出去的个人“自私”的立足点,也是为什么会有人骂那些加入外籍的国人“他怎么忘了,如果没有中国的平台,他什么也不是”。这类人也不是没有自我,只是觉得要先“顾全大局”,如果“大局”都没了,何来“自我”?
这会让人产生一种特殊的移情能力,那就是
处处都要站在“大局”的立场上想一想
——从父母的角度出发想想持家有多难,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考虑考虑。甚至当你批评一个网站时,都有人说:如果你自己去注册一个网站,知道现在经营一个网站有多难,就不会这么说了。尽管很多人嘲讽说这就像“骂饭店菜不好,还要先自己开饭店”,但事实上,这么说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才是最“深明大义”的。
这个论述逻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仍未完全脱离原先的传统基底:脱嵌出去的个体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类,许多人坚信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只有作为组织的一员才能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哪怕是私利,也只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