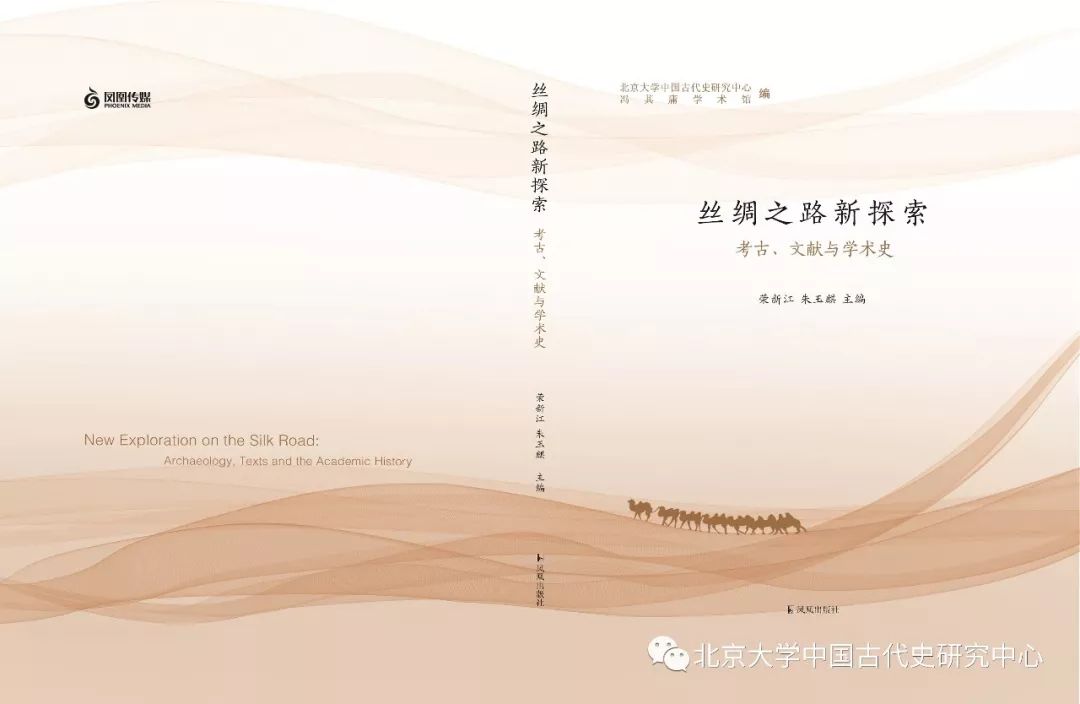
丝绸之路新探索:
考古、文献与学术史
荣新江、朱玉麒 主编
凤凰出版社 2019年11月
序
言
本书是
2018
年
10
月
13-15
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冯其庸学术馆共同举办“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的论文合集。
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渊源悠久。早在京师大学堂创建伊始,经由中国西北与东南海疆的丝绸之路,就备受关注。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著述《帕米尔图说》等,成为认识丝绸之路和中俄交涉的重要依据;总教习张亨嘉著名的政论《奏请回銮折》等,深忧边疆危机、主张海陆并防。这些都为早年北京大学面向全球的办学思路带来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民国以来,北京大学于1925年派遣陈万里赴甘肃考察、1927年参与组建西北科学考查团、1941年派出向达参与并领队中研院西北史地考查团等,开创了丝路实地考察与研究并重的学术新征程。这些无疑也折射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是科学与民主的光辉在丝绸之路上的具体表现。特别是
1927
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呼吁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联合从事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首批
10
位中方团员,北京大学参加者多达
8
人。这个综合的考查团,在丝绸之路的求索中,为我们奠定了平等合作、走向世界的重要经验,也为今天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的多学科团队在丝绸之路的考察与研究上越走越远,正在谱写着更为绚丽的新篇章。
2018
年是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在
10
月间以“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的名义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的承担,希望继承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领域、在丝绸之路的多个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这次论坛在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举办,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学术活动的一个尝试。在包孕吴越的太湖之滨,无锡是江南丝绸重要的产地,很早就参与了丝绸之路的人类文明交流。生长于斯的冯其庸先生,毕生崇尚玄奘执着求法的探知精神,他对丝绸之路的竭诚弘扬与研究成果,是留给家乡人民的无尽财富。他曾经与季羡林先生联袂上书,促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为新时期中国学者预流丝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北京大学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些学者,也曾经跟随冯其庸先生重走玄奘之路。斯人已逝而光辉永存。冯其庸学术馆承办此次高峰论坛,再次实现了冯其庸先生为丝路研究作推手的奉献精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学术馆的联手,正如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纽带一样,我们也在这一文明的研究之路上,承担了学术纽带的功能。
《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正是此次论坛的结集,其中部分论文在出版时经过修改、调整,与会议发言稿有所差异;个别文章因为作者另有安排而未能收入集中,读者可以在书后附录的会议《综述》中了解这些论文的内容。我们将收入论集的文章大体分成三组,分别从考古、文献和学术史方面来探讨丝绸之路,各位专家学者奉献给读者首次发表的论文,是对丝绸之路一些问题的新探索。我们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者以及他们提供的精彩论文,感谢凤凰出版社精心编辑这部论集。
我们也衷心期望在丝绸之路探索的众多成果中,这本论集能够展现它自身的价值。
2018
年
10
月
13
—
15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冯其庸学术馆共同举办的“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在江苏省无锡市冯其庸学术馆隆重召开。冯其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书画家,一生与西域结缘,为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次会议在冯其庸学术馆召开,也是对冯其庸先生学术精神与业绩的纪念。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的主题演讲《以真性情抒写丝路之魂——重读冯其庸先生〈瀚海劫尘•自叙〉感言》,回顾了冯先生的西域诗词、摄影、绘画作品,指出这些作品是以追梦之心和由衷热爱大西北的真性情抒写丝路之魂的典范之作,同时将冯先生的“丝路之魂”概括为“交流互鉴、融汇创新”。
会议期间,国内外
30
余位学者围绕着丝绸之路文明的主题,就历史、语言、考古、文学等多领域展开了充分讨论。
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外语言专家,展示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于阗文、粟特文、梵文、藏文等多个门类。其中,新疆地区新出土丝绸之路胡语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尤其引人注目。段晴与侯世新、李达等先生合著的《于阗伏阇雄时代两件契约》,即刊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两件于阗语案牍,在于阗语词语解释及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同时为研究于阗王国社会体系的运营模式提供了新材料。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范晶晶《吐峪沟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入金刚界曼荼罗之梵语真言解析》一文,刊布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最新出土的粟特语梵语佛经的梵语部分,将其比定为《金刚顶经》(《真实摄经》)中入金刚界曼荼罗的仪轨,进而探讨了翻译者不空在河西的译经、传法活动。粟特语夹写梵语的文献数量极少,新文书的刊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密宗金刚界在西域地区的流传以及汉地佛教回流西域的情况。段晴教授对这件写经的整体情况,特别是粟特语部分做了补充说明。与会者对此做了热烈的讨论。
梵、藏文献的对勘是研究佛经的重要途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欧珠次仁合写的《〈海龙王所问经〉研究》,利用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写本、新比定的敦煌藏文写本与传世的汉、藏译本进行比较研究,阐释了《海龙王所问经》的相关问题,强调了梵文本的价值。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普仓《
〈
宝鬘论颂〉梵文写本及藏译本谱系探究》,介绍了最近在西藏发现的《宝鬘论颂》梵文写本,并与藏文本、梵文注释本进行比较,讨论了为藏传佛教诸宗尤其是格鲁派所重视的《宝鬘论颂》的译本谱系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王继红《达摩笈多〈金刚经〉译本的梵汉双语字书性质》,比照西域出土梵汉双语文献的特点,对《金刚经》笈多译本的性质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其并非是以阅读为目的的译经,实质上是一部需要与梵文原典配合使用的对译词表。对此,高田时雄教授认为也不能完全否定前人提出的译语未完成说,认为两说均可以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李灿《鸠摩罗什失传〈贤劫经〉译本的新发现——比定自书道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吐鲁番藏品》,则是通过藏汉平行文本、语言等证据,从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吐鲁番早期写经中比定出两件残片,推定其应是早已佚失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的珍贵遗存。与会者就此问题讨论了早期汉译本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问题。
巴利文佛典的相关研究则展现了佛经的南传路径。泰国法胜大学(
Dhammachai Institute
)萧贞贞(
Wilaiporn Sucharitthammakul
)的论文“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textual criticism to a comparison of the Pāli Dīgha-Nikāya and Chinese Dīrgha-āgama in Mah
ā
nidana sutta
”(《运用文本批评的原则比较巴利语〈长部〉与汉译〈长阿含经〉中的〈大缘经〉》),对早期佛教经典《大缘经》的巴利文《长部》本与汉译《长阿含经》本进行了细致的比勘,认为二者的相似性达到
80%
以上,但很多证据还是显示巴利文本比汉译本更准确,或者说更加可靠。法胜大学文·憍陈如称法师(
Ven. Kondannakitti
)的论文“
Selection of Burmese Pali Manuscripts
”(《缅甸巴利语写本甄择》),介绍了法胜巴利三藏项目(
DTP
)的基本情况,以及该项目选用缅甸巴利文佛经写本的问题。
近年来福建霞浦文书的发现为摩尼教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从死海古卷到明教文书——摩尼教“十天王”与“四天王”综考》,从霞浦文书中所见《赞天王》入手,认为大力士故事是随着宗教文明向东输入而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从死海古卷中阿拉姆文《巨人书》残片到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大力士经》,再到霞浦文书、日藏摩尼教绘画、屏南文书,展现出这一故事的传播路径。台湾铭传大学应用中国文学系汪娟《从敦煌礼忏到霞浦科册〈摩尼光佛〉的仪节分析》,通过参照敦煌礼忏乃至后世佛教的仪节,对霞浦科册《摩尼光佛》的仪节进行了分析,阐明了《摩尼光佛》与佛教礼忏之间的交涉问题。
丝绸之路是连通欧亚大陆的桥梁,关于丝绸之路交通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唐五代敦煌的交通问题》,考证了沙州通往邻州的道路,尤其是沙州通伊州之路的变迁,并考察了交通道路上的管理体制以及服役民众的个人负担,对唐代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地位,做出了新的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子凡《丝绸之路上的弓月城与弓月道》,通过对进入伊犁的古代交通路线和古代遗址的考查,认为唐代弓月城应在今伊犁地区伊宁县附近的吐鲁番于孜古城,确定了翻越天山到达弓月城的交通路线,认为唐以后伊犁河流域中心城市从弓月城转移到阿力麻里城与丝绸之路变迁有着直接关系,进而探讨了丝路变迁对于古代城市兴衰的影响。
除了通达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通往南海与东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同样是古代交通的重要道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姚崇新《广州光孝寺早期沿革与驻锡外国高僧事迹考略——兼论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以广州乃至华南地区的一座重要寺院——光孝寺为核心,梳理了该寺的早期历史沿革,考证了曾驻锡于光孝寺的外国高僧以及走海道西行求法且曾驻锡光孝寺的中国僧人的情况,进而揭示了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旅顺博物馆徐媛媛《唐通渤海之路——以唐鸿胪井刻石为中心》,介绍了位于辽宁旅顺的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信息、被运往日本的具体过程以及其历史意义,进而考证了唐代通往渤海国的交通路线。
清代西北史地研究方面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祥麟及其散藏海内外的西北行程记》,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京都至伊吾庐行程日记》入手,考证该日记作者为祥麟,并梳理了其散藏在国内外的《皇华劳瘁》、《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祥麟日记》等著作,揭示了这些稿本对于清代西北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吴华峰《清代西域题壁诗研究》,指出清朝平定西域之后大量文人亲历斯地,沿途赋诗题壁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真实自然的创作状态为今人再现了清代西域诗的创作现场,并提供了了解彼时出关文人心态律动的途径。
关于敦煌西域出土汉文典籍以及相关文本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历来是中古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余欣《符应图书的知识谱系——敦煌文献与日本写本的综合考察》,结合史志著录与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天地瑞祥志》写本,兼及敦煌本《瑞应图》和《白泽精怪图》,讨论了汉唐灵瑞符应图书的知识社会史,从知识内核和文本语境出发,重绘了中古符应图书的成立过程与知识—信仰—制度结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西域记〉泛海东瀛考——以最澄〈显戒论〉为例》,从最澄《显戒论》中抄写《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入手,结合日本古文书有关记录,考证了日本引入并传承《大唐西域记》相关知识的历史过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唐写本〈列子·杨朱〉(张湛注)的文献价值——从旅顺博物馆藏残片谈起》,介绍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新比定出的一件《列子·杨朱》篇张湛注残片,并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列子·杨朱》篇残片进行了整理缀合,指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列子·杨朱》张湛注展现了唐代写本的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丝绸之路沿线近年来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及调查发现,新近考古成果的介绍也成为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高原丝路吉隆道的考古发现》,结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出使天竺铭》以及调查所见吐蕃碑铭遗迹,证明吉隆道是唐朝经吐蕃通往印度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路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
2018
年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考古新发现》,揭示了丝路北道重镇北庭故城遗址“两套四重六块”的布局形态,介绍了今年在内城北门和西门、外城北门和南门四个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外城南门附近佛寺遗址进行的勘探工作,以及出土文物情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胡兴军《安西四镇之于阗镇防体系考》,介绍了该所对麻札塔格烽火台及戍堡、安迪尔古城等和田地区现存烽火台与城堡的考古调查情况,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唐代安西四镇中于阗地区镇防体系的具体分布和路线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证。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海龙《吐峪沟新出汉文佛典过眼录》,介绍了
2016
、
2017
年间吐峪沟发掘出土的
14
件佛经残片,并对其中所见高夫人写经题记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考证。
丝绸之路促成了各个文明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示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张德芳《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的实物为中心》,介绍了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居延遗址和悬泉置遗址三个遗址出土的近
2000
件两汉丝织品的信息,并结合汉代简牍中所见丝、帛、缣、练等相关记载,证明两汉时期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地段的河西走廊确实拥有相当数量的丝织品,它们对当时河西走廊的社会生活以及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曾起到过重大作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指出马可·波罗记载中亚巴达赫尚出产的名为巴剌思(
balasci
)的红宝石,在波斯、阿拉伯语文献中称为
la‘l
(或
lāl
),实际上是一种红色尖晶石(
spinel
),受到西亚、中亚人民的广泛喜爱,而且自元代起这类红宝石就已进入中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吐峪沟所见纳骨器的宗教属性》,讨论了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玛扎古墓区出土的两具陶棺的宗教属性,对于以往将纳骨器看作祆教的性质进行了质疑,认为使用纳骨器藏纳余骸或余灰,应是中亚不同信仰者在丧葬中所用葬具之一;祆教徒使用纳骨器更可能是缘于中亚佛教之影响,而中亚佛教丧葬中使用纳骨器恐亦是受到本土葬俗影响所致,是丧葬中的内亚性对外来宗教的渗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楠《东魏北齐河神王之溯源》,对比了北凉石塔、如马德惠塔和沙山塔、高善穆塔以及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索阿俊塔等石刻的河神王图像,指出东魏北齐的河神王形象当来自中亚,并可上溯到斯基泰文明,他们随粟特人东迁时来到中原。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神王形象的热烈讨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毛秋瑾《丝绸之路汉文书法研究综述》,对丝绸之路汉文书法的文字资料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梳理,指出相关研究应着眼于不同材质的书写载体所呈现的书体与书风,以及丝绸之路书法传播和接受的途径。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探险活动获得了大量文物和文献材料,极大地推动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开展。如何认识丝绸之路探险史也成为了学者们重点讨论的话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丝路考古探险与丝路研究》,通过对从
19
世纪末叶以来直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丝绸、钱币、纸张、佛教等文物的分析,指出只有到了西域地区考古探险的时代,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才真正得到证明,而各国探险队的经历与斯文赫定《丝绸之路》等著作对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田时雄《内藤文库所发现之橘瑞超〈新疆发掘记〉(橘瑞超第三回考察报告)》,介绍了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所保存的橘瑞超《新疆发掘记》,指出橘瑞超此行的记录此前并未公开发表过,其第三回考察报告的发现对于大谷探险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冀青《法国碑铭学院保宁中亚考察队研究》,介绍了法国探险家夏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