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的继母,孤零零的外婆船
文 |
李德帅
继 母
清明时节,没法不想起继母。
继母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体型上,都算得上是个彪悍的女人。
初次见她时,我还是个少不经事的孩子。而她,对我表现更多的也是慈爱与温柔。虽然后来的四年我自认为过得有些狼狈,但翻看七岁时依偎在她身旁的照片,似乎我们当时亲密得更像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子。

7岁的李德帅与继母。
那时继母有两个自己的孩子,一个是比我大三岁的姐姐,一个是小我一岁的妹妹,同时,我还有个年长三岁的亲生哥哥。两个姐妹和我们相处得也都还好,直到现在,她们依然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可能是因为有自己孩子的缘故,亦或是我和哥哥做的不够好,继母表现的似乎不那么喜欢我们,有些时候甚至很粗鲁,即便是在父亲面前。
很多年以后,当年迈的父亲回忆起来,证实了当初她的行为的确“有失风度”。而作为父亲,他也为没能过多的给我们兄弟俩个提供更多庇护而愧疚,导致在继母去世后很多年,他宁愿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带抚养我们四个孩子,也不愿意再娶。
要说继母“虐待”我和哥哥,似乎真的是有些冤枉她,虽然在很多外人看来是这样的。她只是在有些时候说话的语气很凶,会让我和哥哥干更多的体力活,并且限制我们外出玩耍。当初家里的经济状况很糟,淘气的男孩子难免会弄坏鞋子和衣服,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让家庭经济雪上加霜。
在物质生活上,我家确实不怎么丰富,但和八九十年代的很多山区农村家庭相比,也没什么两样。她在物质的分配上,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公平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和她一起生活的四年间,我们吃的饱,穿的暖。
作为一个纯粹的农村妇女,继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照顾孩子和地里的庄稼上,当然,也包括喂养家畜。
农民把猪和鸡这些家畜看的和家人差不多,很多时候,家畜死了,主妇们会难过好几天。记得有一年,我家的猪刚长到五六十斤的时候便病死了,继母竟然伤心的哭了起来,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那么强势的女人哭泣。现在回想起来,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时候她比那时更像个女人。
继母性格耿直,脾气暴躁,经常和父亲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当然,身体相对弱小的父亲很少在争斗中占到便宜,因为继母身体粗壮得像是中国排球队的“铁榔头”。有时父亲只能靠着掀桌子、摔碗来出气。但仔细分析起来,每次吵架似乎都和父亲酗酒有关,这也怨不得继母,因为即使在她去世后的很多年,父亲
酗酒
依然是家庭争吵的主要原因。
他们吵架的后果就是吓坏了我们四个都在上小学的孩子,这可能是我直到她去世很多年还不原谅她的原因之一。
继母去世在一个夏季的周末。那天是如此的闷热,以至于连草丛中的虫子都比平时叫得更加撕心裂肺。
那天本来我们一家六口都应该在玉米地里除草、施肥,前一夜父亲就答应了继母,当天不去参加族里一位长辈的寿辰。继母知道,父亲去了必会喝得酩酊大醉,喝醉了的父亲不仅絮絮叨叨,伤身误事,还容易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但后来,作为家族一代人中的大哥,父亲还是被长辈的儿子从地里强行拖去了宴席。
从他走的那一刻起,气氛便骤然紧张起来,连那些撕心裂肺的虫叫声都停止了,似乎都在草丛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偷看即将要发生什么。继母汗水不住地从她的额头滚落,她一声不吭,甩开锄头迈开大步往村子的方向走去,如同革命烈士一样似乎要慷慨赴义。
作为孩子,我们却很开心,因为不用干活,又可以回去玩耍了。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竟是最后一次看到继母,那天也是和她相处的最后一日。继母先我们几分钟回到家,反锁了门,只留给姐姐几句话,便把一瓶农药如同交杯酒一样毫无犹豫地一饮而尽。接下来几天,便是父亲和几个孩子的哭泣,还有满院子凭吊的人群和漫天飞舞的纸钱。
继母的离世是个解脱,尤其对她自己。她一定是太难过,太无奈,以至于刚烈固执的性格再也无法控制压抑六年的不满与悲愤,如同火山喷发一样肆虐地倾泻出来。她觉得,唯有一死才能得到解脱,即便她要留下两个未成年的亲生女儿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家乡的习俗,横死的女人不能葬入祖坟。于是,她便被独自葬在了一座朝向东方并且满是板栗树的山坡上,像是被刻意冷落,那么孤单。
如今,继母离世已有二十一年,我也有好多年没有回家给她上坟,她一定还孤零零地躺在那,坟头上长满了草,甚至连通向坟地的路都被杂乱的植物霸占了。
还好,东出的太阳会先把阳光洒在她的坟头上,也许会让她内心有些许平复,毕竟,那边没有再让她伤心的人。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继母,你在九泉之下,应该也已经安宁了。
外婆船
外婆家坐落在村尾的一个黄土坡上,三间青瓦房前是一个八九十平方米的院子,院子的尽头是一棵梨树,如果前几年不被砍掉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很大了。
因为母亲生病,自从出生四十天后,我便被父亲抱到外婆家,在外婆的呵护下长大。
外婆有严重的肺病,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不停地咳嗽,稍一活动便会喘得厉害。每天晚上,她都是披着衣服靠着窗台,倚在被子上半坐着打盹,隔几分钟便要吐痰,一夜过来,会吐满整个痰盂。
“外婆,你怎么总咳嗽呀?”那时,我常常这么问。
“因为外婆生病了呀。”她总是笑着回答。
“可以去看医生啊!”
“医生治不好外婆的病。”外婆边回答边咳嗽。
“长大后,我要当医生,治好外婆的病!”我信誓旦旦地说。
“好——好——好,外婆一定等着。要是你妈妈有这个福气就好了。”
“妈妈是谁呀?”这时,外婆哽咽了,不住地抹泪。
“外婆,你又哭啦,很疼吗?”我用小手试着帮她擦干泪水。
“不疼,不疼了。”外婆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轻轻左右摇晃着,哼起了童谣。正当我要甜甜地睡去,几滴热泪掉到了我的脸上,微微地睁开眼睛,我看到了外婆老泪纵横的脸。我想,她一定是想起那个叫“妈妈”的人了。

与外婆一起拍的全家福。
记不清那是哪一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院子里来了好多陌生人。虽是晴天,但阳光似乎舍不得给人们半点温暖。这些人或是戴着棉手套,或是把手互相交叉着伸进袖口里,不停跺着脚,嘴和鼻孔里间断地冒着水气。有几个不怕冷的人,硬是把粗糙皲裂的手放在外面,蹲在西墙根的阳光下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屋子里,我和表妹依偎在外婆身旁,用手指在窗子上的冰花上描绘出各种图案。外婆不住地咳嗽,时不时地唠叨着把我们的小手揣在怀里捂暖,我们却又迫不及待地从她怀里挣脱出来,趴在窗前用口哈出热气,透过融化的冰花,仔细观察着外面那些人的一举一动。
外面也许是过于寒冷,一个抽旱烟的人走进屋子,和外公说了几句话,便从柴房里拎了捆玉米秸秆扔到院子里点燃。那些人立马凑了过去,直到火逐渐烧旺,他们才把手从袖口里抽出来,说笑着,开始干活。听外公说,他们是木匠。后来,我还央求外公让他们给我做了把木枪。
木匠们迅速把牛棚里储存了几年的松木板一块块搬出来,斜靠在矮墙上。有个年龄悄长的人相面似地打量着每块木板,时不时地猫下腰用手中的卷尺测量着,再反复地用被他夹在耳朵上的铅笔标记。最后,其他人迅速地把他标记好的木板用刨子刨平,切割,弄的院子里一片狼藉,到处是木屑,就像下了雪。
我很好奇地看着这群有趣的人。很长时间才想起来问外婆:
“他们在干什么?”
“她们在做船。”外婆微笑着说。
“船是什么?”我似乎要问到底。
“等到夏天下过雨,河道涨满水,船可以浮在上面,带你去想去的地方。”
“那外婆,把它给我吧,我要坐船。”我用手指指着还是一堆木材的船。
“这是外婆的船,外婆走路喘,得坐船。”外婆淡淡地说。
“我也要坐船,外婆,让我也坐船好不好?”我用力摇晃着外婆的手,却让她又开始频繁地咳嗽起来,咳出很多痰。
看着外婆出了一身虚汗,我就不再央求她了,转过身来继续观察外面:看到外公在给他们发烟,而且是很少见人抽的烟卷。很多人嘴里叼了一支,耳朵再夹上一支。我真佩服那些人,耳朵似乎什么都能夹得住。后来长大了听舅舅们说,我那几天,也学着把铅笔夹到耳朵上,还经常捡他们抽剩下的烟头,学着他们抽烟,因此还被外公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这是外婆的船,外婆走路喘,得坐船。”
做好船的第二年,夏天里没有多少雨水,河道大都也是干涸的,只在下游的河坝处零星分布着几个水坑,还被几条草鱼霸占了。我猜这点水应该浮不起外婆的大船,况且还没到盛夏,就连这仅存的几个水坑也不知去向了。于是,我就不再惦记坐船的事。而那些大人们,似乎早就忘了家里去年还做了一条船。
家乡的秋天来的早,几场霜下来,院子里的梨树叶就掉光了,只剩下树梢上几个冻僵的果实。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会飞来几只“不速之客”,叽叽喳喳地落在树梢上贪婪地啄食。偶尔我因顽皮被外公训斥,便会用石块把他们驱离出我的领地。
入秋后,外婆的咳嗽越来越重,进食也越来越少,并且下肢开始浮肿。虽然外公接连请来了好几位医生,药也用了不少,但外婆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立冬时,外婆已经病得无法下床。但外婆还每天坚持给我唱着童谣,喂我吃饭,哄我睡觉。而我也早已习惯,睁开眼就能看到外婆的脸,就能听到她咳嗽的声音。
后来,外婆就不吃饭了,只喝点水和橘子汁。她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不分昼夜,好像要把以前的觉都补回来似的。但我被外婆的溺爱惯坏了,少了外婆的照顾,我开始哭闹,不爱吃饭,舅舅们和几个姨妈都换着法的哄我,但我毫不领情。不过有时候,我的哭闹似乎起了作用,外婆缓缓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叫着我的乳名:
“帅——小帅吃东西了吗?是不是肚子疼呀,怎么——怎么又哭啦?” 外婆无力地咳了几声,却没吐出痰来。
“妈,小帅在这,你看看他呀。小帅,快,快喊外婆,快让外婆看看你!”四姨赶紧把我抱到外婆身边。
“外婆,外婆!”我继续哭泣,“你怎么啦,外婆?”我摸着外婆苍老的手。
“帅,好孩子——好孩子——别哭,别哭啊,听外婆说,”外婆的声音断断续续,越来越微弱,“还——记得——去年那条——船吗?外婆——外婆要——要坐船走了,去那边——找你——妈妈!你——以后要——要听话啊!”。
“去哪呀,外婆?你要去哪呀?外婆,你去哪呀?”我不停的哭着、追问着。
外婆没有回答,就又睡着了。外婆也许真的累了,被我累坏了,任我怎么哭,怎么摇晃她,她都不说话,也再没睁开眼睛,只是静静地、静静地像个婴儿似的平躺在那,似乎从来没有那么平静地安睡过。
这一夜,好漫长。我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最后是睡了,还是一直醒着。
第二天清晨,下雪了,很大,很大的雪。我坐在四姨怀里,握着外婆冰冷的手,茫然地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像个傻子。身边的外婆穿上了新鞋子,新衣裳,头发也被梳理的整整齐齐。接着,我看到外婆的船来了。不知道谁拽开了我的手,很多人一起把外婆抬进她的船里去,外婆要去一个她不曾告诉我的地方。
“外婆!外婆!”我撕心裂肺的喊着,“你去哪里呀?你去哪?”我开始大哭,亲戚们也都泣不成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哭了,只是抽泣着,静静地看着,看着那条被漆成黄色的船。我想不明白,这并不是夏季,河道里没有水,外婆为什么要坐船,为什么要走。但不管我明不明白,总之,外婆是走了,在冬季里坐船走了。而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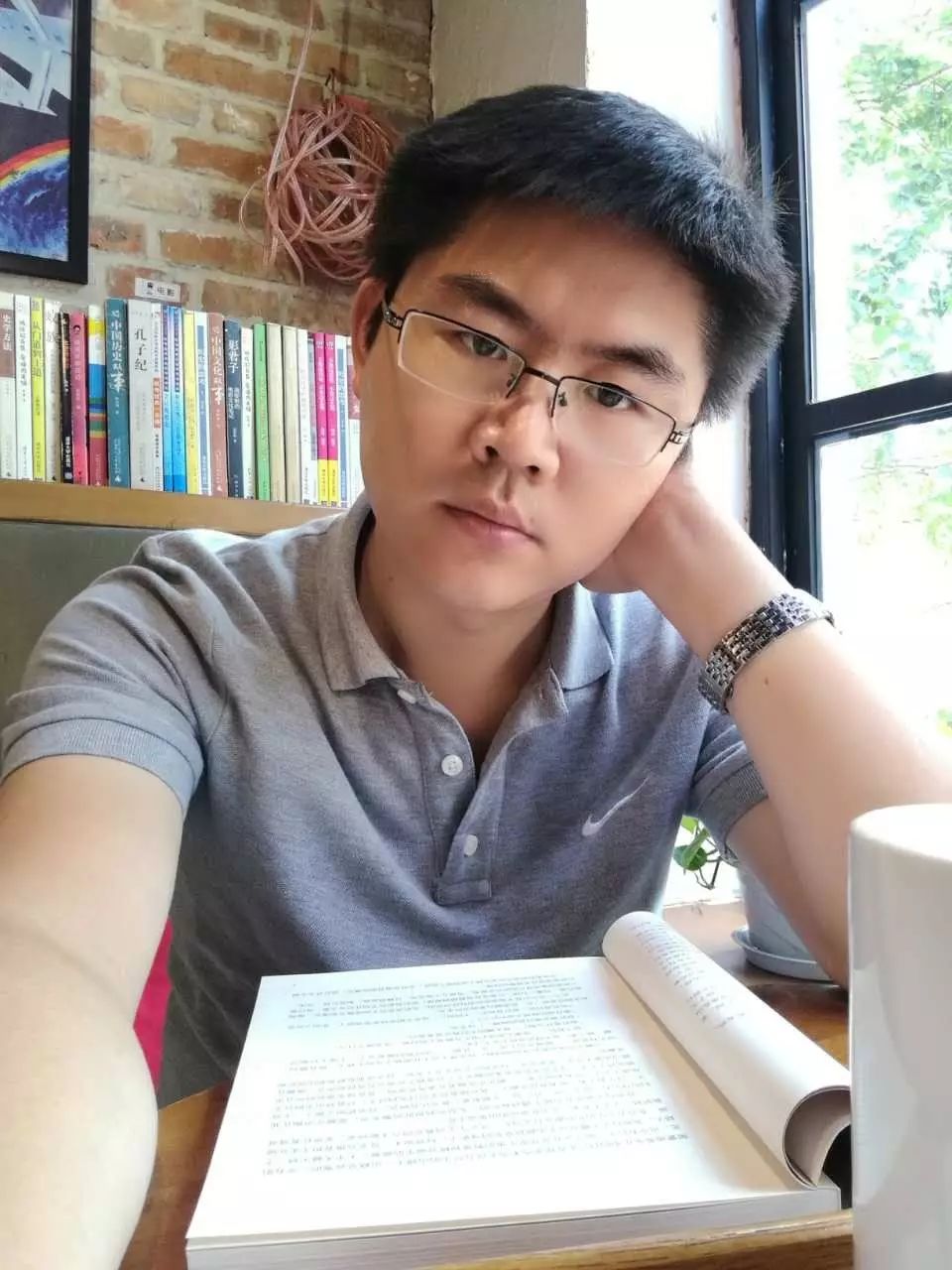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李德帅,31岁,1985年9月15日生于河北承德市承德县满杖子乡李杖子村。2005年至2010年于承德医学院就读。专业:临床医学。2010年至今工作于北京市仁和医院呼吸科。
 《根聚地》约稿
《根聚地》约稿
言之有物,多写亲历之事,故乡记忆,身边趣事,旅游寻访,读书印象,人生感悟,历史钩沉。避免无的放矢。
六根不定期确定某一主题供各位撰写。
暂定每周日推送一篇。每年结集一册纳入六根醉醒客系列。
共同努力,做我们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