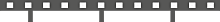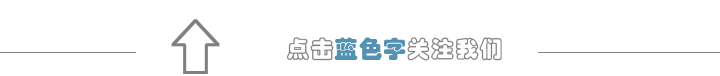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8月号
上午墓园里的人真少,三三两两的。
毕竟离清明还有半个多月呢,再过些时候只怕是要人流如潮了。有几次她是正值清明来的,人头攒动,简直就像是逛庙会那样拥挤不堪。私家车和公务车,能排成数千米的长龙,前来扫墓的男女老少得早早下车步行才能进入园区。这个墓园原来并不大,就在那座小山的山脚下,但这些年来不断地扩建,整个园区也修葺一新。尤其是新辟出来的区块,简直就像是花园一样漂亮,里面长满了各色花草,广场那边甚至还建了一个音乐喷泉。她看到了母亲的新墓碑,黑色的大理石,非常漂亮,上面刻着镏金隶书。工作人员告诉她,清明前一个星期,肯定能竖好。她在母亲的墓前伫立了好一会,心里空空的。曾经真实的一个人,现在就这样不存在了。墓碑和骨灰其实只是一种象征,证明她曾经来过这个世上。往年,她都会在墓前看到一束花,基本都是提前一两天才放在那里的样子。但最近有两年了,她都没再见到过。出了什么事吗?她在心里问。她知道是谁放的,但她从没说过。
阳光晒在她的身上,暖暖的。今天的天气不错,天很蓝。早晨刚从城里出来时,天还是阴沉沉的,仿佛还飘了点毛毛细雨。现在却是完全放晴了,甚至连云彩都很少。整个墓园里真是安静啊,静得能听到远处的鸟叫。墓地里的墓碑排列整齐,就像一列列骨牌。原来的墓碑都是水泥墩,上面刻着那些对外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名字。他们中有年老的,也有年少的,现在永远在这里沉默。生与死,在这里就是这样鲜明。所有站着的人,最后都会躺下去,她想。
那个男人一直陪着她来到墓前,还在墓前放了一束白色的康乃馨。这让她心里有点感动,他周到而细心。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讨好她。她的丈夫过去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这就是差别。
“今天是个好日子。”他说。
她笑了笑。她相信他说这话不止一层意思。她知道他的心思。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男人,不一般。自然,这话本身是很正确的,至少是赶上了一个好天气。她一直就想着要来一次了,却一直没计划好。父亲其实早就念叨了,才过惊蛰,他就催了。看来他要在这个清明节,好好地祭扫一番了。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不太积极来墓园的,尤其是最初的那几年,人们甚至不能提到母亲的名字。通常情况下,她过去都是陪着姨妈来。
事实上这些年来她对妈妈的印象已经有些淡化,像是陈年老照片受潮在逐渐褪色。妈妈出事的时候她也有十几岁,可是她对那段记忆是混乱而模糊的。她无法判断那件事情对她的打击究竟有多大,只知道当时整个人都是木的,过了很久她才感到那种刺心的悲恸。她不敢想,一想就感到心悸。现在父亲对上坟这件事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她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她不相信他对妈妈的看法有了什么根本变化。或许是他老了?她知道她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了证明他妻子的错误,甚至不惜用一直鳏居来惩罚自己。其实他是有机会再婚的,那时候他才中年。真的不止一次有人给他介绍过女人,有些条件还相当不错。可是,他非常干脆地就回绝了。可见男人一旦心狠起来,那真是了不得的,她想。
两天前,她去看望他,他再次提起了这件事。她向他作了保证。就在她回家的路上,姚总给她打了电话,她灵机一动就抓了他的差。
“行的,没问题。”他回答得非常爽快,甚至为她约他而感到有些欣喜。
“这个墓园很不错。”他说,“我还是第一次来。”
她在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这个墓园原来很简陋的,现在越修越漂亮。”
“第一公墓现在已经满了,现在看这里还真不错。”
“是的,现在做得漂亮了。”她说。这对死者算不算是一种安慰?至少对她来说算是的,每年她都会来一两次,清明和冬至。每来一次,她心里就会舒服些。有时她甚至在平常的日子也会来一下,如果她心情不太好的话。这样的体验很奇特。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就像梦一样。
他们在二楼的小包间里。
这家饭店的生意真是好,楼上楼下的,挤满了客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还能要到一个单间。那个单间正好临街、靠窗,坐着就可以看到小镇的街景。街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店铺,路边还有一些尚未收摊的卖菜的、卖日用杂货的,甚至还有卖鼠药、卖假古董的……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镇子,舒适平和。时光在这里是缓慢的,缓慢得就像是镇子中心的那条小河的河水,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流动。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因此感觉格外陌生,陌生而新鲜。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她知道这个地名,离这小镇不远就是著名的温泉胜地,他说那里现在新开了一家很高档的温泉会所。
“我请你吃当地的土菜,非常正宗的土菜。”他说。
“简单点,”她说,“清爽就好。”
俞洁没什么胃口。天气突然热起来了,她觉得坐车有点胸闷。一天前天气还有些阴冷呢。在墓园时她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像极了她多年前看到过的那个身影。当时她心里一怔。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她一个人站在那个空旷的广场上,等待着去洗手间的姚总,不免有些恍惚。许多年前她也是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捧着母亲的遗像站在这片空地上,等她的父亲。她整个人都是懵的。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会临到她的头上。她有些不知所措。然后她看到一个瘦瘦的男人一直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盯着她看,她就扭过了身子。他的神情有些局促,甚至有些紧张。他像是在时刻提防着什么人。可能是他觉察到的确并没有什么危险时,他才向她走了过来。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要向她走来。
“你是文秀的女儿?”他问,脸上有些尴尬。
“是。”她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悲伤的冰凉。
“你妈是个好人,好人,外面的人在瞎说。”他说。
这是一个怪人,当时她想。一直到好久以后,她才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他,妈妈会怎样?她不知道。或许那就是命,命运是最最不可捉摸的。
四菜一汤,两个甜点。对他们两人而言,显然是多了。她看不出菜式有什么特色。“你看这个‘松瓤鹅油饼’就是《红楼梦》里写过的,贾母吃的。又酥又甜又香。这‘泡菜苕粉肉丝’,城里也是没有的,是这里正宗的泡菜,又酸又辣。还有这道汤,这里的圆子其实是鱼圆,特别新鲜。你多吃点。”他说。她笑了,“‘红楼’都出来了,哪里还是土菜?分明是国宴嘛。”
“这相当于是这小镇上的‘国宴’了。”他笑了笑,“很多人是慕名赶到这里来吃呢。”
“从城里赶来这里,倒也还是不近。”她想,美食诱人。
“今天是巧了,”他说,“正好不远。”
菜的味道果真是不错的,在城里大抵是难得吃到这样的特色。吃饭过程中,他的手机响了好几次,他都是匆匆地说了几句就挂了。他是大忙人。为了她,他是把工作全放下了,让她心里有了一些愧疚。
“你妈妈……多少年了?”他问。
“十几年了。”
他叹息了一声,“那很年轻啊。”
她不语。
他居然没有问她母亲离世的原因,当然,如果他问了,她也不能说实话。这是她心里的痛,她甚至对丈夫都没详细说过。丈夫是隐约知道一点的,但他也不细问。他看过她妈妈的照片,说比她还要漂亮。俞洁在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妈妈年轻时比她更妩媚。妈妈有一双非常好看的丹凤眼。妈妈年轻时的生活,好像一直就有些风言风语,谁让妈妈那样漂亮呢?她虽然只是一个商场的营业员,但真的是走到哪儿都光彩照人。那个时候国营商场还很红火,营业员也还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她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跟着妈妈去过她的商场,总有阿姨们抱她、亲她,还塞给她一些饼干和奶糖。那时候她特别羡慕和崇拜妈妈,觉得她特别能干,能说会道。因为她在商场里工作,所以她认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那些人里,大多是有点小权力的,最差也是什么工厂的办公室主任什么的。那些人乐于讨好她,为她忙这忙那的。她喜欢差遣那些人。事实上,很多都是芝麻小事,而且也并不全是她自己的事,大多都是在帮别人的忙。她喜欢张罗,说她是热心,或者是她自己就为了追求那种被人认可的价值?
妈妈其实也烦恼,街坊邻居的不时有人托她买这买那。那些人当时为了想办事,就使劲地夸她,而背地里却一直在嚼她的舌头。尤其是她出事后,什么脏水都往她身上泼。她觉得当年的妈妈好傻。她是个没有活得很明白的人,她喜欢找那些人办事,但她又厌恶那些喜欢占她小便宜的男人。要是换作自己,她一定不会去帮那些人,她想。
她不理解妈妈。直到自己婚后两三年,有时她才会想妈妈当时的境况。过去她从没有想过,可现在却一幕幕地全想起来了。她想起自己看到过妈妈沮丧时的情形,好多时间她坐在一个地方发怔。甚至她有时还在做事,也会发怔,不知不觉地停下手里的活。这样的状况有一年多?有一次还抱着她哭了。她想离婚,也和父亲在争吵时提出过,但却没有真地行动。她内心里是痛苦的,挣扎的。
“你今天真漂亮。”姚总说,“你这件翠绿的上衣好看,衬得你的皮肤更白了。”
她笑了一下,说:“是你今天有企图?甜言蜜语后面,都是有想法的。”他没有说她的外套,却说她的内衣。她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薄呢风衣,黑色的长统丝袜。她有一双傲人的修长美腿。
他却又一本正经起来,“没敢多想。”
她认识他有好几年了。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和她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却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她在心里觉得他这人还真的不错,有好几次她差一点就放弃抵抗,最后失守。可他却就在她那如同一层纸薄的防线前,恢复了君子的风度。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强迫她,她在心里还是很喜欢他的这种淡定和从容。或许,这是另一种男人的坚强?她需要被尊重。她觉得他应该不缺女人。这年头对他这样的有钱男人来说,女人可以像水果店里的水果一样让他尽情随便地挑选。她不希望自己只是他生活中正餐之后的一只水果,当然,更主要的是她不想那样去做。她不想做任何人的情人。她不希望和妈妈过去一样,会在身后有这样那样的风言风语。她希望她能一直和他保持着这种有点暧昧的友好关系。或许有那么一天,他会觉得无趣自动离开。那样她会觉得有遗憾吗?不,不会的,她在心里笑了一下,为自己这样地设问。
“男人是不是都会这样?”她问。
“哪样?”他显然是装糊涂,“男人夸女人?我这可不是夸,我说的是真话。”
突然楼下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接着他们就看到腾起了一股浓浓的白烟,慢慢向四下里扩散……然后他们看到一长溜的车队缓缓驶过来。“结婚?”她说。“结婚。”他说,“看来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春天风大。
他们的车开在路上,不时能看到路边突然地卷起一阵旋风,淡黄的尘风中夹着草屑什么的,斜斜地向远处的半空中直刺而去。太阳很好,天气也许会越来越热。她坐在车里感觉有些困倦,昏昏欲睡。她其实很怕坐熟悉的男人的车子,尤其这个男人如果和自己存有一定暧昧关系的话。姚总过去不止一次地要开车带她出去转悠,大多数时候都被她回绝了。她心里有阴影。母亲那年就是跟随一个男人去郊区,出了车祸。那个男人没事,只是小腿骨折,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就恢复了。而她的妈妈却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当场就香消玉殒。
那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社会新闻,尤其是在熟悉或半熟悉的人际范围里。对于妈妈和这个男人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情人。她记得自己在学校里都能感觉到老师看她的眼神,有些特别。有人说她妈妈至少有五六个情人,而且把她的美貌过分夸大了,说得真像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开车的男人是一个工厂的领导,据说那人不像是出那种事的人,平时作风严谨。他比她大了有十几岁,交往也并不多。还有人说,妈妈有一个情人是什么局长一类的。对所有的传言,父亲都保持了沉默。俞洁从那个时候起有了一种想法,就是美丽和丑恶是互相映衬的。她喜欢美丽漂亮,但又害怕美丽漂亮。她其实很想看看传说中的那些妈妈的情人们,是什么样子。直到几年后,她再次在墓园看到那个瘦瘦的戴着近视眼镜的男人。她当时以为他也是家里有什么人安葬在这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特地来祭扫她母亲的。为了避开敏感的时间点,他都是提前几天在周末的时候,一人悄悄地来。
俞洁不喜欢这个人,她说不出理由。显然,他并不在那些传闻的名单里。甚至她都有些怀疑他和妈妈根本没什么关系,只是他的单相思。她不相信妈妈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看上去毫无理由。在别人的眼里,妈妈是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说起来各种的不堪。但他显然对外面的那些传言毫不介意,依然对已经埋入地下的女人怀有很深的恋情。她听姨妈说,这个人是中学老师,还是个诗人。他写过很多诗,还出过诗集。据说这人年轻时因为写诗倒过霉,离过婚,又丧过偶。“他们真的好过。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爱上他,你妈真是昏了头了,”姨妈这样生气地评价说,“她还被他弄得神魂颠倒的。”
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好上的,反正他给她写了很多很多的诗。俞洁不认为妈妈是个多么文艺的女人,或许她爱上他只是单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崇拜?诗人的神秘?无论如何,她是没法理解妈妈是如何在几个男人间做出取舍的。世俗的和精神的,她更偏重哪一个?俞洁永远也不会知道妈妈内心真实的想法。每个人的感情世界其实都是复杂的,她想。妈妈过去在她的心里是那样的一个好妈妈,她看到的永远只是母爱的一面。
“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姨妈往往提起这些事,气就不打一处来,“你妈死了,没一个男人去送她的。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像是蜜蜂一样围着你妈转。人没了,一个个全缩成了乌龟。”
俞洁想到了那个老师。
时间是试金石,或许所有的男人真的只有他是真心的。她知道他几乎每年都会去,在墓前放上一束花。虽然只是一束黄菊或是白菊,但她觉得这个男人倒是一片真情。有一次她甚至做出了一件很傻的事,去他的中学打听。她想听他怎么评价她的妈妈。可是,传达室的人却告诉她,他调到一所大学去教书了。听到这样的消息,竟让她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欣慰:妈妈看中的男人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她没有再去大学找他,只是听说他依然一个人生活。他有孩子,好像在外地读书。现在想来,也早应该工作了。
“你妈可能真的喜欢这个书呆子。”姨妈后来这样说过一次,“她对他的感情,超过对于别的任何人。我都没对人说过,她曾经和我说过想和你爸离婚,嫁给这个男人,疯了!”她觉得她妹妹应该去追求那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就像她平时表现出来的一样,但后来她也改变了看法。尤其是后来知道这个男人每年都去祭扫,“倒也算是有点良心的。”她说。
她的手机响起来,是丈夫的。她正在犹豫要不要接,电话却又断了。既然断了,她也就没有再回拨。她吃得不多,眼睛就关心起包间的陈设来。包间也是略作装饰的,墙上还挂了一幅书法作品,想来是当地的书法家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她喃喃道。
“‘懒’。”他说,那个字写得有点草,她有点不能辨识。“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她感觉他对这首诗比较熟,前两句她是懂的,只是对后两句不甚了了。她没问,他也没解释。饭毕,两人从饭店出来,发现时间也还早。
“去哪儿?”他坐在车上这样问。
“回家。”她说,她真的想回去了。
他笑了一下,说:“好咧。”
嘴上这样说,但车子却向另一个方向去了。她嘟哝了一句:“骗子。”随即合上眼睛。她信任他。他能去哪儿呢?“我把你拐卖掉。”他说。她在鼻孔里吭了一声。他是个不错的男人,他的价值不是去干坏事。
“这是去哪儿?”俞洁仿佛是睡了一觉猛地惊醒似的,突然这样问。她感觉自己刚才睡着了,至少也有五分钟。五分钟里,思绪可以穿过现实和梦境。她坐在车里,突然想起妈妈当年出事,一定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交代,却没来得及。想到这一点,她心里不由得有点小小的恐慌。
“那个开车的男人其实和你妈没关系。”半年前父亲突然这样说,让她吃惊不小。“他是带她去一个地方,看货。他们一直想合作,做生意。你妈其实内心里很活泛,她一直想做生意,但找不到合适的合伙人。有人说他们是什么私会,纯粹胡扯。”
她有点不能相信,因为她从来就没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他之前为什么一直没说?
“那个时候你妈妈的商场已经不行了,快要倒闭了,好几个月发不了工资。”父亲哼哼着说,像是在表达着不满。“那个时候做生意,并不像现在能光明正大的。那个厂长在外面有关系,他就希望通过你妈出面,倒腾煤灰、钢材什么的。”
俞洁觉得像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一样。
“那时候不能说。出事了,也不能说。”父亲说。
她无法理解为什么直到现在,他才这样说。当然,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说什么都不再有实际的意义。
车里是越来越热,可是姚总却并没有打开空调制冷。
“我真要把你拐卖掉。”他说。
“好。”她毫无表情地说。
他笑起来,“真好。”
“你是坏人。”她说。
“为什么?”惊讶的语气里,他好像显得很委屈。
“你不应该让我喝酒的。”
他再次笑起来,“一点红酒。”
“我醉了。我困得不行了。”她说。
金色的阳光下,温泉度假村非常美丽。
她想不到他会把她拉到这个地方来。这么一个气派堂皇的温泉度假村,正是他投资的。它像一个很大的庄园,占地大概有好几万平方,有一座主楼和两座副楼。到处是绿地,还有喷泉和假山,还栽种了许多南方植物,因此看上去有了不同的异域情调。他带着她,四处看。温泉区占了整个区域的一半以上,但核心却是宾馆住宿和餐饮,还有各种会议室、KTV和各种健身设施,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网球场。宾馆是五星级的标准,客房装修都是格外的讲究。
“真是豪华。”她惊叹说,“这得很大的投资啊。”
当然,他说他只是股东之一,还有另外十多家的投资商呢。“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他轻描淡写地说,“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老板啊。”
俞洁不知道他说的“他们”是谁。但是她知道这个社会里有形形色色的有钱人,有些有钱人是在明处的,有些人却是在暗处的。隐蔽在暗处的有钱人,往往才是真正的有钱人。那些有钱人深不可测。姚总自然也是有钱人,但是他表现得却很平常。
“下次周末你可以和你先生一起来,”他说,“打打球,泡泡温泉。紧靠这里的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很漂亮。”
她不说话。他这样客气是虚假的,她想,他难道不是一直想泡她么?谁会喜欢情敌呢。她和他交往这么久,他很少主动问她丈夫的情况,她也不想说。她的婚姻没什么好说的。除了初恋之外,她没有感觉到多少幸福。母亲的事情,对她的婚姻选择是有很大影响的。没有人知道这两者间的关联,她从没对人说过。
他请她去他的办公室喝茶。
这才是真正拉开大幕,她想。不管前面做了多少的铺垫,男人最终是要一个结局的。她觉得他的耐心已经非常好了。
“你的办公室真是气派。”她觉得算是见识了。
他的办公室是独立的,和业务部门是分开的。他在楼上。办公室太大了,里面一式的红木家具,办公桌简直像是一张台球桌。“我不喜欢。”他说,“装修好了,我才知道。我又懒得去改。”
“喝绿茶还是红茶?红茶有祁红。或者喝普洱?”
“就绿茶吧。”她说。
他在泡茶,她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远方。远处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到处是一片碧绿。太阳这时候呈现出一种耀眼的金色,让整个天空的蓝色显得有点泛白。这里远离城市,相距可能有数百里。她站在这里,仿佛和过去都做了干净的切割。“天气真好。”他在她身后说。她感觉到他就贴在她的身后。她没有回转身。她想好了,她今天要让他做一个了结。是的,既然他这么多年了,一直对她有企图,她总要给他一个结果。
她感觉到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肩头。那么,下一步他可能就是会把她搂住,会亲她,会在她的身上乱摸,会把大手强行地伸进她的内衣。她会温柔地顺从他吗?要不要装着抗拒一下?他当然会不顾她的抗拒,把她拥进他办公室里面的隔间,推倒在那张大床上。她可以不抗拒的,因为她对他是怀有好感的,内心存着一种感激。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关照她的。不管是今天的上坟,还是既往。甚至她过去因为工作问题,他真的帮了她大忙。他从没要过她什么回报,甚至想请他吃饭,也都是他付账。如果他们不能成为情人,至少她要委身他一次,否则她就没法定位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喝茶。”他说。
她看到他已经坐到茶几那去了,把第一遍的茶水泼了,续上了新水。
他很讲究。
她像是释然了,顺从地坐了他的对面。
“茶香。”她说。
“其实红茶更香。”
“还能减肥。你们有钱人,喜欢喝红茶。”
“也就那样一说。减肥还得靠运动。”
“你不是说你经常运动么?又是游泳又是打网球啥的,怎么肚子也没见小。”
“原来也不算大吧?我已经算是保持得很好了。当然,和你们女人不能比。你苗条。”他笑了。
“你肚子里装了坏水。”
“你早就知道了?”
“我真的有那么好看么?”她问。
“……你不自信了?”
“女人的自信都是男人给的。”
“男人的自信是女人给的。”
“不对吧?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男人的自信是金钱给的。男人有钱都是花心的。你这里这么多的姑娘,你是身在花丛里,可以随便采。”
“你是个聪明人。”
“我很傻。”
“有多傻?可以轻易被骗么?”
“你心情不错。”
“你不好?我看你挺好的,年轻,又漂亮。”
她不说话。
他看着她。
她也看着他,眼里有水在流动。不,是光,流光,在闪。
两具赤裸的肉体随意地摆在床上。这是在一场激烈的纠缠后,疲惫地自然呈现。房间里散发着肉体的热气,热气腾腾。“你怎么了?”她看他起身在柜子的抽屉里找出了一瓶药丸,倒出两颗一仰脖子就咽了下去。看他的裸体,上身还是很结实的,胸脯很厚,肩膀也宽。看来他平时积极健身,是真的。“硝苯地平片,”他说,“心脏不太好。”
“你胆真大。”她翻了个身,拉过被子的一角,把自己卷了起来,就像是一个虫子卷起了树叶。“你真漂亮,性感。”他重新躺到了她的身边。“你是个坏人。”她说。他没说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假如他不能算是阅人无数,至少也算是个中老手,自然懂得女人这样说,只是一种嗔怪。语气的后面隐藏着的是真实的喜欢。他的长叹,只是感叹世事无常。有些事情算是命中注定么?
她听到了他的叹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叹息。但她是踏实的。不管今后如何,她今天终于把自己交给了他,算是认识这些年来的一个终结。在这件事上,她是主动的。他们本来喝了茶后都决定由他开车送她回城了,在他准备取车钥匙的时候,她说:“好了,我们拥抱一下吧。”他怔了一下,然后坚定地抱住了她。“你真香,”他说。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嗅着她头发的香味。“你真的喜欢我?”她希望再一次地从他嘴里得到证实。“喜欢。”他说,喉咙有些发干。
“抱我到床上去。”她在他耳边轻声说。
他显得有些迟疑。
“你确定吗?”他似乎有点不相信。
“不许欺负我。”她说,脸烫得就像是被火烤了一样。
车子在回城的路上狂奔。
天色向晚。
两人都没说话。西方的天空正在变暗,云层越来越厚。太阳正在西沉,给那些云层镶上了一层金色的丝边。她看到自己右腿上的黑丝袜不知道怎么跳线了,于是修长的大腿上就有一道长长的痕迹。她赶紧把腿并了并,又拉了拉薄呢的风衣,盖上。好在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去那个饭店吗?”车子快要进城的时候,他突然这样问。
她想不明白。
“那是当年他们一起吃饭的地方。”他说。
“谁?”
“我父亲,和你母亲。”
“那个饭店边上,就是一家旅社。”他说,“当时没有什么宾馆,就叫旅社。”
她想到了那个瘦瘦的老师。世界居然这样小,他居然是他的儿子。显然,他早就知情的,但却一直瞒着她不说。这样看来,他当初认识她就是有目的的。她感觉头脑里一片混沌,坐在车里身体像是要飘了起来。如果她知道这一切,她今天还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吗?不!她在心里说。但她又不能肯定。这一刻,她对自己格外的不自信了。
“你爸是干什么的?”她像是有点疑惑地问。
他眼睛看着前方,前方是一个弯道。护城主干道上,车流繁忙。“二机厂,第二机械厂。”他说,“副厂长。”
她感觉自己又被意外了。她不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心里有点酸,忽然感觉想哭。而这样一想,眼里一热,前方的视线就变得模糊起来。
车里一下像是曲终人散的剧场,空荡荡的寂静。
“对了,你两天前打我电话是有事么?”她想了想,问。
他不说话,眼睛看着前方。
“一定有事的。”她想。她当时抓了他的差后,都忘了问了。
“没事。”他说,“就是突然想起来了,打个电话。”
她再次无话可说。
“你爸……他现在好吗?”她问。
他叹了一口气,眼睛依然注视着前方的道路。
“如果……如果哪一天我也不在了,”她扭过头去,眼睛看着车右侧的远方,“你会送花给我吗?”
他不说话,加大了油门,车子快速地不断地超越前面的车辆,继续狂奔……在这城市的郊外,有着大片的绿色树木和植物。一旦过了清明,就算是进入深春了。越来越浓烈的深春之下包藏了过往太多的隐秘……而越是隐秘,春之色就绽放得越鲜明。
(文内图片若未注明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