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要裸奔,我想可能自己本来就是个比较奔放的人,觉得一辈子没裸奔过,人生不算完整。”
文 / 江芬
编辑 / 卜昌炯
32岁的白宇有过多次裸奔经历,让他感觉最爽的一次是在安纳普尔纳海拔近5000米的Tilicho湖边。安纳普尔纳位于尼泊尔境内,属喜马拉雅山中段,是全世界徒步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当时拍下的一张照片里,白宇背面全裸,张开双臂,凌空跃起,头顶是没有一丝杂质的蓝天白云,脚下是白茫茫的雪地和冰封的湖面。
尽管冻得龇牙咧嘴,他还是很享受做“一具在冰雪中欢呼雀跃的肉体”。那种天地间扑面而来的原始的荒莽感,让他心生冲动。
“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要裸奔,我想可能自己本来就是个比较奔放的人,觉得一辈子没裸奔过,人生不算完整。”他在旅行笔记里写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热血白羊男,好奇、慷慨、坚韧、爱冒险,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洒脱和豪迈。
平日里,他把工作和旅行分得很开,要工作就好好工作,要玩就玩个痛快。2016年,他踏踏实实在网游公司上了一年班。此前,他完成了一段为期580天的极限旅行,足迹遍布印度、埃及、马尔代夫、土耳其、泰国、美国等地,并4次单车骑行进藏。
这段旅程是他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用了近20个月才送达。“我不想通过这件事改变什么,只希望每天都变得独特,让自己更强烈地活着。”白宇告诉《博客天下》。
他的字典里没有“安然无恙”,比起都市生活的稳定,他更执着于穿越世界,恣意狂欢,要的正是热烈而奔流不息的生活。
歌德说:“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是不知生之为何。”白宇说他没有类似的烦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生该如何度过。
不久前失联的知名航海家郭川是白宇的直系师兄,他们都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白宇一直密切关注救援进展,但对于探险随时可能带来的危险和代价,他似乎早已看破。
“心随风舞,葬生荒芜亦无悔。”白宇引用偶像石田裕辅《不去会死》一书中的这句话对《博客天下》说,“这何尝不是郭川一个好的归宿,世事难料,风险不会阻挡我继续远行的步伐。”
白宇看上去比照片上还精瘦,1米69的身高,体重仅110斤。但就是这样一副身板,一路带着他跨过山和大海,在沙漠无人区里冥想岁月,在日出日落、星辰流转间聆听瞬息与永恒。
这是北京立冬后的一天,他在家中只穿了一件休闲卫衣,习惯性将袖子往上卷,右臂上露出“Valar Morghulis”的文身。Valar Morghulis是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里的高等瓦雷利亚语,意思是“凡人皆有一死”。
除此之外,白宇身上还有3处文身,分别是左肩上象征神明庇护的荷鲁斯之眼、几天前刚在后背上文的头戴狼人帽的幽灵公主,以及胸口上的一串英文字母carpe diem(活在当下)。
可能是文身的关系,白宇身上有一种喷薄欲出的奔放和狂野气质,眼神也透着一股锐利,然而说话声音却很柔和。
他的家里摆放着很多探险旅行类图书,墙壁上则挂满了旅途中拍摄的照片——它们出自一台跟着白宇闯南走北五六年的已磨损的尼康D700相机,雪山、星空、姑娘、历史遗迹,是他镜头中永恒的主角。
白宇1984年出生于安徽黄山,父亲是老师,母亲是会计,虽是家中独子,从小受到的却是自立、自由的开放教育。小时候他最爱看的一个节目就是《正大综艺》,“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这在他心里默默埋下一颗探索未知世界的种子。家门口的黄山,他已经记不清爬过多少次。
成年后,父母了解白宇自由不羁的性格,对他在外闯荡的能力也比较放心,很少过问他生活的事情,支持他做出的每个决定。
硕士毕业,白宇是全班唯一没选择在航空航天系统工作的人。“航空航天系统有特殊性,不能随便出国,可能连因私普通护照都拿不到,我的性格也不适合做科研。”
于是,他成了一名网络游戏程序员。虽然平时工作经常加班,但他常利用调休、年假、法定节假日等外出旅行,一年中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奔波在路上。
2014年2月,白宇30岁,他决定送给自己一份梦寐已求的大礼——辞职,开始580天的极限旅行。
在印尼伊真火山,黑夜里,他徒步到距离火山口不到5米处看天然硫黄燃烧时发出的梦幻般幽蓝色火焰。忽然风向改变,他瞬间被二氧化硫包裹,濒临窒息,慌不择路地逃命,直到10分钟后才呼吸到新鲜空气。
在加利福尼亚佩里斯谷跳伞,8000英尺的自由落体,除了风的呼啸声,所有直观感受都被暂时屏蔽了。如果不是出于大脑对重力方向习惯性的判断,左右与前后、天空与地面没有差别。
印巴边境沙漠徒步,夜晚他跟同行的姑娘找了一处沙丘凹陷处露营,一边看着星星,一边入睡。半夜突然被不明温热物体拱醒,睁眼一看,是一只迷路的小羔羊,蜷缩在毡子上,正好夹在他们俩之间,楚楚可怜。
近20个月,途经20个国家,20万元开销,探险旅行已然成为白宇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其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要数骑行和徒步。
“有些地方,用身体的力量而非靠发动机到达时,同样的风景点燃的会是截然不同的情绪。”他痴迷于用燃烧身体的方式,在地球表面划过痕迹,越折腾越辛苦,越感到热血沸腾。
白宇4次单车进藏,每次都沿着不同的路线,中尼公路、川藏公路、阿里北线、阿里南线,共计近6000公里,一路践行“不作死就不会死”的风格,从各个视角领略雪域高原大气磅礴的自然风光。
中尼公路是白宇高原骑行的第一条路线,他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花了2200元买了一辆深蓝色的捷安特山地车,一个人从樟木中尼友谊桥出发,没带其他装备,穿着在印度和尼泊尔买的花哨衣裤,踩着一双快坏了的布鞋,翻越垂直高度超过2000米的雪山,在12天的征程里释放血性。
最大的挑战是阿里北线1450公里的荒野骑行。2015年8月,白宇邀请好友“铁人”姚伟同行。5年前,他们相识于故宫附近的诗意栖居咖啡馆,发现都热爱骑行和探险,一见如故,不久后一起环台湾岛骑行。
阿里北线出发前,他们在拉萨遇到了骗子。骗子支开铁人,对白宇说铁人被绑架了,电话那头传来模仿铁人的呼喊声,白宇为了救铁人,汇出1000元钱。等他们彼此联系上,才知道受骗。“虽然他很傻,但如果是普通朋友就不会汇钱,白宇是个可以交心的铁哥们。”铁人对《博客天下》说。
这次骑行他们带上了帐篷、油炉、锅等野外生活必需品,从狮泉河自西向东横穿藏北,抵达当雄。“95% 的时间里都是灰头土脸的挣扎,只有5%的时间在欣赏美景中得到安慰。”白宇说。
阿里地区全程4500多米的高海拔、多变的天气、简陋的补给条件及无人区的存在,都令骑行变得困难重重。他们对生活的需求降至最低,不挨饿、不受冻就好。“吃得最多的食物是方便面,平均每天至少想念8次火锅。”白宇还因为匮乏新鲜蔬果,一路牙龈出血。
骑行的前15天,他们经历了1000多公里连续起伏的“搓板路”。按每两米3个“搓板”计算,一共约150万次颠簸。每一次颠簸,视线都在抖,空荡荡的胃在晃荡,屁股被磨得生疼,直到血肉模糊。而且相当费力,消耗的体力大约是柏油路的2.5倍。
他们在雄梅镇终于骑上了神清气爽的柏油路,但是从青龙乡到纳木错的93公里路全程逆风,整整9个小时耳边不断呼啸着风声,不仅耗损体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锤炼,“逆风骑行如蚍蜉撼大树一般,同老天爷过不去”。
原本计划骑行15天,结果因为体力不支,用了19天。“我们在此之前几乎没查到骑行攻略,路上只遇到一个骑友,一年可能不超过10个人会骑行阿里北线。”铁人回忆。他说白宇很靠谱,彼此能够互相照应,这是两人一起经历过的最艰辛的骑行。
当时的白宇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想再骑车了,“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公里的前行,都是煎熬。内心深处一边埋怨老天爷,一边痛恨自己花钱买罪受”。但是探险结束,在重庆馆子享受热辣的火锅时,他又开始想念这段苦旅。
留在白宇内心深处的画面是,在空气稀薄地带无尽的荒原里,他如蝼蚁般划掠过一个又一个藏北大盐湖,与藏野驴和藏羚羊一起奔跑,偶尔惊鸿一瞥双日晕、雪山,耳边聆听着朴树的《平凡之路》:“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在色林错湖畔的布嘎村,白宇度过了阿里北线骑行最难忘的一个夜晚。那里是地球表面海拔最高的一片荒野,稀稀落落只有几间屋舍的小村庄,地图上都没有被提及,之前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 2015年8月,白宇在阿里北线骑行,途中仰望星空
银河倾落,他和铁人喝着拉萨啤酒,借微醺喃喃自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等老了以后,再看到‘into thewild’(荒野生存)这样的字眼,我都可以有这段疯狂的燃情岁月作为念想。”白宇说。
对比骑行进藏的4条线路,白宇认为中尼公路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阿里南线的景色一直到了神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错才达到高潮;阿里北线风光以盐湖为主,雪山不多;川藏公路的沿途美景过于分散;相比之下,中尼公路几乎每天都有天地大美而不言的藏地风光。”
“西藏骑行的一个绝妙之处是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束缚,欣赏并拍摄到一般人见不到的风景。”白宇回忆,在阿里北线骑行,他们经过碧蓝的洞错湖时已是下午5点,为了看湖边7点的日落,他们就地扎营,晚上还拍到湖面上星星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让白宇感触更多的是藏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毛垭大草原上,他遇到一位从成都徒步到拉萨朝圣的残疾人,右膝以下是义肢,金属棍发出“哒哒”的“脚”步声,背包上写着“求资助,不搭车”6个字。
“一般人走这2000多公里的路都要两个半月,不敢想象他会付出多少辛酸,许多人许多事,你未必理解,但一定要心存敬畏。”白宇说。
荒野徒步同样是他所热衷的。雅拉穿越、贡嘎穿越、年保玉则穿越、安纳布尔纳环线、珠峰大本营环线⋯⋯
实际上,白宇第一次徒步就迷路了。2011年,他们一行5人踏上从贾登峪至禾木的北疆徒步,在翻山越岭到达喀纳斯河时,误入只有当地巡山员才会走的右岸,直到天黑,他们也没有找到桥过河。
“没有帐篷,没有睡袋,没有生火。”阿尔泰山深处,手机信号全无,求救无望。他们捡来一些干草,将雨衣铺在上面,躺在雨衣上过夜。刚下过一场雪的北疆夜间温度只有零下5度,见白宇没有多带衣服,同行的一位伙伴给他一件羽绒背心,另一位伙伴也分给他一个暖宝宝。
“手和脚还是极度冰冷,要不时让身体自然发抖,产生些微热量。每隔一两小时,同伴之间会相互招呼一声。”白宇记得零点过后,是一个伙伴的生日,大家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唱着生日歌。
在黑暗与寒冷中冻了一夜,第二天水壶里的水都结冰了,白宇身上挂着一层霜。当天晚上到禾木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感冒发烧。白宇说,这是迄今他经历的最寒冷的一晚。
2015年4月,已经快要立夏,川西高原雅拉雪山上依然天寒地冻。白宇沿着若隐若现的山路摸索前行,漫山遍野是红杉木原始森林和杜鹃灌丛,还有缠绕其间的松萝,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银装素裹。
第二天,他在暴风雪中翻过雅拉雪山垭口,恶劣的天气使他全身都处于湿冷状态。垭口的山坡上,大雪覆盖下有许多零碎的乱石堆以及溪流、湿地,一脚下去完全不知深浅,也不知会踩到什么。
“忘记自己跌倒在雪坑里多少次,有时腿抽出来了,鞋子还卡在雪里,有时直接踩穿两尺厚的积雪,踏进暗涌的溪水中,原本就灌了雪的鞋子立马全湿,寒冷从脚底直逼全身。”白宇最倒霉的一次是踩到石头边缘,左腿猛然陷进石缝,膝盖磕着石头,之后每走一步都隐隐作痛。
几天后,他又和6个伙伴在贡嘎雪山徒步穿越海拔近5000米的日乌且垭口。那时积雪厚度达1米,3公里走了近5个小时,他们决定赶在风雪再次来临之前扎营垭口。
扎帐篷时,由于不可能把雪刨开,他们就用脚踩出一片空地,把地钉插进踩实了的雪里,再刨些雪压在地钉上,等雪冻住后才固定好帐篷。刚刚拉上外帐的拉链,白宇就听见冰雹雪粒砸在帐篷上的噼里啪啦声。他们直接在大帐内生火做饭,户外气罐发出的火焰可以顺便烘烤湿漉漉的衣物,使帐内温度达到10度。
等回到自己的小单人帐睡觉时,温度只有零下6度,笔记本电脑都没法开机。他钻进睡袋,用身体把电脑焐热,这才可以正常使用。于是,风雪交加的垭口上,他独自缩在2立方米的单人帐内,享受一边喝杜松子酒一边看电影的小幸福。
天亮钻出帐篷的那一刻,白宇有些恍惚,不仅呼吸在一瞬间冻住,而且像是一觉醒来穿越到南极,360度视野里只有蓝白色构成的一片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在这里才会意识到宇宙之大,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尘埃,会不自觉忘却很多烦恼。”
探险的经历不断磨砺着白宇的毅力。“我见过太多人,身体强壮,装备精良,但却因为吃不了苦而轻言放弃,也见过看上去很文弱消瘦的姑娘,背着60升的包,独自徒步完川藏线。”白宇说,无论骑车还是徒步,都不是竞技,需要挑战并克服的,只是你自己。
580天的旅行结束后,白宇回到原来的公司继续做“程序猿”,过着朝十晚八的生活。像很多长期旅行者都会犯的后遗症,他回到北京后的3个月都处于轻微抑郁状态,每天被动地工作。他会经常在公司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一是为了找回心脏强烈搏动的感觉,二是锻炼身体,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白宇觉得探险旅行是件很私人的事,这或许可以成为他的事业,但并不想职业化。“目前我的工作压力不大,且收入足够支撑自己做喜欢的事情,一旦接受商业赞助,担心会改变旅行的性质。”白宇还未婚,他希望将来的另一半也是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好奇的人。
那辆4次陪着他进藏的捷安特山地车一直放在铁人家里,白宇计划2017年骑着它走另外一条阿里中线,之后,可能会到格鲁吉亚和巴基斯坦徒步。此外,他还准备探索出一些新的路线,“中国西部这么辽阔,很多地方应该还没被发现”。
有人问白宇何必要如此折腾自己,他回答说,其实就是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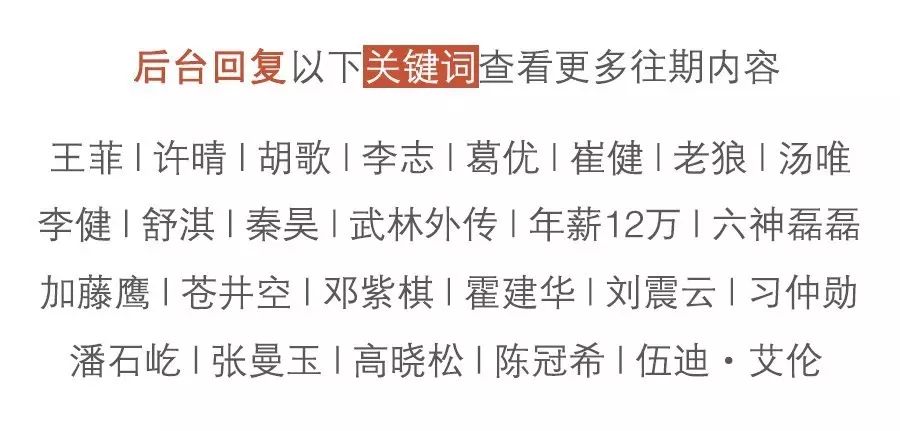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2期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