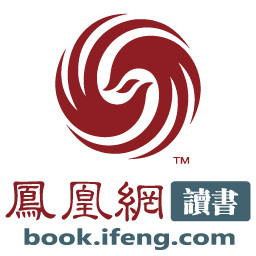松林夜宴图(节选)
▢ 孙频
一
她后来想,一切也许可以从白虎山说起。
所有的山和所有的河都是早已被命名好的。就像脚下这座山,癞秃、干渴、褶皱、独立千年而不能成说。它有一个威风凛凛但已苍老到两千岁的名字:白虎山。
据说西秦首都勇士城两千年前就曾在这山脚下,都城四面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命名四座山,白虎山在西,故名。对应五行之金,四季之秋,六部之刑部。从白虎山再往南便是祁连山余脉。两千年里这里曾有过无数边境之战,灭国之战,屠城之战。后来又几成流放之地,来过各朝的苦役。就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来过一批被城里遣送过来垦荒改造的右派,听放羊老汉说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文化人。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像那些古代的战士和各朝的苦役一样,没能返回家乡,留在了白虎山上,最终被黄沙掩埋了起来。
有时候大风卷过之处,就可以看到埋在黄沙之下的累累白骨,有两千年前的,有几百年前的,有几十年前的,早已经分辨不出老幼。新旧的白骨一簇一簇挤在一起,仿佛是刚刚从黄沙之下唤醒的蚌珠。有些暴露在黄沙外面的头骨安静地睁着两个黑洞,看着西部冰蓝色的天空。皮球一样滚来滚去的头骨被住在附近的小孩子们当玩具捡起来垒在一起,垒成了一座座七层宝塔,远看上去如同一片壮观的塔林。风从一个头颅的眼窝钻进去,像条无骨的蛇一样,再从另一个头颅的眼窝中爬出来。这些头骨宝塔静静地诡异地矗立在白虎山的某个山包上,等待着与爬到山顶来玩的大学生们不期而遇的那个瞬间。
山下有座师范学院,就建在两千年前的勇士城遗骸之上。不知是因为兰州城太过狭长还是因为这学校实在不被待见,青城、金崖、榆中,沿着黄河一路放逐,竟被赶到了这白虎山下。师院的学生们平素的娱乐只有两种,一种是骑着自行车骑十里山路去一个军用机场看飞机,另一种就是爬上白虎山看落日。
十里山路看不到人,看不到村庄,看不到树木,只有绵延不绝天荒地老的黄土沟崖。学生们骑着自行车,吃力地扭着屁股爬山路,一路下来裤子和臀部几欲摩擦起火。在山路上爬着爬着忽然就会有一种身处宇宙洪荒的无力感和庄重感。开天辟地,天地玄黄,日月盈昃,人走在其中如舟行海上,随时会被这无边的黄土吞没,随时会在这坚固如铁的时间里消散成灰。
偶尔会在半路上碰到一个卖苹果的农妇,一点水红色的围巾尖利地刺破纵横的黄土,农妇守着一箩筐木讷憨厚的花牛苹果蹲在路边,不知打算要卖给谁,倒好像看死了他们一定会打这里经过。有时候学生们果真会停下买苹果,仿佛这农妇是他们在宇宙间遇到的唯一人类,连丑笨的花牛苹果也连带着成了这山中的珍禽异兽。下山坡的时候,自行车容易掉链子,刹不住闸,那就索性让自己连人带车地向路边的一堆沙丘撞去,脱缰的自行车驮着一坨惊恐万状的肉,像截失控的火车车厢一样轰隆隆驶向沙丘。车轮稳稳插进沙丘,人则被高高弹起来,若是男生,裤裆里的东西差点被这一弹剪得一点不剩。
终于骑到了机场,军用机场不让随便出入,守在门口的哨兵如果见是女生就多看几眼,如果见只是男生,就依旧泥塑一样挡在门口,目光空洞地看着远处的栖云山。学生们只能站在墙外,仰脸数着起起落落的大小飞机,绿色的飞机像一大群候鸟呼啦啦起飞,结伴从他们头顶盘旋而过,往另一种季节里投奔而去。
直到读完四年大学,这个学院的学生都是看到的天上的飞机比地上的汽车多,竟以为人世间本来就这样。
再或者,在黄昏时分爬上白虎山看落日。李佳音就经常在落日熔金的黄昏带上自己的几个学生们爬上白虎山画落日 。李佳音是一九九五年被分配到这所学校的美术系来当老师的。甘肃榆中人,在三江汇聚的甬城读完了美院,然后,毕业时又被分回了原籍。当她几年前再次回到白虎山下的时候,母亲还有几分不高兴,说,你姥爷活着时就想着你就留到南边了,回来做撒呢?南边到底比这个搭搭干散,把书念上又回来做了个撒沙。她有气无力地说,不服从分配留在南方就连户口都没有了,也没有了工作。听说从明年开始国家就不包大学生的分配了,到时候自己找工作还不定能找到什么样的。我们是被包分配的最后一批了,总得抓住这个机会。
她心里却时刻为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而感到羞愧,多年以后她才想明白,是她身上那种生来与俱的稳妥使她无法自信。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外公执意要教她画画,就时常表现出对她的失望。他总是对她说,侬晓得什么是艺术家,就是侬要去追求那些美而徒劳的东西,只要侬是真的喜欢,就不要讲画画有没有用。外公年轻时候是个画家,曾留学贝桑松美术学院学油画,浙江余姚人。他是几十年前被遣送到白虎山改造的那批右派劳改犯中的一员。几年的垦荒改造结束后就地落户,没有再回余姚,他和一个年长他几岁的当地女人结了婚,那女人身体不好,后来就生病去世了。他们有一个孩子,就是李佳音的母亲。李佳音的母亲因为成分不好,从小被同学们歧视,上完小学就没有再上过学,早早嫁给了当地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就是李佳音的父亲。
外公高瘦清隽,在西北多年仍然没有改掉浙江口音,他对榆中方言里把“喝水”叫成“喝蜚”,“吃吧”说成“吃撒”永远深恶痛绝。他坚持要把“母亲”叫“阿姆”,把“晚上”叫“夜到”。李佳音小的时候就曾问过外公,你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南方来到白虎山呢?外公说,因为吾会画画。李佳音说,为什么会画画就要来白虎山呢?外公说,因为会画画的人都是小居(小孩)。
过了几年李佳音又问他,你们那时候在白虎山上每天都做什么呢?他说,做交观多(许多)事情,劳动啊吃饭啊种粮啊割草啊养猪啊,啥西(什么)都做。阿拉连住的屋子都是自己做的,就在黄土坡上挖个月牙形的洞,洞口小,但里面可以挖大些也可以挖小些,还可以在旁边再挖个套间,套间还可以再套一间,反正阿拉想怎么住就怎么给自己挖。那窑里交观(特别)宽敞,比现在榆中的平房大多了,阿拉可以横着睡也可以竖着睡。吃的东西也交观多啊,青稞炒面、玉米面团子、洋芋角子、浆水面、灰豆子、糜面疙瘩,阿拉在山上给自家种了很多玉米和土豆,阿拉甚至还种过百合和玫瑰。百合的根是可以吃的,囡部部(又甜又软),侬晓得百合花是白色的,其实也有橘色的。玫瑰花也可以吃,侬晓得甘肃这一带从明朝就开始种玫瑰了,最好的玫瑰叫苦水玫瑰。把玫瑰花瓣采下来用白糖腌渍成玫瑰酱,或者包在火烧里做成玫瑰饼,咬一口那真真花香扑鼻。夏天的时候,山上诶到各处(到处)都是阿拉种的玫瑰和百合,红白相间,云蒸霞蔚,登样(好看)极了。就是在六零年那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阿拉也能找到各种野菜吃。和吾住在一个窑里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生物学家,另一个是个音乐家。阿拉干什么都在一起,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有一口吃的都要三个人分了吃。生物学家带着阿拉在山上找龙葵、曼陀罗、苘麻、刺蓟、虎尾草、牛筋草、石灰菜、马唐、鱧肠、水稗,还有一种叫马屁泡的菌子,小晨光(小时候)是白色的,但当长大到不能再大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炸裂,喷出黑色的烟雾,好玩得很。里面黑色的粉末是可以止血消炎的,阿拉都把它当药来用。那个音乐家则每天在落日时分蹲在窑口用口琴给阿拉吹《红河谷》和《三套车》,快要落山的夕阳又大又红,把满天的云彩都染得血红,像在天空里烧了一把大火。
李佳音又问,那个生物学家和那个音乐家后来都去哪了?
外公平平静静地看着远处,声音也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飘过来的,侬晓得,阿拉真的像亲兄弟一样……佢拉后来都回老家了。吾留了佢拉的地址,佢拉一个叫周在堂,是江苏无锡人,一个叫李书平,是湖南岳阳人。吾记得很清楚,都是南方人,又文气又礼貌。自从佢拉回家之后,吾每年都要给佢拉寄去西北的百合干、牦牛干、苦水玫瑰、柳花,年年过年都要寄的,没有一年拉下的。二十年了,侬晓得?吾都寄了二十年了。
虽然从小给她讲白虎山上的故事,外公却从不让她到那座山上玩,于是白虎山在她眼里变得日益神秘,如笼着一层蓝色的大雾。在李佳音记忆中,外公只对两件事感兴趣,吃和画画。李佳音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她画画,他喜欢给她讲格列科、提香、丁托莱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塞尚、伦勃朗。他最崇尚的画家是伦勃朗,他保存着一本破旧的伦勃朗画册,他喜欢把里面那张叫《夜巡》的画一遍一遍指给她看。有时候明明是指给她看的,他自己却坐在那里看得满脸是泪。他说,侬晓得伦勃朗从画完这张画就破产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张画有多么好。后来不久他就死了,才五十多岁啊。可是吾每次看到这张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人生不管怎样虚空和荒诞,某些东西仍然会到来,会发生。
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吃感兴趣。有一天黄昏他带着她去榆中县的十字街口买豆腐脑和麻叶做晚饭,雪白的豆腐脑盛在一口钢筋锅里,上面洒着绿色的韭菜花和红色的辣椒油,他一边走一边不停闻着锅盖下散发出的香味。拐过一个弯之后他站住了,对她说,阿拉还是先把豆腐脑吃完了再回去吧。然后不等她说话他就捧起钢筋锅,哧溜哧溜只两口,就把一锅滚烫的豆腐脑都倒进自己肚子里去了。吃完之后好像又有点不相信是自己吃完的,他狐疑地羞愧地看着那口空锅,自言自语道,吾吃的?不能吧?却久久不敢看她一眼。 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她开始为他感到羞耻。她吵着要回家,生怕有人会看到他们。他明白了她的意图,他捧着那口空锅忽然抬起头,肃穆地对她说,侬是不是觉得吾挺可怕?“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那个和吾在白虎山住过的音乐家曾经告诉吾,这是前苏联的一个叫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家说过的话。他说肖斯塔科维奇一辈子都在等待一个枪决。
后来当他变得越来越老之后,他对画画的兴趣开始越来越小,对吃的兴趣却越来越浓烈越来越顽固,这兴趣长在他身上,像身体上发育出了一只硕大无比的畸形器官,简直要比四肢比脑袋都要显眼。
他越老便越爱惜自己的身体。由于睡不着觉,他每天早晨天还黑着就在炕上开始做一套保健操,横着做完竖着做。起来后按摩太阳穴,干洗脸,然后再出去倒着走半个小时。每天早上要雷打不动地吃三颗红枣三颗核桃,晚上睡前要风雨无阻地喝三杯枸杞泡的小酒。每天都要午睡,一到那个时间他就脱光衣服,头上裹上毛巾是怕受风寒,盖上被子午睡一个小时。午睡过后要喝一碗小米汤去火,然后在屋子里开始画画。他本是画油画的,到后来却只是拿毛笔随意在纸上涂抹,没有人能看懂他画的到底是什么。他画好一幅就往墙上挂一幅,只给自己看。时间一长,墙上挂得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墨挂满了屋子,挽联似的青森阴凉。画挂多了她才渐渐看出来,那画上画的密密麻麻的好像全是人,各种形态的小人或坐或站或睡。看上去有点像日本的佛教画《甘露图轴》,又有点像朝鲜十九世纪的《十王图》,还有点像密密麻麻罗列在纸上的亡灵的墓碑。
更老了些之后,他看见邻居的小孩子喝牛奶,都要过去问小孩,侬一天要喝几袋牛奶啊?小孩想捉弄老头,便伸出七个指头来。他就当真了,侬喝七袋啊,那吾差远了,吾每天才喝一袋。于是早晨喝中午喝晚上喝,咽不下去了就往里灌,每天拼了命也要喝够七袋牛奶。
有时候李佳音的母亲赶集买了些饼干坚果之类回来,他见了就先在自己的枕头下面藏一部分,睡觉前躲在被子里偷着吃,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一醒来又从枕头下面摸出来接着吃。结果被子里的各种食物碎屑多得能养活两窝老鼠。就是这样,他还是一天比一天老下去了,耳朵已经和摆设没有两样了。别人说什么他其实是一句都听不见的,只是看见人家笑了他就跟着笑,因为慢了半拍,别人笑完了他还没笑完。别人问他笑什么,他就说,你们不是在笑吗?因为听不见,只能看见别人的嘴在动,动来动去看着都一样,他大约也有点烦,所以后来干脆就见了谁都没有表情,泥塑似的一张脸上挂满深浅的褶子。有时候看见邻居家吃什么了,回去就和李佳音的母亲闹着要吃,阿拉也吃那个吧。在街上看见小孩们口里吃着什么他会上去说,小歪(小男孩)给爷爷吃点,让爷爷尝一尝,就尝一点,就一点。吓得邻居的小孩子们一见了他就跑,像见了大灰狼一样。
他看起来内里总是很渴,很饿,很空,无论扔进去多少东西都填不满,都能马上听见空荡荡的回声。好像他患上了一种奇特的类似于饕餮的疾病。然而就在那些刚刚吞咽下食物的清醒瞬间里,他仍然会哆哆嗦嗦地拉住她的手,催促她去看伦勃朗的画册,他说,侬一定去看他那些无与伦比的光线,伦勃朗光线,真正的艺术家啊。就是画不出,侬也总可以去向往的。人其实就是在活那一点向往。
外公是在她去甬城读美院的第一学期去世的。等她寒假回到家里才知道,外公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外公曾住过的房间已经被母亲清理过了,墙上挂的那些阴森森的满是小人的画都被取下焚烧掉了,取代它们的是一张外公的遗像。年老的外公站在一种枯瘦冷硬的黑白光线里,嘴唇紧抿,双目凹陷,正像一道谜一样无声无息地看着她。
她问母亲,外公走前痛苦不?母亲说,就是受罪了,你木见他到后来瓜(傻)滴,人都召不住了,裤子掉了都不知道个提。她问外公给她留下什么话没有。母亲说没有,只留下几幅画,他神志清醒时就嘱咐过她,一定要把一幅画和一本画册留给李佳音。那几幅画有的用色粗粝浓烈,有的雅致如青绿山水。有一幅画里是血一样的大片花丛,好像昨夜西风微雨刚罢,满地宫锦残红,飞絮濛濛,有三个长发白衣的老者正在花下品茗下棋。另一幅是寒食前后,杏花如雪,三个白衣老者正赏花归来,满纸是平林新月人归后的清旷。留给她的那幅画的叫《松林夜宴图》,画中充满了北宋李成的寒林气质,荒原空旷,月夜松涛。看起来时节应是冬夜,松间与林下有积雪在月下闪着寒光,此处大约得王詵笔法,在树冠处敷上了厚厚的银粉,便尽得夜雪之肌质。松下有三个白衣老者在煮酒夜饮,其中一个正在听风抚琴,另外两个则醉卧流年。
这幅画看起来和别的山水画不同,有一种奇怪的气质。人物比例被放大,画中那个抚琴的老者正看着画外,脸上有一种似笑非笑的神秘表情,正欲说还休。她与那个画中的老者对视了很久,画的右下角没有标注日期,看不出是他什么时候画的。她一时想不明白,外公为何一定要把这样一幅没有一个字的山水画留给她做遗物。
后来她就一直都把这幅画带在身边,在甬城读美院的时候她曾拿出来给罗梵看过,她问罗梵在画中能看到什么,罗梵看后说,山水倒没有出彩之处,不算上乘之作,只是画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不安气息,很紧张,近似于恐惧。像有什么事情即将要发生之前的那种可怕平静。
外公留给她的那本画册是伦勃朗的自画像册。伦勃朗从十八岁的少年开始画自己,每年画一幅,里面有三十岁如日中天的伦勃朗,四十岁国王一般骄傲的伦勃朗,五十四岁身材臃肿缠着头巾,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的伦勃朗。他越是往后用色越厚重,到了后来,画中厚厚的色彩看上去像是铜铸的,闪着金属的光泽。她翻到了最后一幅自画像,这是伦勃朗生前给自己画的最后一幅画像。整幅画中用的是夺目的金属色光线,人物好似铜版浮雕。画中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落魄老人,戴着一顶旧帽子,满脸皱纹,眯起眼睛正向画外面看着。他苍老的脸上有一丝非常诡异的笑容。她想到了外公的《松林夜宴图》里弹琴老者的表情,手猛地一抖,忽然觉得二者之间有一种奇怪的相似。
她第一次爬上白虎山,是在外公去世之后的那个冬天。几天前的一场薄雪已经基本化尽,只有山脊的背阴处还有斑驳的雪迹。她一站在那里就愣住了,满眼只有无边的黄沙和大小的砾石,枯死的沙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偶尔见一棵低矮的沙枣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满身的荆棘,几颗早已风干的沙枣血滴一样挂在枝头。十里黄沙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看不到一只飞鸟。一扭头却发现几步之外有一只寂寞的头骨正趴在黄沙中与她静静对视着。她这时候才发现,黄沙之下,残雪之中,到处是白骨。有的像树枝一样露在外面一截,有的像发芽的种子一样只露出一点点,还有的完全赤裸在风中,闪烁着一种类似于银色的可怕光泽。她一个人站在白虎山上打着寒颤却迟迟不肯离去,这时候冬日的太阳已经开始落山,夕阳里的白虎山看上去辉煌壮丽而充满诡异之气。
来年暑假的时候她再次独自爬上白虎山,仍然是满眼的黄沙白骨,仍然几乎看不到一丝绿色,偶尔有束灰绿色的沙蓬也是血溶于水,掉进黄沙中立刻就消散不见了。玫瑰与百合听起来像这十里黄沙的一个千年大梦,而龙葵、曼陀罗、苘麻、刺蓟、虎尾草、牛筋草、石灰菜、马唐、鱧肠、水稗这些植物的名字则像一艘早已沉入海底的沉船,锈迹斑斑,长满牡蛎,只见其中草影幢幢。她独自在山上走了很远,似乎只要一直走下去就可以走进外公最后的那几张画里去。玫瑰、松林、杏花、残月。品茗下棋、弹琴长啸、青梅煮酒。她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唯恐找不到痕迹,又唯恐真的找到什么。到最后她只在陡峭的黄土崖上找到一排又一排的土窝。那都不能算土窑,只能算土窝,因为窄小得不像人住过的,而且没有门窗,只有赤裸的洞口在大地之上隐秘开放。就像已经知道里面蛰伏着什么怪物一样,她甚至不敢往里再多看一眼,只是坐在黄土上,大口大口喘气。
从美院毕业被分回榆中的那个夏天,她又一个人来到白虎山上。西部的落日硕大而金碧辉煌,仿佛是从一种无生命的深渊里长出来的凶猛植物,只是不停分泌出金色的光线,再把这箭簇一样的光线掷向每一棵树的生,每一道黄色土地的生,每一道沟壑的生,每一道嶙峋峡谷的生。它像一种无生命的生命,蛮横有力,强暴万物。白虎山上的黄土吸饱了这样浓烈凶悍的阳光,变得通体金黄剔透,天上地下,这么大规模这么浩瀚的金色汇聚在一起,天真单纯而扫荡一切。无论是曾经在那三江汇聚的甬城,还是后来在北京深秋的银杏林中,她都再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大规模的金黄色。黄沙之下露出的白骨像埋在这土地里的种子,不知道将要长出怎样奇异的人形植物。她坐在沙丘上,眼看着自己如旷野里的一座佛陀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色。
山腰上有个放羊的老汉正在唱河州花儿,“天下的黄河往南淌,水大着淹了个享堂。远路上有我的好心肠,看去是没有个落脚的地方。”满山只听见古老悠远的花儿,看不到人,也看不到羊。又过了一会儿,一只领头的黑色大山羊出现在她的面前,接着一群白色的绵羊跟着黑山羊出现了,再接着,绵羊的最后面跟着一个放羊的老汉,甩着皮鞭,嘴里正唱着花儿。
羊群低头啃着沙蓬草,黑山羊顶着一对大角在旁边看守着它们。她和放羊老汉坐在沙丘上聊天。她说,老伯今年有多大了?老汉说,五十四咧,就是看着像个老扎扎。她说,才五十四,一点不老,那还是叫你叔吧。老汉高兴了,说,尕女子是做啥子滴?她说,我是这山下师院的老师。老汉惊叹,大学滴老师?满服(佩服)滴很撒。她说,叔,这山上多年以前是不是还种过玫瑰和百合?老汉嘎嘎大笑,尕娃是梦见了撒?止(这)簸(白)虎山上啥子都不能长,从古只能打仗。她说,叔,你知道这山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骨头,是人的还是动物的?老汉摇头叹气,你是尕娃不知道,我九岁上就在止山上放羊,啥子事没见过?古代打仗当兵的愣怂们都死在止里,我十六七岁还是个崭页子(小伙子)滴时候,很多文化人也被送到了止山上改造,一个个簸生生(白生生)滴,都长得心疼滴很。就住在止山上挖的土窝子里,每日头垦荒种粮,尕娃看止山上还能长下个粮食?啥都不长。那时候止里人多滴很哪,后头两年闹饥荒莫有吃滴就饿死了很多人,就地埋了。啧啧,席嘛吓人,文化人饿了也是逮到啥子吃啥子,老夫子(老鼠),蝼蛄子,蛐蛐儿。为保命啥子都能咽下去,人饿了都一个式子(样子),就是心里得过个坎坎子。席嘛吓人撒。
放羊老汉赶着羊群都离开很久了,李佳音还独自坐在那座沙丘上。她觉得很冷很饿,却是一步都动不了,也不想动,她只想天荒地老地坐在这里。直到天边的晚霞彻底燃尽,一轮巨大惨白的月亮像座宫殿一样,轰隆隆从白虎山下升了起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离月亮那么近,好像只要一步就可以跨进去。
接下来的几天,李佳音在整理外公的遗物时,翻出了厚厚一沓包裹单。所有的包裹单都是外公寄给两个人的,周在堂和李书平,一年又一年的包裹单,看上面的时间,前后大概持续了二十年。奇怪的是,所有的包裹单都是被邮局退回来的,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一年又一年。
这个暑假,李佳音翻遍了榆中县志,地方志,到县文化馆找当年关于白虎山农场的资料,但什么记录都没有。她又逢人便打听,最后七拐八拐才打听到了一个当年落户在榆中县夏官营镇的老右派。那是个一条腿已经不能动弹的老人,出不了门。她骑着自行车去了夏官营镇,找到这老人,向他打听当年在农场可认识宋醒石。老人拄着拐杖坐在沙枣树下,想了半天说,是二队的,浙江人吧,是个画家。她再问更多,他便不知道了,他面无表情地说,那时候还能干吗?把人饿的,每天想的就一件事,吃。然后他再次打住,又不愿往下说了。一直磨蹭到最后她都要走了,他忽然神情古怪地说了一句话,二队那十几个人,最后活下来的就你姥爷一个人。她一惊,那他的那两个同伴呢,他们关系很好,干什么都在一起。一个叫周在堂,是江苏无锡人,一个叫李书平,是湖南岳阳人。他们后来都回自己家乡了啊。老人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群山之上的流云,只平平地说了一句,错不了,二队就活下来你姥爷一个人。然后便再不开口。
她骑车回榆中县的路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月亮再次爬了起来,悬在那里,俯瞰人世。
“月光这么白,北方的大雪都没有这么固执,这么凶狠。没有把一切事物都撂倒的决心,我穿得更厚,才敢从月光里穿过。”

作家孙频
(书评)
向历史与文学深处推进
▢ 金赫楠
《松林夜宴图》触碰到一个颇具难度的大命题:青年写作要如何面对、理解和表达祖辈、父辈所切身经历过的历史之殇和切身之痛?怎样书写历史大事件与日常当下的青年人生之间那种密切的内在关联?
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80后”作家对进一步抵达历史与文学深处的野心、能力与信心。对自己之前习惯和依赖的叙事策略,虽然不能完全摆脱,但是明显克制,叙事节奏和叙事情感都很克制。
孙频小说的高辨识度,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作者用笔之“狠”,“以生猛酷烈作为风格辨识的孙频是年轻一代写作者中的异数”,其作品不时引发讨论甚至争论的,恰是文本中反复贯穿着的一些意象,比如罪与罚、孤独与恐惧,比如身心的耻辱与疼痛。而这些正是孙频小说一直以来习惯、依赖甚至迷恋的叙事策略--“极端情境下的极端人格”塑造或拷问,以此去表达作者眼中的时代和人性图景,确立自己高度风格化的文本辨识度。更早一些时候,孙频被称为“内化的张爱玲”,但其实从题材、人物到语言风格,孙频与张爱玲显然并无明显相似之处,大概就是文本基调和底色中的一腔苍冷和凛冽有几分共通。而孙频笔下世事人心的极致气息,较之张爱玲似乎还更彻底、更惨烈些。
与这种叙事策略相得益彰的是孙频强大的心理描摹能力和叙事语言的丰茂、精准,她有着出入其中精彩讲述情节与故事的能力,繁复而腾挪自如的叙事语调,对人物幽微心理的精准洞悉与淋漓表达。作为一个高产作家,孙频小说的质与量使她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青年写作者之一,更是“80后”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与此同时,大概因为过于依赖那种极致化的推进情节与塑造人物的叙事策略,她的写作中也明显出现了同质化、自我重复的问题。基于上述关于孙频小说的大致印象与判断,喜爱、疑问和期待,我读到了孙频刚刚出版的小说集《松林夜宴图》,收有作者最近的3部中篇小说《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和《万兽之夜》。这3篇小说中,我发现孙频对于自己写作中的问题是自知而自省的,显然,她在尝试改变和挑战,同时亦有坚持和固执。
我最喜欢的是《松林夜宴图》,小说集亦以此命名。这是孙频近来最具探索性的作品,呈现出作者在自己写作惯性上的突破意识和能力;同时,《松林夜宴图》也是近年来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于文学谱系中有来处、有根柢,且又有开拓。小说以“饥饿”这样一个新时期以来文学叙事中常常使用的状态意象,打开了李佳音祖孙两代人的心理创伤。孙频耐心地描摹着外公肠胃与口舌间病态的饥饿感,李佳音精神、情感甚至身体上扭曲的饥饿感,但作者更有兴趣探究与表达的显然是创伤背后参与制造它的时代、历史、社会因子。这篇小说仍然携带着孙频一贯“极端境地下极端性格塑造”的叙事惯性,但在这篇的写作中,她努力为这“极端”安妥了可信的、有历史和人性纵深感的因由与路径。 《松林夜宴图》触碰到一个颇具难度的大命题:青年写作要如何面对、理解和表达祖辈、父辈所切身经历过的历史之殇和切身之痛?怎样书写历史大事件与日常当下的青年人生之间那种密切的内在关联?
《松林夜宴图》之前,同为“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所得到的好评与热切关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于这个大命题的冷峻思考和诚挚表达。《松林夜宴图》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巧妙之处在于,在关于一幅画作的鉴赏和解密过程里,李佳音与外公各自的时代底色和历史境遇,各自隐秘的心事、不安与哀痛,相互打量和碰撞。“她能如此清晰地看到外公活在世上每一天的痛苦和恐惧,他对她想说的太多,她明白,她都明白。她看到了他身上最恐怖的那一面的同时,更愿意像他的祖母一样,泪流满面地抱紧他……我们会忘记的,我们终究还是人类”--小说的结尾处,这幅画里所埋藏的外公的隐秘心事,作者与人物都是看破却不说破的。《松林夜宴图》中,孙频安排她的人物相互宽恕,人物与历史、时代和解,且这种宽恕与和解是可信、有说服力的。而这在孙频之前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80后”作家对进一步抵达历史与文学深处的野心、能力与信心。对自己之前习惯和依赖的叙事策略,虽然不能完全摆脱,但是明显克制,叙事节奏和叙事情感都很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