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个女生,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呢?”
刚转行做风光摄影师时,25岁的姚璐常会被人问到这个问题,那正是对世界还充满好奇又具备独自旅行能力的年纪。每当她坐着硬座火车穿行在中国大地,徒步、扎营,举着相机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景色时,无论在中国的西北、东北还是西南,哪怕和其他摄影师站在同一个观景台,也常有一些陌生男摄影师走来,直接“指导”她如何拍摄。
那几年,姚璐总要面对这些提问和指点,这也让刚准备好拥抱世界的她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所隐含的限制,因此对性别偏见产生了兴趣。
摊开世界地图,中东吸引了姚璐的注意。那时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东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约旦、伊朗、叙利亚都位列倒数。在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度,女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的人生多大程度受制于自身的性别?而在更长的时间里,姚璐对这些中东地名的印象来自于国际新闻中的战争和暴乱,这令她一直好奇,在战乱地区,人们如何维持一种日常的生活?
2016到2020年,姚璐去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为了深度感受当地的寻常生活,她采用了“沙发客”这一旅行方式,住进了31个陌生的中东人的家里。在这四年里,姚璐常常受制于邻国关系和签证互斥政策,也受制于战争,不得不频繁调整计划。在五次造访中东的旅行中,三度以为自己的旅程结束了。
在中东,她遇上了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第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圣诞节,也赶上了沙特阿拉伯的变革期,在沙特的大街上亲眼看见了首批女司机。尽管在中东旅行中,姚璐深度交往和交谈的人都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较开明的中产家庭,都能讲英语,但在这些相处中她看到了另一面的中东。开始写作这段经历时,姚璐自己也经历了因新冠疫情而无法出门的三年。在《看不见的中东》出版的2024年,整个世界似乎在重新相连。她也再次踏上新的旅程。
姚璐的中东之旅始于2016年7月14日。那天,她坐上了飞往伊朗首都的班机。在德黑兰,她叩响了第一位“沙发主”的家门。
以下是姚璐的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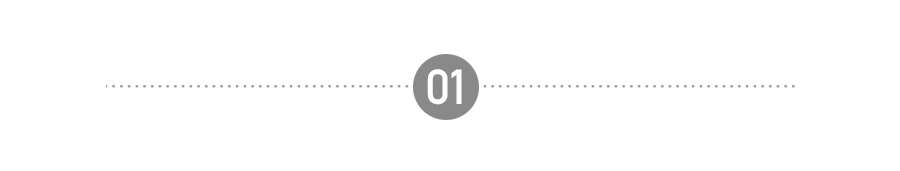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头发的颜色是她的自由”
决定去中东后,我选的第一站是离中国比较近、在中东相对安全的伊朗。之前我对伊朗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新闻里的伊朗看起来宗教气息浓郁、社会氛围保守。只要是女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在伊朗都要遵循当地的着装规范,穿长款衣服、戴头巾。我在抵达前很紧张,害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结果一到伊朗首都德黑兰“沙发主”的家里,那个女孩一开门,我就看到她一头鲜红的头发。
我当时很震惊,哪怕我在上海生活,当时都没见到有人染颜色这么夸张的头发。那是我第一次在动画片之外看到真人有这么鲜艳的红头发。正是因为她要戴头巾,才会在头巾之下染这么夸张的头发颜色,因为头发的颜色是她的自由。
第二天,我在德黑兰坐公交车,因为售货厅没开门,我没买到票,公交车师傅直接招手让我上来,也不肯收我钱。我上车后,坐在前排的伊朗女生立刻特别兴奋地回头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中国人。她兴奋地坐到我边上,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之前出国旅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热情友好、渴望交流的人。
去过伊朗的人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这个国家跟我们预想的非常不一样。伊朗对人的规定和限制有很多,也有宗教警察在街上盯着,但我在这里遇到的人非常乐于告诉外国人他们如何反抗这些规定,特别渴望跟你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
沙发主的哥哥很详细地告诉我,他在家怎么用葡萄一步步酿出葡萄酒。以及,因为美国的制裁,伊朗市面上看不到美国电影,但年轻人会通过地下渠道购买资源,你选好想看的电影,让老板给你下载,一个U盘大概有100部电影。他们
(尤其是年轻人)
也非常想告诉外国人,人们在伊朗拥有一种秘密的生活。他们确实颠覆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在伊朗旅行时,我经常遇到很多陌生人来跟我聊天。在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上,曾经出现很多人排长队来跟我聊天的情况。一个女生在外旅行,其实挺容易被人搭话的,大部分问题还是传统问题,比如你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你这次去了哪些地方?
但是,我在伊朗遇到的这些交流和聊天,都带着明确的目的。他们知道自己想跟我聊什么,他们想跟我聊信仰、聊美国。这明显是他们平常一直思考的问题,突然见到一个老外,就想把平时的思考跟我交流。这个是伊朗人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仅渴望交流,而且特别有想法,一开口就是很深度的交谈。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从伊朗离开后,对伊朗还是非常感兴趣。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哲学思辨很强的国家,他们有非常优秀的思辨传统,有悠久的诗歌、文学和艺术的传统。去完伊朗之后,我才会理解为什么伊朗电影的批判性这么强。
在伊朗旅行的过程中,我遇到的第一位沙发主阿明跟我讲她家三代人的情况,她外婆、妈妈跟她们三代人的权利是一代不如一代。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政府奉行的是比较世俗化的政策,社会也是比较开放、世俗化的。如果看那个时候的照片,你会发现当时伊朗女人的穿着极为西化,女性可以不戴头巾。伊斯兰革命之后就发生了社会大变革,变成了如今的保守、传统、宗教化的现状。
因为我成长在一个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时代,我长时间都认为未来肯定滚滚向前,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开放程度,一定是越来越好。但阿明家里三代人的经历让我看到历史未必是越来越好,它可能是会进一步、退两步,然后再进半步,再退一步,在这样的进进退退的动荡中,人的命运就因此发生着变化和影响。
伊朗作为我整个中东之旅的第一站,完全颠覆了我过去的想象,这让我很激动,因为我对中东的很多刻板印象可能是不对的,对接下来的中东行程就会非常期待。

▲伊朗政府禁止在公共场所演奏音乐,但每逢周五 (伊朗一周唯一的休息日) 夜晚,就有男青年带着吉他到三十三孔桥下弹唱,琴声和歌声在桥洞中回荡,过路人安静地坐下聆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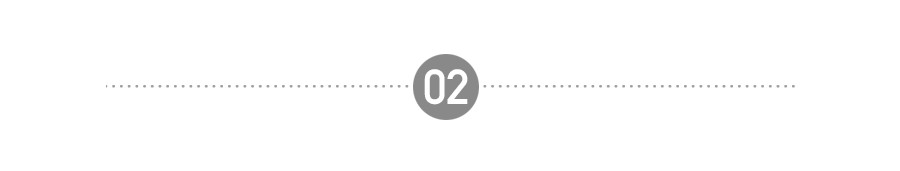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迷恋夜晚
在我小时候,“巴格达”这个地名几乎等同于“爆炸”。因为只要这个地名出现在电视新闻,就是恐怖袭击和爆炸事件,那些新闻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就是轰炸镜头中的浓烟。2018年6月,我在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飞机上还是很紧张,尽管我已经去了伊朗、黎巴嫩、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埃及。伊拉克对我来说很神秘,上网搜资料,几乎一片空白。
我到巴格达的第一天晚上,当地的沙发主要带我去逛夜市。听到“逛夜市”,我就已经不想去了,因为人群密集的地方就是恐怖袭击虎视眈眈的地方。但沙发主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他说“我们去逛逛”,边说边往自己的手枪里塞子弹。
到了夜市,我发现这跟国内的夜市没什么区别,很多大排档卖饮料、烧烤,网吧里有青少年在玩游戏。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迪拜,第二天晚上我就在巴格达的大排档里吃烧烤、喝红茶,跟几个伊拉克人一起闲聊,感觉挺魔幻的。街上的人很多,人们也很放松,但街上几乎只有男人,基本看不到女人,极少的女人都是跟家人一块出门的。
伊拉克的饮食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没有规律的饭点,饿了就吃,不饿就不吃,而且经常是大半夜两点钟不睡觉,一家人像正式吃饭一样围着吃甜品,为了招待我,每次都特意给我一大缸子甜品,我每天凌晨就跟他们一块吃甜品。在伊拉克的那一个月其实很累,我要出门拍照、跟本地人交谈,应对检查站对我的检查,但那个月我还长胖了,就是因为每天晚上吃得非常多、非常甜。
一开始,我也觉得全家人凌晨一起大吃甜品是很荒诞的事,后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对夜晚的迷恋与当地气候、每天的祷告有关。
那里的阳光跟我们这儿的阳光质感不一样,这边的阳光给人温暖、希望的感受,但在伊拉克、沙特这种沙漠气候的国家,阳光像是要吸走所有的生命力,我出门10分钟就会晒到感觉自己的生命被抽干了。那里的人厌恶阳光,人们的很多行动是天黑后才开始。在沙特,每天白天,他们有五次祷告,祷告时几乎所有公共场所关门,所以白天的生活是不连贯的,但整个夜晚是连贯、凉爽的。夜幕降临之后,他们会出门见朋友。周末时,年轻人会整晚不睡觉,跟朋友一起去吃吃喝喝、聊天。夜晚是他们更放松、更舒服的时候,肯定要尽量延长夜晚。
我在伊拉克的那一个月,刚好遇上2018年的世界杯,大部分比赛都是在大排档和酒吧看的。在家看球,只能看文字直播,我在伊拉克住过的所有家庭都不会开电视,因为人们家里的电力有限,空调和电视只能开一个。伊拉克常年战乱,我原本觉得它与其他国家的连接很松散,也比较边缘化。但在看世界杯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也很投入地看我们看的比赛,跟我们一样为进球欢呼,球没进也骂球臭。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没有这么远。
在伊拉克的路上,我常能看到很多车上的战争痕迹,基本上每辆车的车身和玻璃都有被袭击过的裂纹,车的铁皮也被撞得皱皱的。我的沙发主的车的前玻璃就有弹孔。但这边的人都不修车。他们说因为不稳定,修完车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被炸一下,干脆不修了,车能开就行。

▲伊拉克巴格达夜市的棋牌摊位
几个月后,我去了叙利亚。当我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与战争相关的痕迹。大马士革古城里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街边店铺在卖菜、卖鱼、卖水果,卖各种生活用品。但当我去到霍姆斯,情况就变了。一天早上,我出门想闲逛。我住的宾馆在体面的街区,路边店铺还没有开门,四车道的路中央还种了树,我又往前走,穿过两三条街道,在没有任何街景的过渡下,接下来是一整条被炸毁的街道。
我整个人处在一种蒙掉了的状态里,感觉是空空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不知道应该拿什么样的情感去回应。大部分楼房的上层都坍塌,残留下来的一半能看出这栋楼之前是做什么的,住宅、清真寺,还有剩一半的宣礼塔,整个街道都是建筑遗骸。
在叙利亚
(尤其是霍姆斯)
旅行,确实跟在中东其他地方特别不一样,我经常会面对警察和政府官员的盘问,因为霍姆斯是叙利亚内战期间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交战特别激烈的地方,有很多国外的记者采访。我作为一个游客,需要应对很多检查。但当地的平民不是这样想的。街上的人看到我这样的异域面孔很兴奋,特别礼貌地跟我说话,说很高兴看到外国游客到我们国家来了,他们觉得这代表着他们的国家越来越走向正轨。
在叙利亚,大部分人其实都不愿意跟我谈论战争。在大马士革,一个本地朋友对我说,他觉得外界对叙利亚的关注全是战争,大家把战争当成了一个博物馆里被参观的物品,所有人到这边都在问跟战争相关的事情,他希望外界了解到,叙利亚人在战争之外也有生活,“我们也是跟你们一样的人”,也有生活的困扰,也有梦想,也要规划未来。
我去的时候是2018年,战争进行到了第七年。他们已经完全习惯这种状况了,不太会说经历了哪次袭击。袭击完,人没事,学生就要继续去准备期末考了。袭击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个片段、是一个瞬间,不是时刻会发生的事,更多的日常生活其实都是跟我们一样忙学业、生活、工作。他们更想聊在学校里和朋友一起上课,课程什么样,周末去哪里喝咖啡,他们更想分享快乐的、生活层面的事,不太喜欢去谈论那些很沉痛的话题。
我在叙利亚看到,确实全世界的休闲活动都差不多,他们会去听音乐会、看舞台剧,我当时甚至还在大马士革看到“密室逃脱”,2018年时密室逃脱在中国也算是比较新的娱乐方式。后来我反思,为什么我会以为他们没有这些?任何情况下,人活着都需要娱乐、需要音乐、需要体育活动。

▲叙利亚人盛装出席订婚宴,在宴会大厅跳了一晚上的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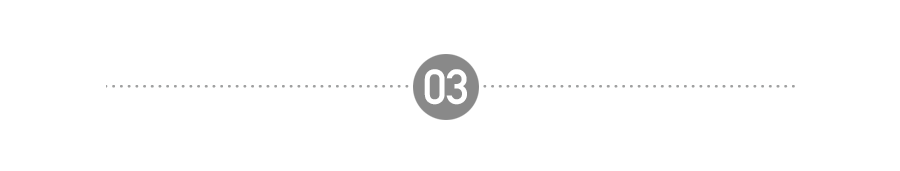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这个世界依然跟以前一样乐于接待你”
在中东,我住进了31个陌生人的家。比起跟人在咖啡馆见面,家是一个更私密的场合,人们在自己家聊天时会更放松。在外面谈论的更多是社会问题,比如国家政治和性别不平等。在家里的夜聊,尤其如果沙发主是一个女孩,她睡床、我睡地铺,会袒露那些更私人的痛苦和不如意。
住在当地人的家中,也能观察到更多细节,我在叙利亚的沙发主是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沙发主的父母。我在贝鲁特的沙发主是一个不爱做饭的27岁女孩,她一个人生活。她刚到黎巴嫩的时候,打两份工来维持生活。她特别坚强勇敢,对社会有很多观察和思考,也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规划。我从贝鲁特离开时,她跟我说她才27岁,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后来,我再到到叙利亚时,她让我去她父母家。去了她父母家,我才知道她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她的父亲有着比较平等的性别观念,认为女孩跟男孩没什么不一样,一直教导四个女儿成为有想法、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也支持尊重女儿们的所有决定。这四个女儿也都被培养出坚强、勇敢和独立的品格。
当整个中东社会对女性都有很大束缚的时候,家庭氛围是很重要的,家庭是一个最好的反抗单位,如果她们的父母可以把手抬高一寸,那她们的生活自由度完全不一样。父亲如果太权威、压迫,小孩子的成长空间就会变小。但如果父亲愿意放一部分权利给女儿的话,女儿就更有可能成长为有想法、有梦想、有力量的人。
在中东,这里的人需要思考在这种传统的伊斯兰教与世俗化之间,要怎么寻找到适应当下的平衡?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两股力量会有一些撕扯。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地方的人都需要去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沙特阿拉伯以前是非常保守的地方,女人出门要穿黑袍、戴面纱,但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赋予了女性更多权利。女人现在能够开车出门,比较先锋的女人已经不穿黑袍、不戴面纱。这个趋势与社会适应全球化的过程有关系 。进步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反复,历史永远是随机性与必然性相伴的,但我相信整个中东一定会往世俗化的大方向去走。
女孩子的一些困惑是相似的,我在伊拉克时,被本地人邀请到他们家吃饭,哥哥的英文不太好,但特别积极地跟我交流,妹妹学的是英国文学,但她不敢跟我对话。每次哥哥说到不会的英文单词,就去问妹妹,妹妹再告诉他,他再很自信地对我说出那个词。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多时候中国女生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自信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从小受到太多贬低和否定,哪怕做得再好,你都会觉得你不够好。但更多的男生受到很多鼓励,他们可以更自信地表达。
很多时候,女生都处在一种“可进可退”的状态中。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把我们往前推一把,说你试试,我在后面支持你,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克服一个个困难。但如果别人说你是女孩子,不用这样做,你缩回来,你就会越来越缩。很多时候你需要一双手把你往外推,很多中东女性就是缺少这样一双手。
时间流逝的速度可能不是均匀的。在上海时,我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的,每次到年底,大家会觉得一年过得很快,没太多记忆点。但我在中东的那些旅行中,在这种高密度、高强度的生命体验里,我的感官放大了,感受力变强了,一个月像一年一样长。
在2020到2022 年,我连江浙沪都没有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感觉还蛮舒服的,那三年在写作和阅读,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到国外去。我那么爱往外走的人,心态已经调整到“我其实也没有这么想出门”。在新冠疫情期间不能出门的时候,我在写这本关于中东的书,也越发觉得日光底下无新事:2016年我刚去伊朗的时候,伊朗人对我说他们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研究生毕业都不容易找到工作,当时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我在叙利亚时,看到人们会囤很多菜,当时我也觉得很荒诞,后来我在新冠疫情时也囤了很多土豆和萝卜。
2012年我辞职去做风光摄影师,正好是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App创业越来越多,社会上的机会也非常多,当时根本不愁没有工作。出门玩一大圈,回到上海之后,很多做新App的公司问我要不要去上班,开的工资都还挺高的。那时候,其实我会更有安全感,觉得我可以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016年初我刚开启中东旅程的时候也是,整个社会的情绪是很积极的,不管是对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都是关注和好奇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到了新冠疫情时,大家就越来越封闭,等到疫情过去,整个社会重新开放之后,大家其实已经自顾不暇了,安顿好个人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时候,人已经没有太多心力往外看了。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的很大变化,我希望它只是阶段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