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上一篇:
都铎玫瑰之七:鹬蚌相争,都铎得利!
引言:
在英国历史上,亨利七世有“贤王”之称;但同时,他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大搞贸易保护,用行政干预市场,开创特务统治,用揭发告密、刑讯逼供、密室审判等方式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分批次处决贵族并没收其财产……
可谓是英国史上的“朱元璋”!
正文:
血腥残酷的玫瑰战争在持续了三十年
(1455年-1485年)
后,终于在亨利·都铎手中结束了。
由于长期的战乱、疾病以及经济衰退等因素,英国人口从1348年之前的高峰(近600万)锐减到原先的三分之一,即200万左右。此后,由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恢复增长。
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和社会需求也跟着增长,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商品化过程,促进了城市和贸易的复兴和发展,并引爆了英国的房地产市场。
用今天的话来说,英国由于休养生息,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趋势。
这使得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有力促进了英国人形成新的激动人心的世界观,尤其是促生了从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
都铎王朝就处于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从这个时代开始,英国不再偏于一隅,而不可避免地与欧洲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多的紧密联系。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都铎王朝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分水岭。
神圣的传统、充满机会与变革、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对社会的焦虑交织在一起,使得都铎时代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
刀光剑影,权谋诡计,艳情谋杀,宗教迫害,党争倾轧,和平演变,阴谋颠覆,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可以说是人头滚滚,血流漂杵!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亨利七世上台时,英国经过长期的nozuonodie,已经衰落成一个老少边穷的落后国家(当然,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这俩难兄难弟垫底,它还不算倒数第一)。特别是英国与曾经的竞争对手法国相比,各方面的国家实力差距越拉越大,显然不可能再像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那样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矛盾。
亨利七世在对外关系上长期坚持的政策基准是:“不是角逐欧洲霸权,而是谋求扩增贸易利益”,换成中国人容易理解的表述,就是“韬光养晦,不争霸”。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亨利七世进行了一系列励精图治的政治经济改革。
前文提到,黑死病使得英国以羊毛纺织业为主的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涌现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这些新贵的经济实力在迅速增长,但是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后面相继登场的权倾朝野的红衣主教沃尔西以及都铎王朝的第一权臣托马斯·克伦威尔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地位显赫,但是因为出身低贱屡遭旧贵族嘲笑,甚至当面羞辱。
虽然大批封建旧贵族在玫瑰战争的互相残杀中或阵亡或被处决,但封建旧贵族仍然具有较强的残余力量,并占据政治高位。
面对这种形势,都铎王朝的国王们果断选择与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联盟,打击旧贵族。
为什么会如此呢?
如果选择与旧贵族结盟,旧贵族们一个个傲娇得很,国王对他们好他们会觉得是应该的,丝毫不会有任何感恩戴德的意思。如果让他们的实力恢复到一定程度说不定还会造反,重回玫瑰战争的老路;而新贵们没有高贵的血统与古老的传承,根基不稳,心态上也谦卑得很,国王提拔他们,会使得他们无比感激而投桃报李。
在十六世纪,欧洲的主要工业部门是毛纺织业。在当时欧洲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英国的毛纺织业不如尼德兰(相当于今天的荷比卢等低地国家,安特卫普是当时全欧洲毛纺织工业的中心)和北意大利,优势产业是绵羊畜牧业,即提供羊毛原料。
如果按照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给后进国家开出的“药方”,
依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来发展,把英国全部搞成大牧场,英国人集体当放羊娃,是符合英国自然禀赋与比较优势的最佳选择。
英国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
亨利七世说,老子才不愿意给尼德兰佬和意大利佬一辈子打工呢,我们英国要搞
羊毛生产、纺织和成衣加工的全产业链
。
因此他大搞贸易保护,颁布产业政策,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三番五次通过国家法令,禁止羊毛特别是优质羊毛的出口,甚至还禁止半制成品呢绒出口,并不遗余力地推出各种措施,鼓励国内毛纺织业的发展。
随后,亨利七世与尼德兰缔结了”大通商”条约,将英国廉价的呢绒等工业品倾销至尼德兰,从而加速了尼德兰呢绒业的衰落,推动了英国呢绒业的大发展,促进了以伦敦–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对外贸易的加强与扩大。
正是基于这一点,亨利七世赢得了“商人的国王”的称号。
从亨利七世之后的三个世纪,贸易保护以及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成为英国的基本国策。
第一次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的感觉。
我们所知的经济学,其发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这些已经工业化的英国城里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创立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就是什么“看不见的手”、政府不要干预经济、比较优势、自由贸易等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之前三百年的英国经济运行状况,基本没有什么人提啊,仿佛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这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是:英国靠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把本国工业搞起来以后,忽悠别国乡下人不要搞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这样再按照“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别国的农业经济体当然就竞争不过英国的工业化经济体了,英国就可以一直当霸主了嘛!
历史上唯一始终践行自由主义经济的欧洲人是荷兰人(其实还有犹太人,不过还是不提了,一提全是血与泪啊!)。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别的国家还傻乎乎土里刨食的时候,荷兰早在公元十二世纪已经在搞工商业并成为欧洲贸易中心了。荷兰人早跑了好几百年积累起竞争优势,而且它国土狭小军事底子偏弱,当然大家都公平竞争对荷兰来说是最有利的,荷兰也正是凭此一度成为世界霸主。
不过,荷兰人在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也迅速变脸,用各种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特别是产业结构跟他们类似的英国佬。英国佬则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时候大耍流氓,公然依靠践踏自由贸易规则的手段积累实力,最终依靠军事手段打残了荷兰人,才将世界霸主的桂冠抢到手。

英荷战争
当年荷兰提倡贸易自由的时候,英国始终反对贸易自由,用各种行政军事强制手段保护本国工商业,打击荷兰竞争对手。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英国终于打败了荷兰发展成世界头号贸易强国之后,要把持全球贸易体系,才将基本国策变为大力禁止贸易保护,提倡贸易自由化。
也正是这一时候,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师们纷纷粉墨登场。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就没有所谓的“纯经济学”,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显学”,都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如果后人单纯学习经济学,而不结合该经济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了解其来龙去脉,很容易就落入别人布好的套路里,而误入歧途。
是不是突然有一点明白,为啥发达国家就那么几个,后发国家沿着发达国家“指明的道路”,无论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了,因为他们都存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担心,所以故意把后来者往沟里带。令人不禁生出感慨:“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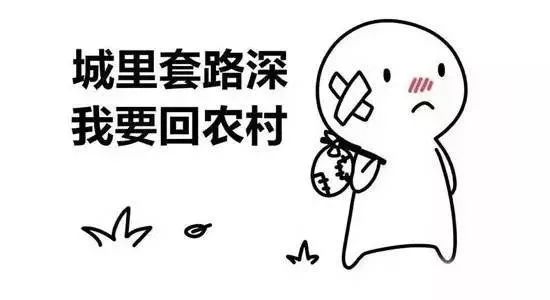
不过,英国再怎么隐藏自己的发家史,有心人还是能发现的。在英国之后的后发工业国德国、法国、美国都是看穿了英国的忽悠伎俩,顶住各种压力,效仿当年英国的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措施埋头发展,等自己发展起来了又不约而同地鼓吹自由贸易了。而对英国最知根知底的美国人,更是把这一套路发扬光大,并将其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读到这里读者不要误解,作者的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理论。恰恰相反,古典经济学理论太对了,但正因为其正确性,后发国家如果始终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必然误入歧途。
古典经济学理论说白了,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环境,让各种经济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国内竞争中,可以保证优胜劣汰,留下来的都是最有效率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而在国际竞争中,这个所谓的公平环境就变成了丛林环境,先发国家的大企业大公司就如同早已进化出利爪獠牙的猛兽,后发国家必须用市场之外的手段将自己用坚硬的壳保护起来,才能获得壮大自身的机会,否则与先发国家处在同一个自由竞争环境中,就是“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命。
另有一个讽刺的例子从反面说明这一点。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后,成了全球一体化(说白了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获益方,而发达国家则纷纷自我打脸,置原先自己提倡的自由贸易原则于不顾,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这也说明,发达国家始终都没有将“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严格区分过,从来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灵活运用。
对于经济学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再回到都铎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发达的商品经济对建立在封建土地基础上的旧经济产生了瓦解作用,间接削弱旧贵族的力量。王权控制着各种贸易往来,初步形成了保护工商业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统一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初步形成,城乡关系从对立到一体化过渡。
都铎时代,君权与议会达到了空前的协调一致,共同维系着英国政治机器的运作,以至于某些西方学者把都铎议会称作“奴性十足的国王驯服工具”。
那时的英国议员们基本是这么开议会的:
国王赞成的我坚决赞成,国王反对的我坚决反对。
在地方上,国王任命的各郡治安法官的职权被扩大了,变成了中央王权的“杂役女佣”,全权负责一切地方管理。政治统一结束了国内封建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使得英国的工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可能各位读者有些奇怪,为何曾经跟国王对着干的议会变得如此顺从,而曾经叛乱不断的贵族们好像销声匿迹了呢?难道说,亨利七世就是传说中冒着王霸之气,贵族们纷纷俯首帖耳,口中高呼吾王“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怎!么!可!能!!
旧贵族集体噤声的真实原因是:凡是造反的、要造反的、想造反的,甚至看起来像是要造反的那些旧贵族们,都被用各种借口安插了叛国的罪名给咔嚓了,剩下的都匍匐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自然就没声音了。
读者们是不是想起了一个人?没错,那就是比亨利七世早生了一百多年,大杀开国功臣的明太祖朱元璋!

亨利七世,另一个时空的“朱元璋
”
是不是画风转换得有点太快有点不适应?没关系,我们从头讲起。
亨利七世发动叛乱推翻理查三世获得王位的过程,无论披上怎样的华丽外衣进行粉饰,本质上仍然是被旧贵族们拥立上台,可以说是与兰开斯特王朝的开国国王亨利四世获得王位的过程如出一辙。
相对于亨利四世的根正苗红,亨利七世的父母两系都来源于私生子,血统上就不算纯正。坐在王位上的亨利四世成天心惊胆战,生怕那一天就被掀下王位身首异处,亨利七世心中的焦虑与恐惧比起亨利四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加冕典礼上,虽然国会把亨利七世夸得跟救世主似的,但是亨利七世从戴上王冠的那一刻起,心里盘算的都是怎么避免重蹈兰开斯特王朝的覆辙,消除贵族们的叛乱隐患。
亨利七世很喜欢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灵感。可是,英国历史就是一部贵族叛乱的历史,亨利七世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归结到一条釜底抽薪之计:只有把这帮英格兰旧贵族都给灭了才能一劳永逸。
如何把旧贵族们都给灭了又不激起反抗呢?二十世纪关于纳粹德国搞迫害,有个著名的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