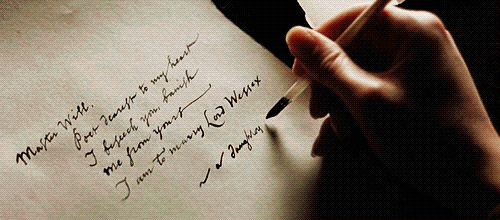
作家没办法以禅师的方式教学。我们可以去听一门作家的课,但这是不够的。课堂上我们看不到作家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如何找到写作灵感。我们坐在教室里,学习什么叫叙述,却想不明白如何去实践。A不会导致B。我们无法完成这关键的一跃。因此写作总是只存在于书架上的小说里,在教室的黑板上被讨论着,而我们只能傻傻地坐在座位上。我认识许多人,他们渴望成为作家却不知从何下手。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就像一道裂开的伤口。
写作如参禅,它将你带回到自然的心理状态,回到心灵的旷野,那里可没有修剪成排的剑兰。
心灵是原始的、充满能量的,是活的,也是饥渴的。大脑思考事物的方式并不像我们从小被教育的那样中规中矩、有礼有节。
读一本关于写作的书与真正坐下来写是两码事。所谓知难行易,正是这个道理。
光看关于写作的书是不够的。要想成为作家,要有一定的生活方式,并以一定的方式去观察、思考、存在。这是一种传承。
作家们把所学所知传递下去,就像我对禅宗的大部分了解,都是片桐禅师面授于我的。
举个例子,我刚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市,想要学习佛学。此前我住在博尔德市,师从一位藏族老师。这一藏传派系讲究排场。学习中心规模很大,我们需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与老师面谈一次,并且需要穿着盛装去见他。
在明尼阿波利斯,我打电话给禅修中心,问能不能约个时间拜访那里的禅师。电话那头的男人说话带着很重的日本口音,他让我直接过去。我这才意识到他就是禅师。我连忙穿上盛装赶过去。片桐禅师走下楼梯,下身穿一条牛仔裤,上身穿一件写着
“Marcy School Is Purr-fect”(马西学校很完美,喵)的绿色T恤,T恤上印着一只猫的图案。他的小儿子读马西小学。我们聊了十分钟,平淡无奇。然后我离开了,感觉毫无所获。
大约一个月后,禅宗简报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为秋季刊采访一下片桐禅师。我答应了。采访当天的早晨,我醒来后满脑子想的都是该买什么颜色的窗帘。那是
1978年,彼时我刚结婚。在开车去禅宗中心采访的途中,窗帘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打算速战速决搞定访问,然后火速赶往纺织品店。
我把车停在禅修中心前,冲下车。此时我已经迟到了好几分钟。等我走到一半,突然想起来笔记本落在了车前座。我又冲回去,拿上笔记本,跑到禅修中心的后门。我一把推开门,转过拐角,猛然停了下来:穿着黑色袈裟的禅师正站在厨房的水池边,给一株粉色的兰花浇水。这株兰花是他三个星期前得到的。有人从夏威夷的一个佛教婚礼上给他带回来,我也参加了那场婚礼。时隔三周,兰花依然鲜活如初。
“禅师!”我手指着兰花,惊诧不已。
“是的。”他转过身来,面带微笑。我感受到他身上每一个细胞的存在,
“你悉心照料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会活很久。”

这是我与他展开真正交流的开端。
我从片桐禅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傲慢、固执,也懂得了仁慈与同情。这些并不是通过批评或表扬学到的。他既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表扬我。他就在那里,与他的生命同在,耐心地、长久地等着我也能够与我的生命同在,等着我觉醒。
作家没办法以禅师的方式教学。我们可以去听一门作家的课,但这是不够的。课堂上我们看不到作家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如何找到写作灵感。我们坐在教室里,学习什么叫叙述,却想不明白如何去实践。
A不会导致B。我们无法完成这关键的一跃。因此写作总是只存在于书架上的小说里,在教室的黑板上被讨论着,而我们只能傻傻地坐在座位上。我认识许多人,他们渴望成为作家却不知从何下手。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就像一道裂开的伤口。
我的另一本书《再活一次》首次出版后的一天下午,优秀的南方小说家塞西尔
·道金斯(Cecil Dawkins)读完之后,缓缓开口对我说道:“哎呀,纳塔莉,这本书会很火的。读完这本书,人们会对作者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读者真正想要的
,
”她边点头边说,“
就是深入地了解作者。即使是一本小说,他们也希望了解作者。
”
人与人之间的孤立是可怕的。我们渴望相互联结,找到写作的意义。
“你怎样生活?你在想什么?”我们问作者。我们都在寻找暗示、故事和例子。
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经验,从而在写作这条路上帮到我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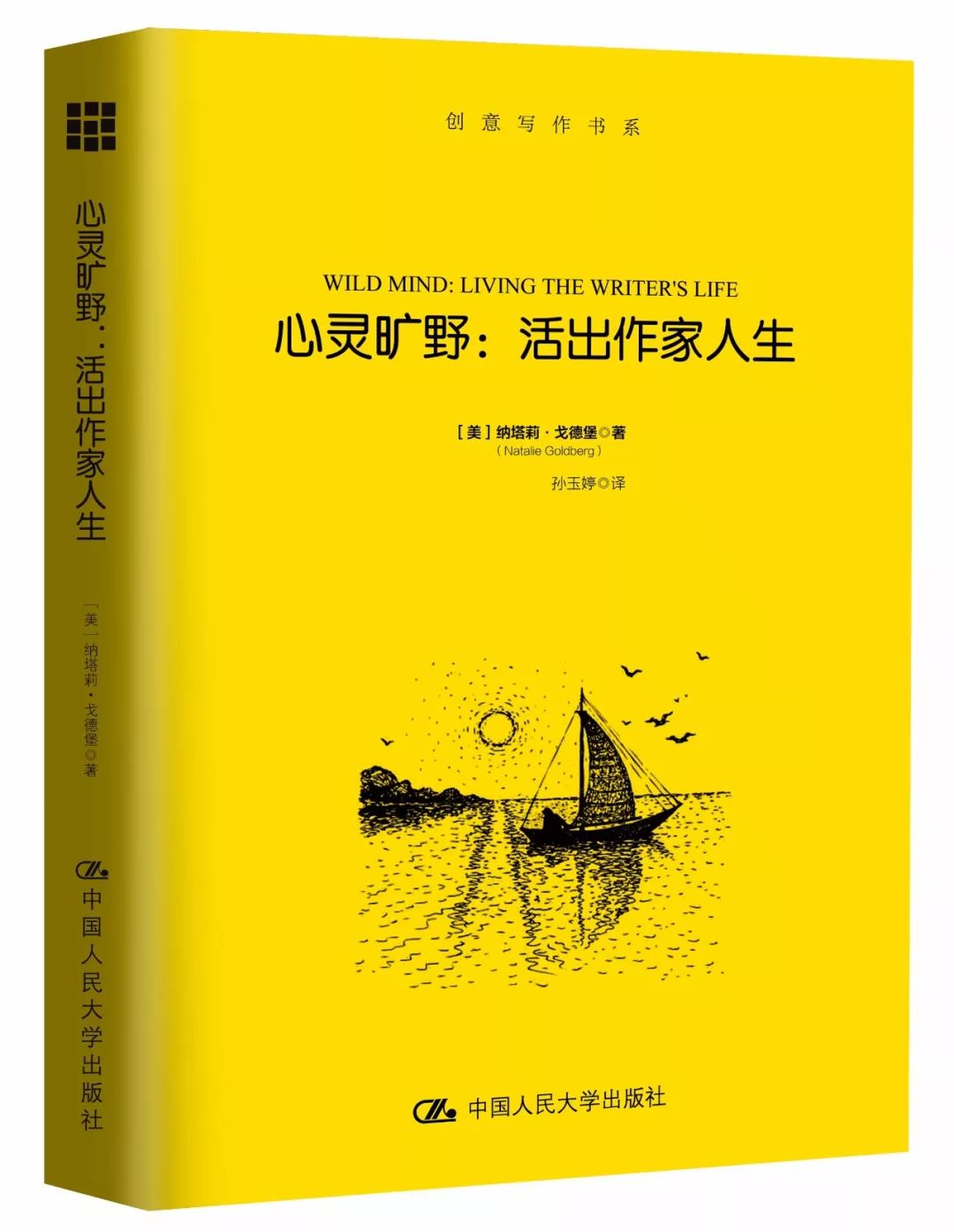
心灵旷野:活出作家人生
纳塔莉·戈德堡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1
在你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式和风格之前,写作练习的训练是帮助你进入写作、熟悉写作基本形式的最好方式。
写作练习就像禅宗里的冥想一样,需要你长期坚持做下去。
写作练习让你注意到你的心灵,并相信它、理解它,这是写作的根本。掌握了根本,你就可以写任何东西。
一旦坐下来写,不管十分钟还是一小时,只要开始,就不要停。
这么做目的何在?大部分时候,我们写作时既是创作者也是编辑者。将你写作的手想象成创作者,将另一只手想象成编辑者。两只手握在一起,手指紧扣。这就是我们写作时的情形。写作的那只手想写周六晚上发生的事:“我整晚都喝着威士忌,盯着酒吧那头一个男人的背。他穿着一件红色
T
恤。我想象他长着一张哈里·贝拉方特的脸。凌晨
3
点,他终于转头朝向我,看清他的样子后,我往烟灰缸里吐了一口唾沫。他的脸长得像一只掉了牙的湿漉漉的杂种狗。”写作的手刚写了几个字:“我整晚都喝着威士忌……”另一只手就收紧手指,让写作的手动也不能动。编辑者对创作者说:“这么写不好,威士忌什么的……别让人知道这些。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昨晚,我美美地喝了杯温牛奶,然后
9
点钟上床睡觉。’就这么写。写吧!我这就松开手。”
如果写作的手不停,编辑的手就难以抓住它、锁住它,写作的手就可以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手不要停”的规则让创作者更强大,不给编辑者插手的空间。
手不要停是写作练习的主要构成内容。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管对不对、礼不礼貌、合不合适,别理会后果。艾伦·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练习的是押韵诗。那时他做了大量正规的格律等方面的练习。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告诉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忘掉程式化的条条框框,结果他写出了《嚎叫》(
Howl
)。我们当然不能忽略他此前的大量实践积累,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告诉学生“好了,说你想说的,尽情发挥”之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自然了很多。
不是车,是凯迪拉克。不是水果,是苹果。不是鸟,是鹪鹩。不是一个依赖性强、神经过敏的男人,而是哈里,哈里跑去给妻子开冰箱,以为她要拿苹果,实际上她是去煤气灶边取火点香烟。提防大众心理学的标签,越过标签,具体到个人。
但写作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不要说:“我真是个白痴。纳塔莉说了要具体,我却愚蠢地写下了‘树’。”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你写了“树”,那么就可以更进一步,在“树”的旁边写下“美国梧桐”。对自己温柔一点。别给编辑者的“铁掌”有乘虚而入的空间。
我们通常活在第二层或第三层思维里,想法常常是加工过的,而非第一层思维,即我们对事物的真实反应。留住第一反应。写作练习可以帮你接触第一层思维。忘掉一切杂念,只管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