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新作《被埋葬的巨人》中,石黑一雄杂糅真实与神话,继续以记忆为切口,通过书写英国民族形成之初人类生存境遇来反观当下。他戏仿奇幻叙事并舍弃惯用的叙事视角,聚焦个体与集体两个维度上记忆选择带来的伦理困境。小说虽书写远古,但却喻指当下。
关键词
:石黑一雄
影响的焦虑
记忆选择
身份认同
创伤愈合
2015
年
3
月,经过十年不辍笔耕,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1954
—)终于推出新作《被埋葬的巨人》(
The Buried Giant
)。它聚焦英国民族形成之初的模糊历史,以一对老年夫妇的寻子之旅为叙事主线,书写记忆碎片化的伦理情境下个体与集体在记忆选择上面临的伦理困境。该小说出版后受到好评,《纽约时报》称它“具备一切巨著该有的东西:读完之后久久难以忘怀……它是一部出类拔萃的小说。”
①
自处女作《群山淡影》(
1982
)至今,石黑一雄始终以“记忆”为切口展现全球文化碰撞与交融下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新作除延续作者一贯的创作主题外,又力求突破与有所侧重。《卫报》称“尽管石黑一雄痴迷于记忆与失去主题,但总乐于给读者制造惊喜……在这部创作周期长达十年的小说中,他对文类做了最为惊人大胆的改编。”
②
该小说突破点之一便是戏仿奇幻小说叙事,将魔怪等超自然元素,尤其是母龙奎里克,置于旅途中。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喷出“失忆雾气”,使人类世界陷入记忆碎片化的伦理情境之中。可以说,整个旅行就是一场探求真与正义的屠龙之旅。因而,尽管被一些评论家诟病,但石黑一雄的戏仿却有其深意所在。在谈论该小说创作动机时,他在采访中说:“我十分关注当代现实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我并不想把它设在这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中,让它读起来像报告文学……作为一名作家,我想写一些更具有隐喻性的故事。”
③
小说叙事时间虽设定在后亚瑟王时代,但由于奇幻叙事模糊历史与神话之间的界限,超脱“时间牢笼”限制,从而使作品主题更具隐喻性与当下性。
除在叙事元素外,石黑一雄也在继承其以往写作主题上有所创新,以求摆脱先前作品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他曾将其小说定位为“关于个体如何面对痛苦的记忆”④,因此,其作品常蕴含浓厚的记忆意识,如《上海孤儿》中班克斯对童年记忆的探寻、《群山淡影》中悦子对日本长崎的追忆、《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对英国过往的留恋等。新作中艾克和比阿特丽斯夫妇相信,只要找到多年前离家出走的儿子就能恢复一切记忆。于是,这场寻子之旅也可视为其记忆追寻之旅。旅途中,他们先后遇到撒克逊勇士威斯坦、撒克逊男孩埃德温以及高文爵士,他们身上隐藏的或伤痛或焦虑的往事记忆也随之被揭开。同样书写“痛苦的记忆”,但该小说侧重点与先前小说有所不同,它更注重从个体与集体两个角度考量记忆选择所引发的伦理困境。为达此叙事效果,石黑一雄放弃惯用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转而采用第一和三人称视角交替叙事,多角度呈现对同一记忆所持的不同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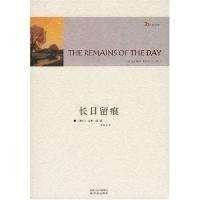
从某种意义上说,夫妇二人的寻子之旅可视为对其为人父母伦理身份的寻求与
建构,然而,这种努力却将身份建构引向其反面——解构,进而引发个体身份认同困境。导致这场困境的始作俑者在于记忆本身。小说中,失忆割裂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联接,人们的生活也就因此被切分成瞬间的当下记忆与碎片化的过去记忆。面对记忆危机,除夫妇二人外,部落中其他人都未曾意识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艾克向邻居谈及不久前失踪的红发女医师时,很多人都云里雾里,甚至有人说,这事肯定发生在很久之前。与其他人的心安理得不同,记忆断裂带来的失落感横亘于两人心中,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种克服之道:一是忘记曾拥有的过去,接受瞬间当下;二是向过去进发,拼凑碎片过去。现实生存困境最终促使他们做出选择,重访过去以探明失忆真相。夫妇二人在部落中基本上属于边缘化存在。他们住在山洞最外延,远离象征权力的大厅。更为严重的是,部落权威禁止他们使用蜡烛,这就暗示他们失去对其处境的反思能力,因为“辨别能力……首先是光所象征的东西。”⑤他们好比柏拉图“洞穴理论”中的囚徒,光源的剥夺使其难以察觉“阴影”的虚假,也就难以意识到当前的生存困境。与其他人的完全失忆不同,他们能感知到失忆的存在,因而,生活中碎片化的记忆就如零星的“火光”刺激他们走出洞穴。最终,失忆带来的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在对儿子的记忆上得到释放。他们坚信,只要找到儿子,就能解开失忆之迷并将过去记忆拼凑完整。这样,儿子成为触发他们伦理意识的记忆符号,寻子之旅也就成一场父母伦理身份的建构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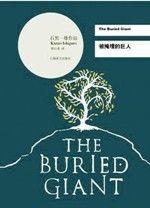
随着过去记忆被零碎地唤醒,建构新身份的初衷非但没有达成,反而使他们,尤其是艾克,陷入身份焦虑之中。当智者乔纳斯道出失忆是由奎里克造成的秘密时,他们在是否屠龙以找回记忆上发生分歧。比阿特丽斯坚持屠龙,因为她认为:“如果没有记忆,我们的爱只会枯萎直至死亡。”⑥与妻子的决绝相反,艾克却陷入某种恐惧之中,因为未知过去的揭开逐渐消解其现有的两种身份——勇敢的强者与忠诚的丈夫。旅途未开始前,日常生活中,艾克始终都以一个勇敢的强者身份关护着妻子。然而,被唤醒的记忆碎片触碰并解构这一强者身份的核心——男性气概。当看到乔装的威斯坦被士兵羞辱时,另一士兵脸上怒不敢言的表情唤起他对过去的记忆。感同身受的体验使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身份并非一个敢做敢言的强者。随后,他断断续续地记起自己“窝囊”的军旅生涯:面对无辜的撒克逊人被本族士兵屠杀,他无力阻止;而在随后与亚瑟王对质中,他又只能选择怯弱地离开。可以说,他过去的懦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其当下的男性气概。此外,随着过去记忆的揭开,困扰他们许久的儿子离家之谜也渐渐露出冰山一角。比阿特丽斯说:“那晚我独自躺在床上,但心中却清楚你去找其他年轻貌美的女子去了。”
(
Buried
:250)
丈夫的不忠引发父子间争执,最终导致儿子负气出走。在妻子质问下,艾克无力求证这一模糊的记忆。艾克始终称妻子为“公主”,对其呵护有加,但过去的背叛行径却消解了“忠诚的丈夫”形象。最终,两种身份的解构使艾克逐渐丧失探寻失忆真相的勇气,乃至拒绝屠龙。小说快结尾时,三个孩子请求他们把体内有毒的山羊带至奎里克活动的平原,这样它就会因为吃下山羊而中毒死去。但艾克严词拒绝,以此抵制过去记忆对当前身份的解构。碍于妻子的坚持,他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他们的请求。由于担心过去记忆会让妻子忘记现在的自己,所以,在去奎里克巢穴的途中,他恳求道:“公主,答应我在雾退散后,不管记起了什么,你都要铭记此刻内心对我的感受。”
(
Buried
:258)
后现代文化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己经崩溃了。小说中,石黑一雄借失忆成功地将记忆的后现代状态呈现出来,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与反思。在记忆碎片化的伦理情境下,弱势群体在寻找精神归属时,难免会遭遇身份认同危机。对于他们来说,记忆轴上向前或向后的“破镜重圆”努力可能都是徒劳的,因为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始终交织此种选择之中。正如小说结尾所示,尽管他们找回记忆,但却再次被“戏弄”。儿子其实早就死去,这就暗示记忆真相的虚无性与身份建构的破产,旅行原本的意义也就此消解。
母龙被杀死后,艾克反思道:“谁都无法预知这片土地上会有什么旧仇被重拾。我们祈祷上帝将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但习俗与质疑总在分离我们。”
(
Buried
:297)
由此反观小说故事脉络,一条隐含在寻子叙事线之下民族创伤叙事线就清晰可见。小说中,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已停战多年,起初两族间敌对状态也已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失忆,两族人可以混居生活,进而有融合成新民族的迹象;另一方面由于大屠杀,植根于撒克逊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仇视感随时可能会被点燃。这两种可能在第三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夫妇二人来到撒克逊人部落不久后便遭到围堵,剑拔弩张之际幸而得到同族人艾弗的解围。艾弗解释,此时部落正受到食人魔的威胁,但间歇性失忆让士兵忘记外在危险,转而抓捕异族人,这说明失忆并没有完全让他们忘记民族身份。然而,艾弗作为一名不列颠人,但在撒克逊人中却有一定的地位,这表明两族人又有融合的可能。创伤会以何种形式愈合,融合抑或敌对,这取决于两族人如何对待集体创伤记忆。
虽然奎里克喷出的雾气能抹除人的记忆,但却无法移除记忆的物质载体。威斯坦来到寺庙后开始感到不安,艾克以为是旅途劳累所致,但他对艾克说:“或许我的恐惧仅是源于这些墙壁传递的过去记忆。”
(
Buried
:140)
从墙上剑痕及寺庙布局中,威斯坦推断,这里曾经是撒克逊人占领的城堡。通过进一步探访,他又断定如今的和平祷告之地曾经是个屠宰场,无辜的撒克逊人遭到不列颠人的屠杀。多年过去,这一创伤事件的施加者与承受者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伤体验,也面临着如何走出创伤阴影的难题。寺庙中的不列颠僧侣虽非屠杀的直接实施者,但因本族人的暴行而内疚自责,饱受良心拷问。他们认为忘却是最好的疗伤之道,因而,他们暗中喂养奎里克,借失忆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事实上,正是由于失忆,两族人才得以友好共处。也正是出自这个善的初衷,当得知威斯坦一群人将去屠龙时,他们才会百般阻挠,直至不得已痛下杀手。同时,他们又定期将自己捆绑在刑具上,自愿奉献血肉喂食鸟类以求得到上帝宽恕。然而,这样一种救赎之道却使他们陷入迷茫。一方面他们尝试忘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忘记,因为定期的身体创伤总是在提醒他们这样的缘由——先人所犯的罪孽。这种困境最终导致了内讧,放弃献祭的僧侣占了上风,囚禁了以乔纳斯为首的“燔祭派”。整体而言,尽管存在分歧,但在创伤愈合上,以僧侣为代表的不列颠人选择忘记创伤记忆。
相对于创伤施加者的忘却,受害者们更在意还原历史真相,让正义复归原位。本质而言,记忆也可视为一种历史叙事。叙述者伦理立场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事姿态。作为亚瑟王朝功勋卓著的骑士,高文爵士有着浓厚的怀旧情结,自始至终都穿着那套承载其往昔光荣回忆的破旧盔甲。因而,他在叙述大屠杀事件时更愿意将之神圣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面对艾克责问亚瑟王破坏和平协议下令屠杀撒克逊人一事,高文维护亚瑟王并认为大屠杀是合法的,因为“我们可以一次性终结复仇循环,一位伟大的君王在此事上必须果敢。”
(
Buried
:213)
在高文看来,失忆成为抚平创伤与维系和平的唯一良药。与之相反,以威斯坦为代表的撒克逊人认为大屠杀应该铭记而非忘却或美化。在屠龙的最后关头,他质问高文:“爵士,什么样的上帝打算让错误被遗忘且免于处罚?”
(
Buried
:285)
在他看来,虽然遗忘让本族人与异族人安居乐业,但不能因为屠杀的结果是善的,就可以将行为本身等同于正义之举。威斯坦坚持屠龙,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正义成了掩盖复仇的说辞,正如高文为屠杀正名一样。这样,正义在创伤受害者的言说中只不过是一纸空谈。
小说在威斯坦等待族人开展报复行动中渐进尾声。石黑一雄就此停笔,不再叙述此后历史。小说中人物无法得见未来局势,也自然不知民族创伤以何种方式愈合。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我们可知,撒克逊人终达复仇初衷,而战败的不列颠人大部分选择与外来者融合,一部分逃至威尔士以及英格兰西南部。英国民族就此开始了漫长的形塑过程。伴随这一过程,民族创伤也在遗忘与记忆并置的矛盾中逐渐消弭。
石黑一雄在采访中坦言,曾为跻身流行小说家之列而刻意地模仿历史小说写作。新作中,他将笔伸至先前作品从未达到的历史之境,从英国民族形成之源头上反思身份认同与创伤救赎困境。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困境在当下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某种层面上说,当下多元文化社会也是一个文化记忆多元化的社会。在记忆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伦理环境下,人们都很难绕开身份与创伤问题。因此,该小说虽书写远古但却直指当下,将关乎人类生存状况的严肃主题寓于奇幻小说叙事之中,使读者在阅读狂欢之中能有所体悟。这也是为什么《出版人周刊》认为它“容易阅读但却难以忘怀”⑧的根由之一。
①
Neil Gaiman: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
,
www.nytimes.com/2015/03/01/books/review/kazuo-ishiguros-the-buried-giant
②
Tom Holland
,“
The Buried Giant
Review
–
Kazuo Ishiguro Venturesinto Tolkien Territory
”,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mar/04/the-buried-giant-review-kazuo-ishiguro-tolkien-britain-mythical-past
③
NRP: The Persistence -- And Impermanence -- Of MemoryIn '
The Buried Giant
'
④
, Susannah Hunnewell
,
“Kazuo Ishiguro: The Art of Fiction No. 196.” Paris Review 184(2008), p. 42.
⑤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225
页。
⑥
Kazuo Ishiguro:
The Buried Gia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p. 45.
下文随文标出书名首词“
Buried
”和引文页码,不再另注。
⑦
Lydia Millet:
The Buried Giant
,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978-0307271037
作者单位: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5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公众号责编:文娟)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2017
年《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
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
:
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
010-59366555
征订邮箱
: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