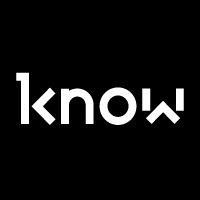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来自于我们和4个朋友聊了聊他们“最努力的时候”。故事的主人公们努力的方向很不同。有的人是在备战高考和毕业求职,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获得自立而努力,可能会令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人感同身受;也有人最努力的事情是用10年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虽然这份喜欢在旁人看来没有结果,且使自己失去了很多机会,但她仍然认为自己从中获益。还有一位父亲,他用2个月的时间,将自己被顶尖专家诊断为自闭症的儿子救了回来,事情的过程几乎可以用“神奇”来形容。
他们努力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有人达到了目标,有人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或者会被认为是失败的。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自己曾经做出的努力并不后悔,而且认为仅仅是努力这件事本身,那种全力以赴、全心全意去做一件事情的状态,就足够使自己的人生变得不一样——曾经非常努力过,才能够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也才能更好地出发。
可能你能从他们的故事中,看到一段自己的记忆:

1
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为高考努力,
因为那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
最努力的时候当然是高考,因为在18岁以前,那是我唯一的出路。
那时候我在一个小县城里,和经常打骂我的父亲一起生活。我反感应试教育,总觉得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和身边人无话可说,喜欢的书、音乐和电影都不是同一类型。我遭受过同学的霸凌,后来又开始霸凌他人,总之,几乎是一个自暴自弃的问题少女。
但我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去田径场跑步。有一天跑到一半,我停下来喘气,突然觉得内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求生”的念头。
我发现自己非常想要摆脱这个环境,因为我相信有更好的地方在等着我,我可以在那里过得更舒服。我想要过上像一些书和电影里描述的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这可能是为什么,那时我很喜欢听Radiohead那首Creep:“I’m a creep, I’m a weirdo…I don’t belong here.”
但是摆脱这种状态,我需要离开家,离开学校,离开这个小县城。离开的唯一方法则是高考。
在高一结束、文理分科时,我的成绩还是班里倒数,有两门课的成绩不足30分,所以我开始像发疯一样的学习。为学习努力的过程都是相似的,比如我对自己进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只睡3-4小时,每周六补觉半天,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每当我累得感觉自己无法支撑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你想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故事的结局还是好的,我考上了名校,去了大城市,也过上了让自己更舒服的生活。后来我也遇到过更多比当年更复杂、更困难的情境和挑战,经常感叹,钱和考试就能解决的问题统统都不是问题。但我依然很怀念那段为了心无旁骛、奋力拼搏的时光。
后来我学日语的时候,发现“拼命努力”所对应的词是“一生懸命”,觉得实在是很贴切。那时候我真的感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只好尽全力去做这件事。
人都是有惰性的。当我真的变得自由,没有了那种“生存压力”,我发现无论什么样的考试和挑战,都再也无法让我燃起那样的斗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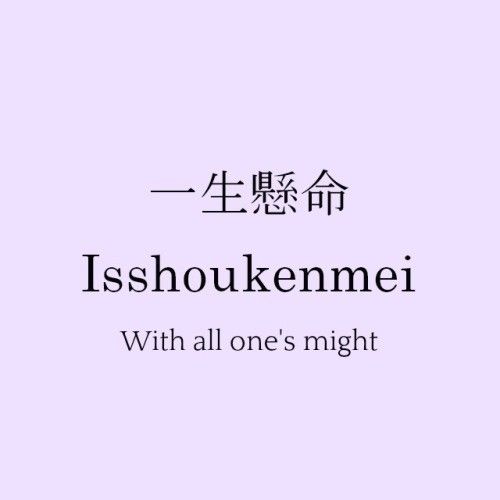
2
我用了2个月时间推翻了专家的结论,
“治好”了儿子的自闭症
三年前,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努力的两个月。当时,我两岁半的儿子被诊断为自闭症中度,说这种疾病是脑神经发育异常,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终身不愈,将来生活不能自理。
在被诊断之前,我儿子的身体指标都正常,智力水平算优秀,跟小朋友们在一起也是大方、自然。在他2岁时,我们把他交给爷爷奶奶来带,但爷爷奶奶一个从早到晚都在上网,一个守着电视看,我儿子总是一个人在角落待着。
2岁4个月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孩子不对劲。跟他说什么都像没听见一样,自顾自地玩。他也不再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了,如果别的小朋友跑到他身边,他甚至会避开。
这个时候,我妻子的单位请了一位育儿专家办讲座,把孩子的情况跟专家讲了之后,专家让我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看,他怀疑是自闭症。
我们赶紧打听权威的医院,然后托人找到安定医院的儿科专家,这位专家仔细观察了我儿子半个小时,详细了解情况后,诊断为自闭症。我们不甘心,又去了北医六院的儿科,2位自闭症专家也正式诊断我儿子为自闭症中度。如此,三个全国顶尖的医生给出了一致的诊断结果。
我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但我不敢让家人知道,因为他们的心理压力一定不比我小,不能再给他们增加无谓的负担。但我也知道我必须睡觉,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要为我儿子攒下每一分钱,要比他多活一天。
医生虽然说终身不愈,但我不可能不想方设法救我儿子。从那天起,我拼命地在网上查阅信息,看了一尺多厚的书,和其他家长交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究自闭症,除了吃饭和睡觉。
我没有在资料中发现有用的治疗方案,但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一天夜里,我在研究自闭症诊断标准时,猛然发现我自己小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症状,而且如果按照诊断标准来看,我的自闭比儿子还严重。(我的记忆力很好,连小时候在我妈怀里吃奶的场景我都记得,只是别人都不相信。)但我显然早就走出了自闭,现在我的社交、社会生存能力一点也没有问题。
自闭症诊断标准中,有一种叫克氏量表,我把我小时候符合克氏量表的行为,和当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想法和感受,详详细细写了下来,用A4纸打印出来,有十页左右,拿去给北医六院的专家看。
专家虽然收下了我的材料,但她告诉我要接受现实,自闭症是脑神经发育异常,要抓紧训练孩子,多少能挽回一点儿。
我们全家人也不相信我,不断地要我接受现实。我好像和全世界战斗,却仍然毫不动摇,义无反顾,就好像有一个猎狗追兔子的故事里说的那样,猎狗为了一顿饭而拼命追赶,兔子为了自己的命而尽力逃跑,都在全力以赴。我要救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以满怀奇迹发生的心态观察过自闭症孩子,我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儿子并不是对我们的呼唤都一律不理。如果他觉得爸爸妈妈有谁不在他身边,但我们出其不意地在他身后叫他,他就会第一时间回头看我们。但之后,任我们如何喊他,他又置之不理了。我们在多个场合做了试验,屡试不爽。
然后我就开始怀疑,如果自闭症是脑神经问题,应该是这个功能缺失,但为什么第一次喊他有反应,之后再无反应?我觉得只有一种答案:不回应我们的呼唤,是他经过思考后,自己做出的选择。
之后,我继续挖掘还有什么能让我儿子对我们的话做出回应,我发现糖、米老鼠都能把儿子从他的世界里拽出来。这令我更加确定,从接受外界刺激,到信息处理,到控制身体做出反馈,他的这整条神经是通的。再结合我自己小时候的心理感受,我越来越觉得我儿子的自闭行为,是他自己做出的“他认为对自己最合理的明智选择”。
但如何把他带出自闭呢?我问了我父母和哥哥,但他们什么都想不起来,于是我再次仔细回想,自己是如何从自闭,走向与幼儿园的小朋友交朋友、打开心扉的。我最后总结出两个因素:一是我有个有趣并且神通广大的哥哥,我总是观察他在干什么,然后学他;二是我们幼儿园里有很漂亮的女孩子,我很想和她们一起玩。我是通过他们开始关注别人的。于是我想,一定要给他找同龄的伙伴陪在他的身边。
当时正好是暑假,我们把他表姐接到了家里,但儿子不为所动,甚至会避开。于是我想办法让他主动接近表姐。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豆,让表姐往他嘴里塞了一颗,儿子觉得很好吃,我们就说“你找姐姐要”。第二天早上,我儿子一睁眼就爬起来,跑到表姐的房间说:“姐姐,快起床。”这是他陷入自闭之后,第一次主动找同龄人玩。
类似这样的努力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之后我又想了一个笨办法:我每天记录儿子一天的生活细节,并在晚上儿子睡觉后,和他妈妈对他一天的表现做一次ABC量表(另一种更复杂的自闭症诊断标准)评分。几天后,我们发现儿子每天的分数是不同的。于是我就开始倒查日记,分析是哪些因素导致儿子的自闭程度发生了变化。一周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简单但是很关键的因素:当他心情好时,量表分数就低。于是我们制定一个规矩:所有事情都以不惹孩子生气为第一原则。
这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儿子真的渐渐不再沉浸在他的世界里。大概一个月后,我们全家人都明显感觉到,他不再沉迷于自闭状态。于是我们再一次带孩子去了北京儿童医院孤独症门诊,主任医师经过两轮诊断,说我儿子不仅不是自闭症,将来发展为自闭症的可能性也很低。从儿子被怀疑是自闭症到排除,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随后我儿子便逐渐进步,追赶同龄人。现在他5岁了,学习、生活、社交能力都很正常。
那两个月是我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在被诊断半个月之后,我无意中发现我的体重掉了十斤,当时我吓出了冷汗,而等我儿子被排除自闭症的时候,我总共掉了二十斤。那段时间的感觉实在太痛苦,所以至今都记得很清楚,但是又非常值得。虽然那时的我并不确定会不会有好的结果,以及转机何时会出现。这件事情也让我发现,任何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要积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但同时不能没有自己的判断。
我是幸运的,这种事,绝大多数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可能不会遇见。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在想办法帮助其他的自闭症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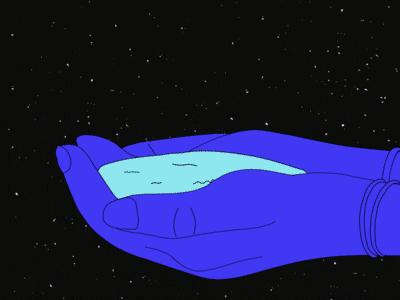
3
是那一夜的窘迫使我发现,
没有找准方向的努力是无效的
不知道有多少名校的学生像我一样,求职是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
从小学到高考都一路顺风顺水,但也就像很多“好学生”一样,我到毕业时都还没明白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大三那年暑假,各种500强公司开始来学校宣讲,我才如梦初醒,开始跟风做简历海投。
我的专业是中文,没有特别对口的职业,所以从广告、公关、市场到媒体、行政、文秘,各种岗位我都投。尽管时常困惑于面试中的那些奇怪考核方式是否能真实反映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但我依然买来专门指导面试的书进行准备,每天在BBS上查找前辈的面经,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我也是第一次学习化妆,买了人生第一套正装,每天踩着高跟鞋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时间一天天过,进的面试越来越多,但临近春节,我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offer。年底时,一天晚上突然收到某国企的通知,让我第二天就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面试。我奔向火车站,买了晚上的卧铺车,第二天又直奔酒店,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轮到了我。
那场面试1分钟就结束了,那是一家央企的行政岗位。面试官寒暄了两句后问我:为什么投简历?你看起来不像是适合做这个(岗位)的人。
我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职位所考虑的对象。但我还不死心,因为面试官表示,无论有没有通过面试,晚上都会接到短信通知。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穿着单薄的正装徘徊在街头,但在9点钟时,短信铃声响起,我还是收到了拒信。
我默默地背着包走去火车站,买了回程的高铁票。上火车后,突然发现邻座的女孩是几个月前面试遇到过的一个女生,她也来参加了那个国企的面试,也被拒绝了。她眼眶湿着问我: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在进步,但还是没有工作要我?是不是我努力的方向不对?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们一起默默地同路,下车。到站时已经是深夜,地铁停运,唯一的选择是坐黑车,和人拼车回去。黑车司机开价40,我摸口袋时才发现,身上只有最后的30元钱了。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窘迫”——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远在家乡的父母,自己的求职并不顺利。他们以我为骄傲,以为中国顶尖高校的毕业生一定找得到工作;他们也不知道,在大四过半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大多数应届生不会像我这样,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没有给我额外的生活费,而无论是印简历、置装、来回面试的交通,这些都需要钱。在这一刻,我发现坐黑车是避免露宿街头唯一的办法,但我这个月剩下的生活费还够不上车费。
我在路边坐了一夜,想了很多事,也可能是人生第一次,我对自己的个人价值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是否这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我在学校学习的所有知识,似乎并不能对工作有多大帮助?最后我又想,是真的一无是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吗,为什么要去投这个行政的岗位?
第二天,我搭早班公交车回了学校,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筛选每一个准备求职的岗位,问自己:这真的是你想要的、适合你发挥能力的工作么?最终,我取消了所有这些申请,在春节前没有再进行任何面试。
我用了一个春节的时间思考自己要做什么,以及适合做什么。到下学期开学时,下定决心只投某一种类型的岗位。开学后投了不到5份简历,到3月份时便有一份工作给了我offer,还是我很喜欢的一家公司。
如今我换了3份工作,在职场稳步发展,再也没有遇到过当年那样窘迫的情境。大概就是那个晚上,让我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任何没有找准方向的努力都是无效的;第二,当你非常努力、却反复碰壁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太笨或者努力得不够,你需要的是停下来,想清楚。
但也全靠那段非常努力而又非常绝望的经历,才会让我明白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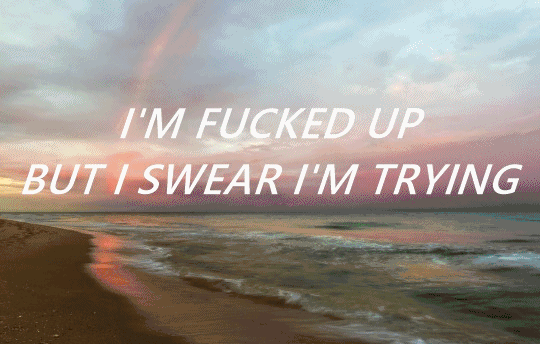
4
十年的喜欢不仅是在感动自己,
也让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我做过最努力的事情,是喜欢一个人。在大二那年我遇到了她,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
不想说“坚持”,因为一说坚持,仿佛我的喜欢就有种被迫的感觉。但其实喜欢就是自然而然发生,又自然而然持续的。又想说“坚持”,是因为我确实全力以赴地、用生命去喜欢过一个人。我也是女生,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大二的校际交流项目,她短期入住了我们寝室。她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随性但不随意,有一种我一直称之为“自由”的特质,让在流水线上长大的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灿烂的世界。
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能够永远在她身边,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事。但总觉得她是那么的美好和遥不可及,我太普通、太简单,还是个女生(她喜欢男生),这是根本没可能的事。但我无法说服自己的心,所以一开始,我只是暗暗地跟自己约定,尽我所能让她生活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