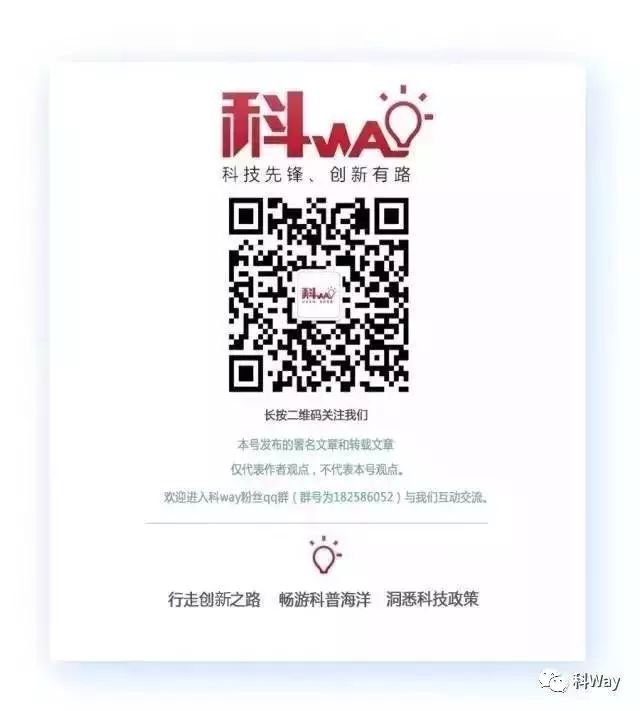上海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至5%的速度增长。我们每天扔垃圾,却很少关心垃圾去了哪里。事实上,垃圾是每个人、每座城,都不得不承受的重量。
此文共6320字,每个字都是诚意。
大约在2015年,一个名叫王久良的北漂摄影师,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为北京绘制了一张垃圾包围图。期间他共拍摄了近5000多张照片,并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很长时间内,这部纪录片在中国大陆地区禁播。
▲王久良《垃圾围城》纪录片图片
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现实情况严峻;二、我们无能为力。
比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的是垃圾制造的速度。早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 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以上海为例,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至5%的速度增长。
这个远远超过城市承受能力、也远远超过我国现有垃圾处理能力的数字像是一个无形的巨爪牢牢扣在苍穹之下。
每个人、每座城,都不得不承受。
每天一大早,上海浦东最东侧的曹路镇黎明村沿海滩地上就排满了一辆辆环卫转运车。空气质量好的时候,往海的对面一望,就能看到长兴岛。
黎明,因为地处上海本土最东侧,是全上海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也因为地处远郊,这片诗意的土地也成了城市生活垃圾最好的“藏身地”。
从1998年开始,黎明境内新建了两个生活垃圾处理厂,一个是占地500亩的黎明生活垃圾填埋场,另一个是2002年建立的美商国际集团生化处理厂。附近还有一个火葬场、一片墓地和养猪场。全部紧挨着农村住房,最近的只有5公里。
▲垃圾车正在倾倒垃圾
两家生活垃圾处理企业日处理垃圾分别为1500吨和1000吨。由于垃圾处理技术的限制和标准执行不够严格,在生活垃圾的处理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有害物质和恶臭气体,其浓度远远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高限值。海上一吹东风,金桥、合庆、高东、高行等几个镇都能闻到一股酸臭味,甚至张江、杨浦也时有所闻。
现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黎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华银锋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画面:2012夏天,在对原有垃圾填埋场和生化处理厂之间建设黎明资源再利用中心的过程中,气候闷热,整片作业区域酸臭味熏天,有时走着走着,感觉嘴里有什么东西,吐出来一看,一只苍蝇。
相比其他城市,上海的情况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1983年3月,由于垃圾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20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北京日产垃圾18400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高产量的垃圾直接导致北京不负重压,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像一个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垃圾填埋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渗滤液和溢出的填埋气。堆积数日甚至数年的垃圾分解后,伴随着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入渗,会产生棕黑色的垃圾渗滤液,俗称“垃圾汤”。
“处理这种垃圾渗滤液是世界难题,水质变化太大是难以达标的重要原因。”长期研究渗滤液处理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环境院副院长蔡辉说,垃圾渗滤液是高浓度的废水,受居民生活习惯影响,我国生活垃圾有机物、盐分含量较高,南北方垃圾渗滤液浓度又相差很大,同一填埋场的污染物浓度也会随着填埋龄和季节变化。而垃圾填埋场酸臭味的来源则是填埋气,据估算,1吨垃圾将产生100到140方垃圾填埋气,如果这些填埋气自然溢散,产生的臭气会对大气、臭氧及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除了一般生活垃圾,黎明还时常会接收到企图浑水摸鱼的建筑垃圾等
除了一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电子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工业垃圾……目前都缺少有效的处理,大都采用填埋的方式。
在今年5月4日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环保(固废)技术论坛上,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建筑垃圾专委会主任助理李文龙给出了一组数据: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国内建筑垃圾已占城市垃圾的70%。预计到2020年,中国还将新增建筑面积300亿平方米,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等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保守估计在15亿吨以上。
更可悲的是,由于我国对于垃圾处理管理不严、处理手段粗放,在利益的驱使下,“洋垃圾”会不择手段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电子垃圾为最。
今年2月,深圳海关对外通报,该关近日一举摧毁一个走私固废的犯罪网络,查获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废旧的电子产品等固体废物42吨。
在广州清远,电子垃圾拆解是一个有着约40年渊源的行业。国内外的电脑、显示器等电子零件通过集装箱在珠三角码头上岸后,最终会通过公路来到紧挨珠三角的龙塘、石角等镇。其中一部分流入再生资源基地等有正规牌照的拆解场,另一部分流入散落在村镇、公路周边角落的个体拆解户,由村民用人工拆解的方式将零件捣碎、拆卸,把有用的铜、铝等金属分离,无用的塑料就地焚烧。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垃圾也越来越多
经过多年的演变,电子垃圾拆解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2007年之后,当地政府多次打击非法个体拆解户,无奈从业者甚多、行业过于庞大,整治行动结束后屡屡出现反弹。2014年,当地还发生过拆解从业者集中到镇上访的事件。
▲有些人闻着垃圾的臭味抱怨,有些人靠着垃圾谋生,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垃圾的包围之下
北上广不是个例。有数据显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经超过80亿吨。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80万亩。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何者更重要?”这是辩论场上的一个经典辩题。如今想来,甚是可笑。探讨这个问题,就好像是问一个男人:“你妈和你女朋友同时掉进水里,先救哪个?”
这不是一道单选题。与其左右纠结、反复权衡,不如拿出点行动力。
一直到2010年,在对垃圾焚烧技术已经成熟掌握的前提下,由上海浦东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投资12.16亿元,启动了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方案策划工作。2010年12月项目获批,2014年8月正式商业运行。
▲新黎明俯瞰图
新黎明占地约1100亩,包括了资源再利用中心(编者注:即垃圾焚烧发电厂)、填埋场(编者注:原垃圾填埋场已封场,目前主要处理填埋垃圾的填埋气问题)、有机质固废处理厂、填埋气综合利用厂、渗沥液处理站等几大功能区。除此之外,全是茂盛的植被。傍晚时分,附近的村民甚至会来这里散步,“感觉垃圾场还挺高大上。”
▲远远看去,改建后的黎明和大学园区相差无几
有人说,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日产垃圾数量更庞大,垃圾场的改建是不是只是面子工程?现在垃圾不填埋改用焚烧,那么焚烧后产生的二恶英不是更恐怖吗?
新黎明正式运行之前,华银锋跑到德国、芬兰等发达国家考察,与垃圾有了十来年接触的华银锋大吃一惊。
国际上,垃圾焚烧是一种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在日本,垃圾焚烧厂直接建造在市中心,在东京都的23个区中总计21个垃圾焚烧厂。从90年代开始,日本以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焚烧厂效率,降低了垃圾焚烧对环境和居民健康的影响。其垃圾焚烧厂不仅毫无异味,甚至还设有市民健康体检中心、游泳池和健身中心。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实时空气质量、垃圾焚烧厂每天的垃圾吞吐量等数据全部向社会公开,而且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发电也已经成为东京都重要的电力供应来源。
“科技的发展以及严格执行环保标准确实让垃圾焚烧成为可靠、安全、高效的垃圾处理方式。”华银锋说。
▲在黎明,工作人员坐在控制室中监控焚烧情况,各类数据实时传输至操作台
▲每天一大早,2000吨的垃圾从城市的各个居民楼里被装进垃圾车,再被转运到黎明,在卸料大厅将整车的垃圾倾倒入垃圾坑
▲坑内一只巨大的爪状机械吊臂对垃圾进行混拌,使得垃圾的湿度更为均匀,以便能够充分燃烧
▲操控台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大抓斗。这里的玻璃全密封,可以有效隔绝垃圾的臭气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能从垃圾的成色和臭酸味中判断出是“新垃圾”还是“旧垃圾”。大约2-3天后,巨大的机械爪将已发酵完成的“旧垃圾”投入焚烧炉中进行焚烧。黎明最新的焚烧炉可通过850℃以上的高温对垃圾进行焚烧,当垃圾热值不够时,会自动添加柴油助燃。“炉膛内的温度最高可达1100℃。”华银锋说,垃圾燃烧后产生的热值每年可发电上网约为2.4亿度,不但满足了黎明自身运作的用电需求,还可以向社会供电。
▲焚烧炉内的熊熊烈火
“焚烧炉内的高温燃烧能够抑制二恶英的产生,炉膛内喷射的尿素能够去除氮氧化物,燃烧后产生的高温烟气经过减温塔的快速冷却有利于提高酸性物质的脱出效率。”华银锋说,这些都是国际上最先进且普遍运用的垃圾焚烧技术,而黎明采用的工艺设备也都来自日本和欧洲,可以保证“万无一失”。此外,水银、氯化氢、硫氧化合物等有害物质也会利用干石灰和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湿式洗涤塔、活性炭固定床等设备进行处理。经过处理的废气最终以近乎“无色无味”的状态通过60米高的烟囱排出。“我们的烟囱看不到烟。”华银锋说,“烟气处理达到欧盟2000的排放标准,部分指标优于欧盟2000标准。可以说一点味道也没有。”
▲垃圾焚烧必须经过层层步骤
经过这一系列的焚烧步骤之后,垃圾的体积变成最初体积的约1/40,实现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以及可持续的发展。
但技术层面的趋同或者超越,并没有根治我国的垃圾围城之困。
“要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越来越多,超过了设备的负荷怎么办?炉子都不敢停。”华银锋无奈得说。
目前,除了黎明,上海目前还有7座这样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分别位于江桥、金山、老港一期、奉贤、松江、崇明和御桥、全部已经饱和运行。早前,由于垃圾产量的增加,江桥焚烧场计划在原址上进行扩建,而在该场附近已经建成密集的居民区,扩建难度甚大。
▲黎明内景
如果仔细考察德国、日本等国的垃圾处理经验,不难发现,处理技术及工艺的提升只是其“表”,解决问题的核心实质在于全社会严格执行的垃圾分类制度。早在上世纪,德国、日本就出台了极其严苛的垃圾分类标准,并逐渐养成国人绝不买非刚需品的“极简主义”。
反观中国,垃圾处理的各个关键“点”被简单又粗暴得压缩在了最末端。
“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应该是目前唯一与其现代化城市水平不相符合的方面。”曾有人这么评价。早在2000年,上海被列为国家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再次推行垃圾分类。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
“垃圾一定要分类。我们也希望能有机会参与源头的垃圾分类。”华银锋说,“现在居民一包垃圾袋一扔完事,垃圾袋里面可能有一次性餐盒、皮鞋、电池、玻璃酒瓶等等,到了我们这里,全部烧掉。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事实上,不同属性的垃圾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从而实现资源的再循环和垃圾的减量化。比如,厨余垃圾更适合填埋或堆肥、部分简单工业垃圾可以拆解再利用,而不是一烧了事。但目前,就算源头做到了分类,环卫工人在收集垃圾时又将全部的垃圾统一“打包”拉走,到了垃圾焚烧厂还是“一锅杂汤”。
▲垃圾坑中的“一锅杂汤”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卫工作都属于公益事业,由地方环卫部门主导,基本上是地方环卫部门“大包干”,导致地方环卫部门管理机构庞大、资金来源单一、管理效率低下、环卫保洁及垃圾收运处理缺乏市场竞争,这些是传统环卫管理运行机制中始终无法有效破解的难题。
垃圾分类到底由谁来做、怎么做?谁又需要对未分类的垃圾负责?
可以说,没有垃圾分类的垃圾处理只是“舍本逐末”,无法根治“垃圾围城”的尴尬现状。
出国考察期间,让华银锋百思不得其解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国外的垃圾焚烧厂可以盈利?
华银锋给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一个垃圾焚烧厂一年基本必须保证330天的运行时间,行业内考核满8000小时,每年安排一次检修得停炉20天,目前所有设备已经处于负荷临界点。“如果不考虑设备折旧,一年运行成本就高达1.2亿元人民币,其中1200万元用于设备改造。”越是设备、工艺先进的垃圾焚烧厂,运行成本就越高。
▲华银锋和同事们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左二为华银锋
如果没有政府买单,如此高额的运营成本有谁可以负担得起?
事实上,国外的各类垃圾处理终端不但自负盈亏,甚至推动了整个循环经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许多城市的垃圾处理也与我国目前情况一样,垃圾处理厂无法容纳不断增多的生活垃圾,且带来水环境和空气的污染。为此,德国联邦政府于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厂家必须对其产品包装全面负责。
随后,工业界成立了垃圾回收和再加工系统(SDS),主要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和再加工工作。每年各地政府会给每个家庭印发专门《垃圾分类说明》和《垃圾清理日程表》,要求居民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分类。清运车会按照时间表,到居民区收运各类垃圾。
与此同时,垃圾焚烧工厂、垃圾机械及生物预处理工厂等专门处理工业废物的工厂得到迅猛发展。到今天,德国不但实现了金属、纺织物以及纸制品的回收外,其他可循环使用的材料也必须在进行分类收集后重新进入经济循环。德国也因此形成了一个营业额超过2000亿欧元的生态垃圾经济产业。该产业产值每年增长14%,为大约25万人创造了就业岗位。
黎明也在尝试资源再利用。“除了热能,垃圾焚烧后还会产生废渣和飞灰两种物质,废渣要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进行熔融处理,变成砂状的熔渣,可经过再次加工变成建筑材料。”华银锋说,黎明园区内的道路砖头全是由垃圾废渣做成的。
▲但无奈的是,这些尝试大多停留在“展示”层面,而没有形成一个产业链。“我也想做资源再利用,但缺少条件。”华银锋欲言又止
▲焚烧后的熔渣从一个个小窗口被送出来
▲随后经由抓斗运至卡车,再清运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在上海,因为没有专业处理各类分类垃圾的企业或机构,分类后的垃圾没有合适的去处,最后还是会回到焚烧厂一锅烧;而专业从事分类垃圾处理和资源回收的企业或机构则因为没有足够的垃圾来源而难以存活。
“垃圾处理也应考虑价值经济性,在没有一定数量支撑的前提下,回收处理的成本是市场难以承受的。”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说,以报纸回收为例,如果不能保持固定的数量,回收旧报纸再生新报纸的成本远大于直接生产新报纸。
除了一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电子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工业垃圾……目前都缺少有效的处理,大都采用填埋的方式。面对种类繁多的各类垃圾,再有钱的政府也不可能全包,还需要调动企业、政府、社会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去改善。在一个社会治理成熟且完善的自生体系内,媒体、民众、学者、企业、政府各自履行着社会权力和职责,从而形成一个闭环。
行动者已经在路上,一个叫“绿色地球”的创业公司在成都率先做了起来。成立于2008年的“绿色地球”效法美国“再生银行”的理念,为每户开设账户,详细指引垃圾分类,把回馈绑定在积分体系上。居民每投递100克可再生垃圾积1分,用积分可以兑换香皂、电影票,手机等生活用品,在2011年以前,“绿色地球”一直在成都尝试着 “概念性”的推广。
2011年,成都试点垃圾分类,成都市锦江区主动找到绿色地球,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投入400万元购买为期3年的服务。绿色地球承诺在2012年达到5万用户,2013年8万用户,长线目标则是覆盖整个成都市,成为中国城市提供生活垃圾回收的有效模板。到2014年,绿色地球每天收运垃圾超过3吨,其中可再生垃圾率超过90%。
“在获得政府采购后,我们回收的垃圾越来越多,最终和成都最大的纸厂华侨凤凰纸业坐在了谈判桌上。以牛奶盒为例,最高可以卖到800元一吨。当然,在达到一定的量后,上海的公司也愿意接受,甚至可以卖到1800-2000元一吨。”其创始人汪剑超说,除了垃圾再销售环节的盈利,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其他渠道的商业价值也开始凸显,已有银行主动与其合作。
根据2015年的财报,在不计算每月在做新投资的情况下,绿色地球从2014年6月开始达到收支平衡。政府购买在其收入中的占比在逐步减小。而垃圾再销售及其他盈利点则逐步扩大。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垃圾的资源再利用不但可以实现市场化而且潜力巨大。有关专家表示,垃圾产业化其前提有三:一是垃圾成分有利于资源化;二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垃圾收费制度和分类收集系统;三是完善的产业政策,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完善。
目前上海市的垃圾成分和特性已经达到了垃圾资源化的要求。成都已经成功,上海还在等待什么?
毕竟,产于土地上的垃圾也终将回归土地,永远不会凭空消失。

此文原刊于《浦东科技》杂志,本文略有修改。
文/金婉霞
美编/毛毛大徒弟
图/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