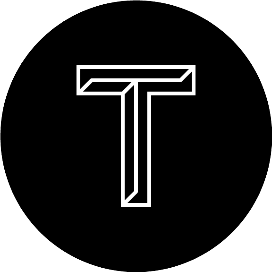我第一次见到窦靖童,还是疫情前。当时,我去山下学堂看第一届学员的毕业演出。那是一出以色列人编剧的话剧,叫《冬天的葬礼》。剧情晦涩,表演夸张,但依然能看出来是一个关于迷茫和寻找的故事。演出结束,众人鱼贯而出,挤在剧院外的图书间听陈坤讲话。很快,周迅也来了,笑嘻嘻地站在一侧。窦靖童站在更远的角落里,很快就不见了。
即便如此,她还是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见之下,她的外形和本人的气质有奇妙的戏剧张力:一头粉色短发,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皮衣,酷极了,像真的要去参加「冬天的葬礼」的黑帮分子。但出人意料的是,她的神情并不酷,甚至有点羞怯,像个很好说话的人 —— 如果一个人很好说话,却又入了黑帮,那就极有可能是一个动人的悲剧故事。
另一个印象来自窦靖童的作品。在《幻乐之城》里,她发布过一支 MV,叫《幻月》,有一段类似「猴子捞月」的剧情设计,透出一丝向内探索的意味。当时,窦靖童不过 20 岁出头。
因为她实在太年轻了,你会感到好奇,这样的创作与表达,确实不俗,但到底是一个年轻人的新鲜刻奇而已,还是一种属灵的天赋?

我也断断续续关注过她的影视作品。有些电影是在电影院看的,有些作品则是留在互联网的片段和零碎剧情。那些年轻女孩的角色,年龄、职业各不相同,但是她们的生命状态出奇地一致 —— 都是一些有内在的不安,不断在寻找自己,想要突破某种禁锢、重回内心之家的女孩。
窦靖童并非经过系统训练的职业演员。通常来说,导演启用这样的演员,一定会选择提炼她本人和角色之间最相通的特质。如果窦靖童是一个在寻觅着的人,导演就不会贸然安排她饰演一个老练笃定的角色;如果她非常天真,通常也不会有一个城府深的角色找上门。或者可以这样理解:窦靖童的表演中,有她自己,至少是一部分自己。
她在不安什么?她在寻觅什么?窦靖童本人也未必说得清道得明。但是,如果她确如《幻月》里呈现的那样,有很强的灵性,她就注定要去寻找 —— 假装不找,或者找不到,都会带来灵性的痛苦。
6 年之后,2024 年夏末,我再一次见到窦靖童的时候,她比起当年已经有所不同。她的短发早已染回黑色,开始穿裙子,开始写中文歌,开始唱中文歌。她好像在小心翼翼地捅破一些由他人
(但终归还是由自己)
设定的边界,想因此离自己所不了解但又真实存在的那个「窦靖童」,更近一点。

穿黑色皮衣的那个窦靖童,21 岁。会穿白色羽毛裙的这个窦靖童,27 岁。有道是,长谷川天,27 岁,身心俱疲。27 岁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年纪,它不像 18 岁那么欢天喜地,也不像 30 岁那么郑重其事,但稍有不慎,一个人就会在 27 岁崴一下,不然哪里来的著名的「27 岁俱乐部」。基本上,27 岁是正式进入成年人世界的「临门一脚」,你面前有一扇门,但你手里有一大串钥匙,哐当作响,你不确定应该用哪一把来开门。万一选错了钥匙,你也许在开门的过程里就已经老了。
窦靖童就正好在这样一个年纪。两小时的聊天,也从这个轻灵又迷惘的 27 岁开始。没有想到的是,窦靖童极其诚实,开口第一句,就是承认自己在 25 岁那年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而那场危机的影响持续至今,深刻地改变着她的生活、她和音乐的关系,以及她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当然,她也有必须隐藏的,危机的起承转合是抽象的,其中的具体事件和细枝末节,不足为外人道。
为了避免误读和被误读,这个部分,我们选择以口述的形式记录。如果再过 6 年,窦靖童看到它,也可能会心一笑。
最后说几个有意思的细节。
其一,我忍不住一定要问那个著名的问题 ——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她著名的母亲在她现在这个年纪,「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女儿 27 岁的最大烦恼则是,「太害怕要做的这个演唱会了」。
其二,窦靖童最近几年读过看过的文艺作品清单不算短,有限时间里能得知的是 ——《纽约提喻法》《暖暖内含光》《完美的日子》《百年孤独》《雪国》,以及《悉达多》。我终于看到了黑塞的名字,这个作家一生都在书写挣扎和寻觅,一生都画同一幅画 —— 有绿色树冠和红色房顶的家。窦靖童不光看过他的小说,还找来黑塞的纪录片。她甚至好奇,如果有机会能和黑塞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是什么感觉。

最后,我问她,在所有演过的影视作品或者 MV 里,选一个最能代表自己的场景或者画面,会是什么?
窦靖童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了。
「就是在《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里面,有一个片段,是一个梦境,她在一个卖假发的人那里看电视,电视里有一个假发广告,说,你想改变你自己吗?你讨厌你现在自己的样子吗?请拨打
(号码)
多少多少。梦里,她就坐到卖假发的这个人身边,然后他们有一个对话 —— 就这个场景。」
你如果看过《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又读过荣格,你会发现,窦靖童的这个答案实在太荣格了。荣格讲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有一种已经被父母创造出来的生活氛围,但这种生活氛围不见得适合你,你成年后,就需要走出来,为自己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全新的生活氛围。这个创造的过程,就是成年。
以下是窦靖童的自述。

你刚才说,二十七八岁可能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精神上的成年礼,才是一个人真正为自己的道路做选择的时候。这个我很有共鸣。
18 岁或者 20 岁当年,我的确没有那种感受,好像我就长大了 ——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长大了」是什么意思。但我自己感觉,我大概是从 25 岁开始
(长大)
的。在那之前,我一直活在一个对自己不是很了解的状态里。我会对自己有很多的假设 —— 我觉得我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是那个样子 …… 我
(会)
以此为前提,去践行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但总是会被打脸,或者会有一些错愕的时刻。
(那些时刻)
会让你觉得,怎么回事?我难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刚开始那几次,我总是会把这类事情扫到地毯下面,当做无事发生,直到它们堆积到临界点,我才不得不去跟自己有个对话,或者去面对一些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很吓人的。
我是个冲突回避型的人。害怕冲突,很难去面对那些比较真实但是也比较危险的东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不善良,我会有一个定义,然后会有一系列的行为。比如我觉得对一个人好,就是什么都说「好」;作为一个好人,就是不拒绝别人。你可能会觉得,怎么
(窦靖童)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它就是很难。尤其面对活生生的人,就很难去说「不」。我总是在刻意地回避,或者去营造一个假的和谐状态。其实到后来你会意识到,如果没有所谓的智慧,你其实根本看不到当下你以为的「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是我这两三年的内心变化,也算一种内在的成长。我试着去解释一下。
以前,我一直认为大家要在一块儿。如果我很欣赏一个人,我会神化这个人,我会觉得他 / 她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会觉得,我要走的,跟他 / 她要走的,是同路的。但其实,我自己的这条路,只有我自己可以走 —— 这是我之前无法接受的。我看待事情的方式和别人看待事情的方式,注定是不一样的;就算我们再好,对事物都不可能达成百分之百的同频理解。

所以,在我的生活达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我和生命中一直都很好的人,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其实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只是我选择不去看到它,也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 有时候,可能要各自走各自的路。
我不是 180 度大转变的。不是说,今天我决定不再妥协,我就真的再也不妥协了 —— 这个态度是一种慢慢培养出来的习惯。
(但)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把这些感受写进我的歌里。它现在还不够明显。拿滑板举例吧,学习滑板最简单的动作就是「跳」,练习了 100 次以后,可能无意识地,你就做成功了一次,但不代表你下一次又可以成功。我也是这样,找到了一点灵光乍现的感觉,但是还不够确认,还摸不太清楚。
而且吧,它
(对于感受的捕捉)
和「肌肉记忆」还不太一样。它
其实贯穿着所有的平衡。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去找这个平衡。这是我现在生活里一个很大的重点。
几年前,我给电影《七月与安生》做音乐。当时陈可辛导演问我,觉得自己身上是七月更多一些,还是安生更多一些。当时我们都觉得,是安生更多一些。他说我「有态度,但没有刺」。其实,我肯定有刺,只是我把自己隐藏得比较好罢了。
和那时候相比,我肯定是有变化的,而且是很大的变化。
光从音乐来讲,我看待音乐的方式已经完全变了。以前我会神化音乐,我会把音乐分为酷的音乐、不酷的音乐,我会用音乐去彰显自己的某一些特点。对那时候的我来说,音乐就像一件穿在身上很酷的皮夹克。对,音乐就是一件最酷的时尚单品,有这种感觉 —— 是个用来嘚瑟的东西。
后来,这个事情就有一点撞到墙了 —— 他的皮夹克好看,她的皮夹克也好看,哪个更好看?就是你懂吗,做音乐变成了哪件皮夹克更好看,变成了我做的音乐到底够不够酷,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很厉害。我可能是想要证明自己,但是证明了之后呢?我会更开心吗?我会满足于现在这种别人对我的看法吗?他们的看法能给我带来什么不一样呢?

第二张专辑《Kids Only》之后,距离第三张专辑《GSG MIXTAPE》,有 3 年。这 3 年,我觉得自己遇到了障碍。做音乐变成了一件枯燥、让人很孤单,很寂寞的事。它变成了喂食自我的一种工具。
我所说的孤独,还不是那种歌手面对空荡荡的舞台下方的孤独。我那段时间的孤独,更多地来自 —— 我也很难形容清楚 —— 就是某些东西好像需要调整,好像不大对味儿。这些东西有时候不是跟音乐直接相关的,
(而是)
更多地跟人相关,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音乐,我要用音乐做什么,我怎么看待我自己。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的思考和探索,会给音乐带来非常直接的影响。
归根结底,音乐只不过是一种呈现「你是谁」的方式。所以,如果我有一些东西是不敢让别人知道的,或者我对自己不够诚实,在音乐里是可以听出来的。
那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其实是我内心的信念:不再对自己撒谎,不再糊弄自己,也不能再把音乐当成一件时尚单品。换句话说就是,我想用音乐做什么,或者,我觉得音乐是什么?
慢慢地,我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 音乐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没有任何性质,它的性质是你赋予的。你可以用它去传递这样的信息,也可以用它去传递那样的信息。
对我来讲,我也慢慢找到了自己想用这个工具去做的事。有两方面。
一方面,要用音乐去打破自己的一些习惯。以前我对音乐有执念,比如我要做小众音乐,我要做英文歌,但
(后来)
我就会问自己,能不能不只是「小众」?能不能不只是「英文歌」,否则路只会越走越窄。
另一方面,我相信愿力这个事情。我希望跟更多人产生连接。我做音乐不是给我自己听的,对吧?我既然有这种渴望,也有平台,就想让更多人能听到,能听明白。
以前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音乐人 —— 这是我确定的使命和确定的道路。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讲,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活着,不是为了要做很好的音乐;但我生活中所有的其他事情,都会不断地为音乐添加柴火。没有生活,就没有音乐。如果一个人很单薄,音乐其实也不会丰富到哪里去。
这些内心发生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跟我父母聊过,他们也不知道。我好像没有跟任何人聊过这个。父母从小对我就是散养,我不觉得他们有把自己那一套强加于我,
(我的人生)
肯定是相对自由一些的;但我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没人给我一条明确的路,我面前就是一片「荒原」—— 我这么走,再绕个弯回来,都可以,都试试 —— 其实也是一种迷惘。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希望,就是,「要么你直接告诉我吧」。但不行。还是要自己去经历,得自己做决定。
2023 年,我出了第四张专辑《春游》。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徘徊着一个想法:希望发一张轻松的东西,也能反映我性格上的特点。但不是一下子把自己都敞开 —— 我害怕那种猛然打开的感觉。打开之后会怎么样呢?不知道。也正是因为不知道会怎么样才害怕。所以,我总是开一下,然后关上,再开一下,然后又关上 …… 这是我的习惯,或者说我的习性。

这次的新专辑,尤其《空中飞人》这首歌,也是一个「打开」的过程。我写它的时候,整个人都很拧巴,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都好像在说「不要这么做」。录这首歌的过程也很难受,几乎每唱一句,我都会自问,「要这样唱吗?」或者「这个旋律会不会太过
(流行)
了?要不然我再往回收一收?」对我来说,(这种创作和演唱)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空间。
但是,我想告别以前的一些框架,我想呼吸外面的空气。我以前一直住在一个瓶子里,我想击碎这个瓶子,对这个瓶子说拜拜。
写完和录完《空中飞人》之后,我其实有一种幸福感。我的老师跟我讲过一个例子:黑着灯的时候,地上有一根绳子,看不到的人会把它误认为一条蛇。当你认为那是一条蛇的时候,心里产生的恐惧是非常真实的 —— 直到有人把灯打开,你发现那就是一根绳子,恐惧就突然一下都消失了。
《空中飞人》就是一个开灯的动作吧,我觉得。
我最早接触音乐的时候,觉得做小众比较酷,或者比较「高级」。这个概念束缚住了我,是它让我在写《空中飞人》的时候浑身难受,因为我的脑子里还是有这个概念。但其实我自己的喜好不是这样的啊,别人做的流行音乐我可以完全地喜欢,太爱了,恨不得听一万遍。到我自己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做了流行,肯定会有一些人说我。这些东西是日积月累的一面高墙。我只能说,《空中飞人》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突破。我第一次试着去「破」了一下 —— 如果我不那么酷,也不会怎么样。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想「酷不酷」的事儿。
这两年,至少我自认为,我在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圈。这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地方。我在做专辑的时候,看到 David Bowie 的采访,他说,当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整个创作的过程非常舒适,你一点也没有觉得难受,那你应该就是在原地打转。他还说,如果你觉得双脚抓不着地,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似乎什么都摸不准,这个时候,你应该相信,自己正在做着一些突破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