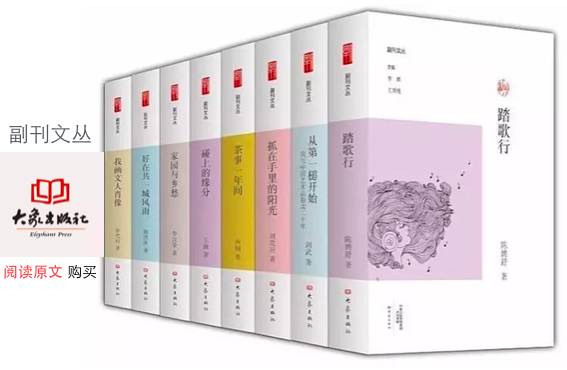墓碑不会战胜生命,因为两者之间没有战争
文 | 李辉
一直喜欢看探险和旅行的书,从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到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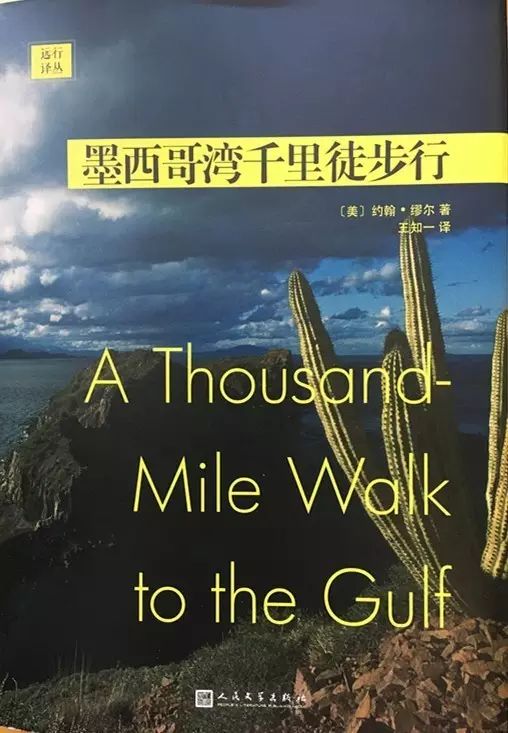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书影。
最近,“远行译丛”中的这本《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颇为喜欢。作者约翰·缪尔,被誉为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用优美笔调和精彩细节的勾勒,将一百多年前徒步旅行的过程,留存于这本已有百年历史的老书之中。
千里徒步,约翰·缪尔看到一片他觉得最美的波那文都墓地。伫望墓地,他看到的是生与死美丽的融合和交流 。下面这段文字,品味再三,为作者的这种感悟而赞叹:
让孩子们走入大自然,让他们看到死亡与生命美丽的融合和交流,它们不可分离的地快乐结合在一起,就像森林与草原、平地与高山、溪流与星星那样,孩子们就会了解死亡事实上并不痛苦,它跟生命一样美丽,坟墓并没有战胜生命,因为两者间从来没有战争。一切都如上帝安排的那样和谐。

1867年前后摄影师格利森拍摄的波那文都墓园。
波那文都墓园内的几座坟大部分都种上了花。通常,坟前靠近竖立的大理石墓碑旁边种着玉兰,坟后是一两株玫瑰,坟上或两边则是紫罗兰或鲜艳奇特的花朵。这一切都用黑色铁栏围住,那些坚固的铁杆可能是地狱战场上的矛刺或棍棒。
观察大自然如何勤勉地补救这些愚蠢的人工作物,着实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它腐蚀铁栏及大理石,把隆起的坟头渐渐铲平,好像是过重的泥块不应压在死者的身上。弯曲的绿草一棵接一棵长出来;种子默默无声地舞着柔软的翅膀飞来,把生命的至美带给人工的尘土;而壮盛的常青树枝干装饰着各种蕨类,树兰的帘幕更覆盖了所有一切——生命在各处滋长,消灭了人类的所有迷惑记忆。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第51页,美国约翰·缪尔著,王知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约翰·缪尔说得不错,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总是会感受到过去从未体验的东西。包括墓地。

黄永玉为沈从文墓地所题碑文,李辉 摄。

2014年陪同沈朝慧大姐在凤凰郊外拜谒沈从文。

2014年陕西汉中拜谒诸葛亮墓。

位于庐山植物园的陈寅恪夫妇墓碑,李辉 摄。

2016年12月6日,丁聪百年诞辰日在故乡枫泾墓地拜谒丁聪沈峻夫妇,李辉 摄。
我的母亲曾是小学教员,许多年里奔波于乡间。因而,我的童年是在不断流动的状态中度过的,而时间呆得最多的自然是农村。
与城里墓地不同,农村的田野最多,坟也最多,大多不集中,它们似是被撤在荒野,星星点点,孤零零的。除了一年一度清明扫墓时培培新土外,人们很少光顾它们,一般来说它们总是显得破败、寂寞、荒凉。
按照我们湖北家乡一带的习俗惯,好像是在人被埋七天或多少天后,亲朋好友应该夜间去祭奠。祭奠往往要延续一整夜。在这个夜晚,死者的灵魂会走出坟墓,大人说,年纪越小,心越诚,就能看到鬼的影子,看到他吃亲人送来的食物。
后来从书上得知,佛教中有“七七”之说,人在死去之后,到第七个七日时,必定会重生他处。按照佛经解释,人生有六道流转,在由死至生之间存在着“中阴身”,以求再生。每七日为一期,如不得生缘,就再延续,最终到四十九天时便再生。生者在此期间需要做超度、祭奠等。我想,我们那里乡间的习俗,想必与此有关。
曾记得十岁之前,在一个无月的夜晚,我随一个小伙伴去祭奠他的爷爷。新坟在一处山冈上,并不孤单,周围散布着不少旧坟。完成例行的摆放祭品鞠躬放鞭炮之后,所有人就远离坟墓,躲到低洼处,等着亡灵走出来喝酒,品尝家人的祭品。夜很深,很静,墓前两支蜡烛在夜风里飘飘忽忽,神秘得很。我有些害怕,紧偎在大人怀里,但眼睛还是死死盯住前方,生怕漏过神秘的那一瞬间。
那一夜就在等待中熬着。“瞧,爷爷出来了!”小伙伴惊奇地轻叫一声,立即被大人捂住嘴巴,说是怕惊动亡灵。可是我尽力睁大眼睛,还是什么也没看见。是心不诚,还是根本就没有,我说不清楚。但我后来宁愿相信小伙伴的眼睛,我想,即便根本没有,他也能从他的错觉中得到安慰。在这样的场合,表面上看,人们是为了亡灵,其实依我看更是为了他们的愿望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
这也许就是人们创造墓地的意义所在。

1997年拍摄的维也纳墓地之一。

1997拍摄的维也纳墓地之二。
诚如约翰·缪尔所言,坟墓为死者而修,更大程度上却是为了生者。看到它们,生者往往看到的是他们自己。记忆,愿望,情绪,生者生活中种种形态,在墓地里闪烁着光影。鲁迅把他的旧文汇编成册,命名为《坟》,就明明白白地说过,他“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方面是为了埋葬,一方面则是为了留恋。
埋葬的是过去,留恋的也是过去,但它们都属于生者的现在。墓地就具有这样的双重意义,它既代表生,又代表死。当你把目光注视着墓地时,就仿佛能听到生与死的对话,无声,却并非空白一片。说得再明白一点儿,在我看来,墓地的每一座坟丘,每一块墓碑,是生与死之间的门槛,是两者拥抱的空间。生者由此表明跨入另一世界,而死者也由此意味着与生者保持了持久的联系。
于是,走进墓地,生者看到的不仅是死者的影子,更有自己情绪的波动。实际上,生者之所以常常光顾墓地,之所以把墓地作为永恒的话题,与其说是为了死者,不如说更是为了自己生命情绪的某种平衡。

在卢森堡二战美军墓地,拜谒巴顿将军。

位于台北阳明山的阎锡山墓地。

2001年,来到美国弗农山庄安葬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墓地。

2014年8月在英国牛津郡拜谒奥威尔。
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要使自己习惯死亡,唯一的办法就是更靠近它。”但他说的只是墓地的一种哲学意义。更多的时候,墓地是和人的感伤紧紧相连的,在文学家那里,则是常常借墓地来渲染感伤。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撰写萧乾先生传记《浪迹天涯》。二战爆发后,萧乾在英国生活七年,曾在剑桥大学潜心研究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晚年,他和夫人文洁若一起联袂翻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圆了他当年的梦想。
萧乾告诉我,二战结束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特意前往茵梦湖畔寻访乔伊斯墓地。走进墓地,他在墓碑之间徘徊,从依稀可见的墓文中寻找乔伊斯的名字。他敲开管理墓地人的房门,走出一位身穿粉红衫的小女孩,她带领萧乾走到乔伊斯的墓前。在四周都是大理石的墓丛中,出现在他面前的不过是一小方块灰石块,上面刻着: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
乔伊斯对墓地的描写也十分优美。他在小说《死者》结尾部分写道:
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朦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第一片地方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落在香农可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学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地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死者》)
我读过的一些描写墓地的作品,乔伊斯的这段文字,恐怕算颇具感伤也颇为优美的描写。自读过这段文字之后,我的印象里,感伤与墓地就是一体。
第一次走进欧洲墓地,是在瑞典旅行期间。

1992年在瑞典乡村教堂旁的墓地。
我在瑞典的日子里,去过不下十处墓地,或在城市中央,或在乡村,或在湖畔。无一例外,它们都在教堂附近。有时匆匆一瞥,有时悠闲自在,便独自一人如同观光一样在里面缓行,还不时拍摄几张照片,抄录几句碑文。瑞典墓地给我另外一种感觉。没有荒凉,甚或没有感伤,而是一种平静下的和谐。

位于哥德堡的墓地一瞥,李辉 摄。
去得最多的一个墓地在哥德堡,它就在我居住的瑞典朋友家附近,有好几个早上,我到那里散步。在我所见过的墓地里,这座最大,据说也是哥德堡城最大的。大约上千座坟墓,有规则地排列着。墓地以一座小丘为中心,四周则为平地。这是一块有很久历史的墓地,我曾看到十八世纪的墓碑。当年修建它时,想必属于郊区,但如今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公路、住宅区、商店与它相伴,它完全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部分。
墓地中央,有一处喷水雕塑,阳光下,水雾透明而飘逸。墓地非常整洁,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处水并或自来水龙头,并备有水桶,供每日前来扫墓的人使用。每一处墓碑前,均留有一小块地,用以种植花草。这是春天,鲜花已经开放,和身旁水灵灵的嫩绿一起,点缀着墓地,渲染出暖意。早上刚刚浇过水的花草,更显得鲜活明快。这里距海不远,一群群海鸥,飞来,又飞去。
几乎每一块墓碑,都是一个雕塑,但形状不同,大小各异。大者是一门石屋,最小者只是小小一个十字架。精致者为铜雕塑,或是身有双翼的小天使,或是狮身人面像,或是海鸥和我叫不出名字的鸟。至朴者,只是一块未做任何雕琢的礁石。
最有特色的一处墓碑前,没有花草,但却摆放着几个大小不一的海螺。死者一定是位水手或渔民,他的亲人愿意他在宁静的世界里,仍然聆听大海的声音。还有最为简单的碑文,上面只刻着三个字母,没有生卒日期,也没有多余的装饰。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庞杂的墓地,但在清新的空气中,在一片片花草点缀下,它们显得和谐而具有艺术氛围。

布拉格郊外犹太人墓地,卡夫卡一家人合葬一起的墓碑,李辉 摄。

布拉格威舍堡墓地,著名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墓碑与教堂相映衬,李辉 摄。
这里感觉不出阴森和荒凉,与周围流动的车与人,与每日变化跳跃着的世界,也没有形成强烈的明暗反差。相反,却有生者创造出来的温馨。看来,墓地在瑞典人手中。不是渲染感伤。瑞典给我的总的感觉是静多于动,感情真挚但有节制,并不随意挥洒。对他们而言,生活需要平静与安适,需要艺术,纪念死者也同样如此。这样,创造墓地,就是充实自己的生命,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墓地也自然而然成为城市的一个场景。
我看到人们不时驾车或步行来到这里。
一位老太太,年过古稀。她手拿小铲,正在修整花草。看到我留心地观看每一块墓碑,她便站起来,微笑着等候我走过去,然后热情地指着墓碑和我交谈。但她只会讲瑞典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听出“爸爸、妈妈”的发音。我明白她是说这是她爸爸妈妈的墓。看得出,她很高兴我这样一个东方人,能来观看她父母的墓碑,能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和她分享墓地的温馨。
去瑞典之前,我翻译的英国作家布瑞南的散文集《枯季思絮》,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其中有一段也写到墓地:
世界上最美的墓地是在乔治亚州的萨凡纳。苍老的灰色墓碑,躺卧于绿草之间,生机勃勃的橡树,低垂下蒙蒙长枝,墓碑上笼罩着树的影子,布满西班牙苔藓。在这样的地方,死亡既富有诗意,又合乎自然。
(《枯季思絮》 )
他对墓地氛围的描述,与我在瑞典看到的墓地,颇为贴切。
这些年,时常会去走进不同墓地,拜谒亲人和前辈,在墓碑前献花,鞠躬。最让人为之痛苦的是,不到十年时间,妹妹、父亲、哥哥相继去世。不过,我们把他们一起安葬在湖北襄阳的同一个墓地。这样,他们三个人相聚一起,不会寂寞。他们也会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与生者对话。

2007年我们兄妹三人与父母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父亲、哥哥、妹妹一起安葬于襄阳这片墓地,李辉 摄。
清明将至,又是走进墓地祭扫的日子。约翰·缪尔说得多好:“让他们看到死亡与生命美丽的融合和交流,它们不可分离的地快乐结合在一起,就像森林与草原、平地与高山、溪流与星星那样……”
完稿于2017年3月, 北京看云斋
-END-
▌版权声明:六根为一点号签约作者。六根文章全部首发于一点号,除一点号与六根公众号外,未在其它任何平台开设六根账号,也未授权其它任何渠道转发六根文章,擅自以六根名义转发者均为盗版。
六根者谁?
李辉 叶匡政 绿茶 韩浩月 潘采夫 武云溥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微信号:liugenren
长按二维码关注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