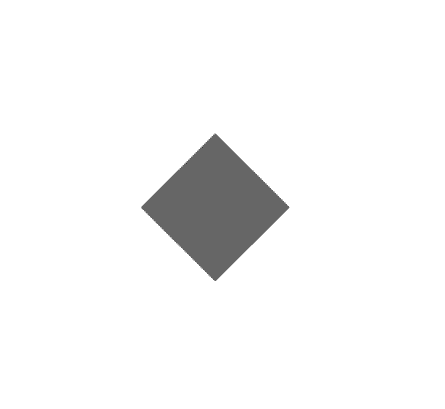欲望得以满足带来的幸福是加法,因为那只能使一个人感到幸福。而“给予”创造的幸福是乘法,因为它使更多人感到幸福。
在日本, 有一家制造无尘粉笔的工厂,工厂比邻一所残疾人学校。 1959年,工厂应学校的要求,聘用了该校两名应届毕业生。这两名年轻人来到工厂后,工作异常勤奋,有时午饭铃声响了也不停下手中的活计。他们的表现感动了厂里上上下下。
从此,这家粉笔厂每年都从这所学校招聘毕业生。一年又一年,渐渐地,这家工厂在日本无尘粉笔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市场领导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竟有70%的员工都带有某种残疾。
一次年底职工聚会,工厂的总经理恰好坐在一位寺庙住持身旁。他问住持:“在我厂里做事的这些残疾人,看上去比那些在福利院的残疾人更幸福。他们每天早上要乘拥挤的火车来上班,却从不迟到,而且工作起来很卖命,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住持沉思了一会儿,平静地答道:
难道你认为拥有物质和金钱就会让人觉得幸福吗?
有四样东西可以让人获得终极幸福:
被爱、受到赞美、为他人服务、被他人需要
。在你的工厂,员工在工作中至少能获得其中的三样,大概这就是他们感到幸福的原因吧。”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管理的本质在于创造幸福
。
一百个人也许有一百种理解,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者不同地点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幸福感”。
通俗的看法认为幸福与个人欲望得到满足的程度有关。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例如,对一名刚参加工作并渴望拥有一套住房的年轻人来说,买彩票中了一套房子会令他感到非常幸福;那么换作一位房地产大亨呢?他未必觉得这有多幸福,除非这套房子是他渴慕已久的,比如全世界最豪华的。
然而,日本这家粉笔厂的故事却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幸福。
这种幸福不是来自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是来自 “给予”产生的快乐。
那些努力工作的员工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他们感到被社会需要,被他人赞美,他们的产品能为人所用。一句话,
他们感到幸福,是因为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幸福。
同样地,那位为他们提供岗位的总经理也一定感到幸福,因为他给了员工机会,他的“给予”是员工们感到被赞美和被需要的必要条件。
欲望得以满足带来的幸福是加法,因为那只能使一个人感到幸福。而“给予”创造的幸福是乘法,因为它使更多人感到幸福。
从这点上看,“给予”创造了一种更加崇高和更加深刻的幸福。
为什么“给予”能创造更崇高的幸福呢?
从哲学上讲,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靠本能和自然赋予的本性生存,因此, 动物从来没有为超越自己本性的意义活着。
而人不同,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令人类有目的地行动,而且去做有意义的事。仅仅为了满足个体生存最基本需求的行为,是一种类似动物生存本能的利己行为。 所以,它带来的幸福感是低层次的。
对人来说,应该超越“利己”的层次
,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依赖社会生存,也应该对社会做出贡献。缺少后者,人类将走向灭亡。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获得了多少,而是更多地要看他“给予”了社会什么。
“给予”赋予了“做事”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它既能为他人创造幸福,也能令给予者因为分享他人的快乐而感到幸福。
从“给予”的角度看待企业,人们会对企业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将企业的目的仅仅局限在“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显然是一种以满足“获取”利润欲望出发的“利己”观念。
柯林斯和波拉斯在《基业长青》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已告诉我们:超越利润才是公司“基业长青”的根本。翻开那些令人尊敬的企业历史,哪一家不是在“给予”?
它们给予顾客物超所值的产品,给予员工安定的工作条件和精神激励,给予社会大力的支持和赞助。 正是它们的“给予”,促进了社会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反过来又推动企业成长。
一旦我们将企业的目标锁定在“给予”这样崇高的层面,管理就该是为创造幸福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活动。
不仅管理活动会对他人造成影响,管理者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引起对方的反应。这种反应反过来会影响企业家和管理者自己。
印度古谚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给予他人鼓励和赞美,一定会收到同样的回馈,从而使自己也感到快乐。
反之,一位每天苛责员工的管理者,你能指望他幸福吗? 假如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都感觉不幸福,你能期望这样的企业受到人们尊重,并推动社会进步吗?
道理说完了。当你工作时,千万别忘了这个原则:“
管理的本质是创造幸福。
”
作者简介:
吕源
,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