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 14 寸的电视机像是一个小小避难所,屏蔽掉许多现实中的不快和孤单。」电影伴随着一代人成长,一代人也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在肉眼所见的电影画面背后,是镜头的时空运动,是思维才能接触到的语言。以下这篇文章回忆了卫西谛童年时和电影一同成长的经历,剖析了他生活态度转变的整个历程。

我走进阴暗的圣庙,
去完成简朴的仪式。
那里,我等待一位丽人,
红色的灯火在闪耀。
我无意中读到俄国诗人亚历山大 · 勃洛克的这几句诗,想起曾经走进电影院里等待光影投射出来时的心境。
哪怕那一刻只是记忆的虚构,但也足以让我激动。
最早的记忆
也许是因为都知道我从事电影写作,有很多人会和我聊起自己的电影经验来。回想起来,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位。一位比我年长约十岁,说起自己下乡的时候怎么看露天电影的,因为放电影的地方远,等到放工后奔过去,每次都只能看到最后十分钟。但也不管许多,每次都这么奔过去,于是看了几年这样的「最后十分钟电影」,乐此不疲。还有一位比我大三四岁,说自己童年在乡下时,如何向往流动放映员的生活。三个人,两辆小推车。一辆上放机器和胶片,另一辆放被褥和生活器具,一个乡、一个乡的放下去,恨不得就跟了去。有时候,我很羡慕有这种回忆的观众,我也生长在乡下,可是同样的电影记忆却几乎是零。

我 1970 年代初期生在上海的郊县崇明,十岁时离开这个位于长江口的岛,随着家人到南京定居。去年陪着父母返乡,开车经过县城附近一座老旧的建筑,上面有一块「鳌山电影院」的招牌,忽然惊觉: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去过的电影院!
依稀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可能是姑父一家带着我进去,看的电影是香港的《画皮》,当时风靡一时并且被渲染的过于恐怖,以致于我全程都捂着眼睛。想想很有意思,我生命中第一次看的电影,居然是一部「未看见」的电影。前两年新版《画皮》上映,我查资料才正式知道这是鲍方在 1965 年拍的,确实在 1979 年引进过内地。看来记忆也不是完全靠不住。
来到南京之后,曾暂居在市中心的新街口,因为转学问题,无所事事的一段时间,但是年纪小,哪里也不能去。对于我来说,城市里到处都是新鲜事物,所以当比我早几年来这里的哥哥带我去看电影时,反而没什么惊喜。现在只记得那是一部隐约关于攀登雪山的美国片,别的一律忘了。
那座影院倒是一直记得,因为非常著名,叫做「大华电影院」,现在去看还跟当年一样。这座影院 1936 年建成,建筑学家杨廷宝设计,据说开业时有梅兰芳这些名流捧场,走进格局不凡的大厅里去,就能想见当年的盛景。只是随着近 20 年国营电影院的持续衰败,「大华」也逐渐无人问津,最后底楼不得不租给卖皮具和卖服装的,我有时偶尔会经过,但连向里张望的勇气都没有。大概因为属于文物保护建筑,才勉强保住在地价昂贵的市中心未被铲除。
在我中学之前,大华电影院还是热闹非凡的,引进外国片目丰富、国产电影也繁荣。我常独自留恋于此,未必真的进去看,但总买一份四页纸的「电影介绍」。这种影院自己出的印刷品,报纸的纸张、黑白色、油墨味浓,现在想起来当时对剧情文字和剧照图片的热爱,似乎超过了影院真正放映的电影。
那个时候人生一片空白,没有欢乐、没有忧伤,也没有对远方的渴望,所以对「活动影像」的喜欢,却只停留在纸面上。
直到整个八十年代结束,我都还没有体会到约翰·伯格所说的电影魅力:
它是一种旅程;它将我们带往别处。
14 寸避难所
1989 年的夏天我正好从初中升到高中。在之前的两三年里,我总是在每个礼拜三,趁老师们政治学习的空儿,一个人跑到学校隔壁的大桥电影院去(就在长江大桥旁边),总是看武打片;在之后的三四年里,没有人去电影院里,那里既不放引进片、也没有好看的国产片,就只能到满是烟味的录像厅里,还是看武打片。
每次散场后出门回家路上,总觉得身轻如燕,心胸都好像开阔很多。
这可能是我最初从电影里接收到的一种幻觉。
在文化空白的那几年里,唯一的银幕印象,可能是学校组织我们集体观看《妈妈再爱我一次》,一部台湾的小成本悲情伦理片。我记得女生们开始哭的时候,男生们就散场出去了;但是很多男生还买票再看几遍,永远就看开头的几分钟——因为有各种姿势荟萃的床戏嘛。谁也想不到如此「纯洁」的亲情教育,到最后倒是我们那代人的性启蒙。当时我可不知道,在北京一个叫张元的年轻人自己筹钱拍成了《妈妈》,成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
不久以后录像厅也不去了,追求时髦的城市家庭开始购买录像机;接着每个街区、每个菜市场都会开上两三家录像带租赁铺子,录像带大多是店主翻制。那时候的风潮就是传看吴宇森拍的《英雄本色》,以及之后一票来自香港的枪战片。我记得看着、看着、就看到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当时就愣了一下,好像忽然看见电影还有别的样式,不全是打打杀杀,还有莫名的力量击中人的情绪,从此就对电影多留一个心眼。
我租的最后一盘录像带叫《铁窗岁月》,那时候刚刚工作,有一个稍长的同事告诉我,最近有一个好片,讲一个哥们花了 19 年功夫用一小钢勺挖了个地洞,从牢里跑了。一听就让人激动,下班就赶着菜市场租片店借,觉得真好看。后来,这个片子最流行的时候叫《刺激 1995》,正式的名是《肖申克的救赎》。

录像带被 VCD 影碟全面取代的时候,我刚算得上经济独立,还在 VCD 机还挺昂贵的时候我花一个月工资去买回来,接上床头放着的一台被宾馆淘汰下来的 14 寸电视。从那时起,我的影迷时代才算真正的来到。
除了上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去淘碟、看片,还跑到图书批发市场买港台的电影过刊读。慢慢地就发现电影世界里不光有好莱坞,还有基斯洛夫斯基、还有侯孝贤、还有岩井俊二。
总之,那个 14 寸的电视机像是一个小小避难所,屏蔽掉许多现实中的不快和孤单。
和我这样一路看过来的,是好朋友小张。我们都有点藏碟癖,好东西都想买一份留着。小张手上拮据,那时看到拿着三五十张碟卖的路边小贩,觉得以碟养碟也不错。他借了几百块钱,拿了一个鞋盒,在外秦淮河上的草场门桥上试卖,如果我有空就替他望风。国庆节生意好,结果一辆警车开上桥直直地停在他面前。那天我有事不在,没替他看着点。小张下意识拔腿就往桥下的小路里窜,跑了不多久终于两头堵住,被捋翻在地暴打了一顿。
据小张回忆,自己被拎到警车后排,前后都是铁栅栏,当时桥头围观群众无数,他手握铁栅栏,望着车窗外。——他说,这是多么熟悉的电影场景啊。那件事,好像已经成为我 VCD 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了。大概是终于发觉:
现实的归现实,电影的归电影。
看清这一点,再面对活动影像的时候,就会多一份判断和认知,从此与虚伪或虚假的东西疏远了。
后窗
1997 年学会拨号上网,世界忽然就不一样了。有着同样喜好的人,原先都散落在黑暗的四面八方,忽然星星点点的都能看见了。通过 BBS,以往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同一现实空间里的人逐渐汇聚,构成了「趣味的共同体」。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土木工程的设计人员,坐在拥挤的办公室里,面前堆着厚厚的图纸、计算书、标准图集,用复杂的程式给建筑物配上混凝土标号和钢筋根数。
网络的出现,就像荒漠里行走看不见尽头的人,突然发现了绿洲。
每天一回到家,就爬上线去,发贴、留言、回复,把以往只能埋头写到日记里的话,发在网络上和人交流。对于内向如我的年轻人来说,个人与个人的隔离状态被打破了,而电影成为了彼此亲近的通行语言。在有网络的最初几年,我看着别人提到的电影,别人看着我提到的电影,生活就是这样无意识地被改变了。
最初上网,没有太多选择,南京本地的人都上「西祠胡同」,刚开始的时候,电影和音乐、娱乐、时尚混在一个版内。到 1998 年入冬的一个晚上,也许是挺长时间不满足于没有单独的电影版,我决心自己来创建一个。名字是想一定要嵌套经典电影的片名,忽然就想到「后窗看电影」。还写了一句很文艺的宣传语:
电影是生活的一扇后窗。
其实嘛,当时连希区柯克的《后窗》都还没有看过呢。虽说抒情得有点夸张,但对我个人的生命而言,此言倒是非虚。电影真是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的人生透了一口气。在我每天骑车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看不见未来的时候,它让我看见了一点梦想的光芒。

2000 年的初夏,有一天「后窗看电影」的副版主秘密客来找我,说要开展观影活动。在 DVD 还没出现的时代,大师电影和独立电影都还是稀缺货色,很多片源普通影迷没办法接触到。这时全国都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民间观影」的活动,大量放映这些影片,形成了一次浪潮。
在南京之前影响最大的是北京的「实践社」、上海的「101」、广州和深圳的「缘影会」,同期的还有「武汉观影」等等。因为当时我们总觉得「后窗看电影」有几分号召力,于是有了「后窗观影」活动。从此,交流更进了一步变成了分享。
当一群人来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这个活动起初是租用东南大学的图书馆放映室,后来也曾在一家影院和一家音响器材城里进行。从一周 1 场到一周 3 场。刚开始的时候,电影开放都是在晚上六点左右,秘密客和其他几个负责放映的年轻人,在此后就会去东南大学旁边的小餐厅去点肥肠酸菜鱼吃起来,但是因为放的是 VCD,所以四十五分钟后还得跑回场地换碟,回来继续吃。遇上放《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样的片子要跑三趟。来的观众每场大概 50 人左右,遇上放伯格曼也可能只有两三个人看,来的人多是学生以及本地文化从业者。
在那差不多两年间的时间里,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观影活动的入口处,看那些影迷走进去,脸上闪烁着对电影的渴望。
从当时开始,就渐渐理解,电影是「黑暗中的仪式」这回事。
一群人在熄灯之后,看着眼前的银幕亮起来,等待他们期待的人物和故事浮现。尽管观影活动的放映条件非常简陋,但毕竟聚集了影迷,培养了一些作为集体行为的观影习惯。
后来有次我听纪录片导演黄文海讲他去日本参加某影展的事。说一天由翻译陪同参加一个重要活动,大概是某位日本电影大师的回顾展。坐定熄灯后,银幕上一片黑暗,就听有一男一女在说话,说了半天电影也不开场。日语也听不懂,就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说:今天放的是成濑的电影,胶片已经遗失了,所以那两个演员在念剧本。可能也只有身处黑暗之中,才有对电影的尊重。
视力工作者
大约是一年多以后,各地的放映活动纷纷被勒令禁止或自行关张,总之逐渐凋落。可是 DVD 的出现,使得影迷们随便就可以买到之前一直梦寐以求的经典和禁片。
在我的印象当中,在 2001 年,实践社、《南方周末》共同主办的首届独立映像节,反而成了「民间放映」退潮的预告。在那年的 9 月末,我被通知作为南京的代表,匆忙买了一张加班车,颠簸了大约 22 个小时,到北京去做评委。从早到晚 12 个小时,看各种纪录片、剧情片、实验片。此时大家都刚刚开始玩 DV,参赛片目质量落差极大,观众刚被大师电影洗礼过,对那些做作幼稚的片子使劲哄笑谩骂。导致第二、三天,影展主席羊子不得不跑到台上呼吁,请观众尊重导演,尤其请坐在前排的评委不要扔矿泉水瓶。
因为有关部门的意见,这个活动的闭幕式最后不得不挪在郊外的一个汽车电影院举行,一群人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一面志趣盎然。闭幕片是贾樟柯的《站台》,说山西方言、没有字幕,贾导演只好亲身做同声传译,说「他妈的」这种粗口的时候,那正儿八经的腔调,大家一听就哄笑。
来年的 2 月 1 号,广电总局宣布,对非国有资本的电影单片许可证发放制度将正式实行,也就是说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电影制作,而那些独立电影制作者不再需要购买国营制片厂的「厂标」了。
这一年的 12 月,张艺谋的《英雄》上映,票房过亿,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了热闹而畸形的「大片时代」。

与商业和审查控制下的公映体系相平行,一个自由的独立电影世界也相应形成。2003 年起,南京开始出现了一个名为「中国独立影像展」的活动,放映年度最重要的独立电影。每届的海报都做出很革命的态度,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温和的影展。每年秋天,有许多独立导演以及一些海外选片人会来到南京,放映的地点每年在不同的高校里举行。
我是从第四届开始成为独立影展的选片人,成为张献民先生所谓的「视力工作者」。每年有这么几天,被关起来从早到晚看来自全国的独立电影,包括一些学生作业。张先生把现阶段中国社会有五个阶层的分法,拍独立电影和看独立电影的人被分在「中间一类人」:
这些人既不试图成为官僚和资本家,也尽量避免去做为官僚和资本家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每年的独立影展差不多就是这「中间一类人」的派对活动。期间每天有一堆独立电影放映,放映完了是导演上场交流,集体交流完了还可以到隔壁咖啡馆和这些拍电影的人单独交流,可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你可以很直接感受到这些电影作者的思考和欲望。
2009 年的 9 月我在平遥住了一个礼拜,参加一个中国独立影像文献及作品的巡展,名字叫「这里发生了什么?」。文献展的展厅在古城的柴油机厂的某个车间,放映场所是车间最深处搭一个简易的黑棚,起初两天阴雨连绵,车间渗漏,塑料顶篷兜着很多水,时刻有倒塌之险,不得不人工用木棒去顶。结果观众都坐在浅浅的水坑里,而观众除了工作人员和我之外,都是来参加活动的导演们,颇像内部放映,放映后必有讨论。我们感慨这个展「复原」了独立电影最初期的放映条件和观影模式。即便如此,我和很多纪录片、剧情片的作者们仍然觉得这种集体生活很有意思,大家每天一起吃住、观影、讨论、在古城街道上游荡,享受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似乎也是小影展最好的赐予。
在平遥的展览是那届国际摄影展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位置偏远,即使有参观者前来,也只是钻进篷子里看上两眼就走开了;但是依然有两三观众自打看上两眼之后每天都来,有普通的摄影爱好者,也有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们说,他们没见过这种电影,电影里出现的人、发生的事如此真实,就在当下,为什么他们却感到如此陌生。有两个女生看完一部纪录片后,几乎哭着问导演,为什么这样真实的生活在电视里、电影院里她们看不见。我们在场的人试图说明,这些现实为什么不能看见,好像也没能让这两个女孩都明白。但是组织者和作者们仍然很高兴,因为
这些看不见的影像、看不见的现实,终于有人看见了。
至此,电影和现实又交汇了。我已经不再是「14 寸避难所」里的那个年轻人,而是必须有勇气面对广阔世界的「真正的观众」。
这就是我经历过的电影体验。
坦白说,
我知道电影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仍然愿意信任它、期待它,让它继续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始透过自身经验去理解电影;开始承认生活才是电影的主角。而理解电影,又成为我去理解世界、理解人的新途径。
我从电影那里看见现实冰山的耀眼一角,灵魂森林的幽暗深处。
《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上市啦
作者卫西谛是 49 届金马奖特邀评委,也是微博话题王者杜蕾斯的座上宾。他与贾樟柯、水木丁谈笑风生。他阅片无数,看尽人生百态,自然无码高清。愿你从中看到你想看到的人生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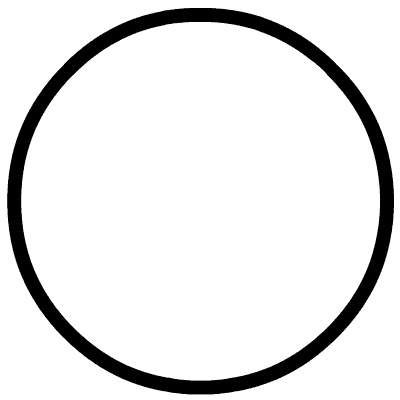 戳原文,立即购买!
戳原文,立即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