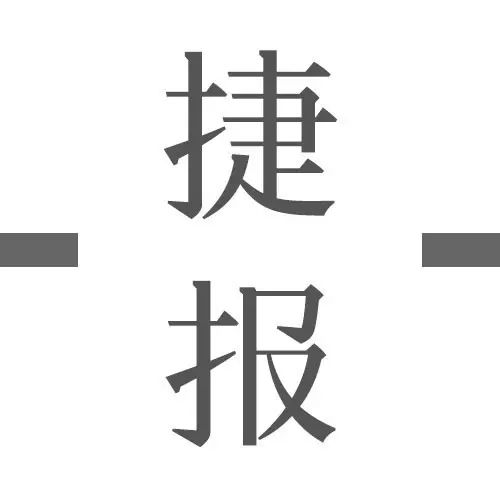为搞清欧洲政党是如何吸纳穆斯林候选人和选民的,笔者分析了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英国近300个城市中的数千场竞选活动。笔者的研究表明,各政党采取的不同策略与穆斯林选民群体的大小和影响力相关。
许多中左翼政党考虑到他们选民的世俗化、在社会议题上自由化的偏好,希望招募符合这一偏好的穆斯林候选人。他们希望能一石二鸟:通过展示包容性来吸引他们的全球主义票仓,同时向也穆斯林选民群体表达对他们选票的兴趣。我把这种策略称为“象征性融入”。为达成这种象征性融入,政党通常会选择时速的、进步的、支持女权的穆斯林。而这些候选人经常时女性,因为仅凭参选本身,穆斯林女性就可以表达这样的信号:她已经同化了,不再受父权的规制,如果她还不戴头巾的化,这一信号就更加强烈。而一个穆斯林男性就无法轻易表明他是进步的,而此前的研究表明,选民在考察候选人时,这些简单化的形象的确是有用的。
这种象征性融入的策略往往出现在穆斯林选票对赢得选举并非关键的情况下。它的受众其实是那些不愿投给清一色由男性、白人、基督徒组成的政党的非穆斯林选民;能吸引穆斯林是加分的,但这只是次要目的。象征性融入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女性经常在显眼的位置上出现,即使她们所在的国家和政党中穆斯林政治人物的总数并不多。
象征性融入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和德国的地方政党提名的穆斯林女性候选人比例明显高于比利时和英国的政党。在所有这几个国家中,穆斯林融入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话题,而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大体相似。但奥地利和德国更严格的公民身份制度使得穆斯林中拥有国籍的比例更低,因此他们在选民中的比例也就更低。大多数政党政党的动机都是赢得选举,而非坚守意识形态上的包容许诺,因此,奥地利和德国的的政党便更少有穆斯林候选人。他们通常并不需要穆斯林选票,而是通过挑几个穆斯林候选人来向他们的进步派选民传达象征性的信号。
相反,在比利时和英国,当选的穆斯林候选人所占的比例比在奥地利和德国高几倍,但其中穆斯林女性候选人的比例却更低。事实上,在笔者研究的奥地利和德国城市中,穆斯林地方政治人物中女性占了几乎一半,而在英国城市中,这个数字却只有14%。
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奥地利和德国的穆斯林并不比英国的穆斯林更世俗化、更进步。原因其实是,在英国和比利时的许多城市里,政党选择了被我称为“基于选票的融入”的策略。当政党有动机去积极吸引穆斯林选票时,便会采取这种策略。
英国和比利时拥有更为宽松的身份法律,也因此拥有更多穆斯林选民。而英国的选区划分方式还对地域上聚居的群体更有利:集中居住的族群——经常是宗教少数群体,比如欧洲的虔诚穆斯林或是美国的正统派犹太人——可以对选举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宗教少数群体中经常有密集的社会网络,在选举当天能有效动员成员去投票。左翼政党自然也不会放过利用这些群体的机会。在伦敦、布鲁塞尔和鹿特丹,在选战中获胜时常要依靠社团领袖和伊玛目的催票。
然而“基于选票的融入”策略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被穆斯林社群投票这块蛋糕所吸引,而对穆斯林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宗教教育或女性地位问题上的争议立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对欧洲穆斯林的政治动员,而是在自由、世俗的民主国家中对待宗教少数群体的一个普遍问题。)
的确,依靠人种-宗教连结来动员选民会让社会议题上的保守传统派得势(无论是候选人还是选民群体),而这些人在社会议题上的姿态是与左翼政党的官方立场以及他们世俗、自由化的选民的看法有冲突的。例如,针对穆斯林社群内存在的家庭暴力、强迫婚姻现象,过去曾有地方上的穆斯林政治人物不肯与执法部门合作。英国伯明翰的穆斯林女性最近就向工党(Labour Party)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提交了一项正式投诉,称穆斯林男性政治人物在当地工党的许可下,对渴望参政的穆斯林女性常年实施“系统性歧视”(“systematic misogyny”)和抹黑行动。
事实上,“基于选票的融入”策略所产生的穆斯林候选人几乎总是男性,当政党领导人选择这种融入策略时,也就在事实上——而且是有意地——减少了当选女性的数量。这些左翼政党(也包括一些右翼政党)只有在不影响选举基本目标的前提下才会去推动党内的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