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迷获知并熟悉罗杰·伊伯特,是个与正常途径相反的过程。
我们最早在各种盗版DVD的封套上看到了他的影片推荐语和类似「Two Thumbs Up」(两个大拇指朝上)之类的担保时,只有少数人凭借英语和网络之便,略微窥读过他的影评作品。又过了些年,关于他个人的介绍和评论文章才在中文世界里得到传播。

罗杰·伊伯特
也就是说,在真正了解伊伯特之前,我们已被预先告知了他的权威地位。因而,在阅读最近出版的两部伊伯特影评集译作(《在黑暗中醒来》和《伟大的电影》)时,中国读者难免会带着某种混杂着好奇和怀疑的心情来审视这位盛名之下的「美国第一影评人」。
其中《伟大的电影》像是对电影史的某种总结陈词,《从黑暗中醒来》则是伊伯特个人生涯的摘要式呈现,全书分为几个大的板块,包括伊伯特早年作为记者撰写的人物特写、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影评文章(并非像《伟大的电影》是事后的回顾和盖棺,这里辑录的影片多是在影片上映时写成,更能反映影评人的前瞻眼光,并作为价值颇高的历史记录),及若干主题各异的电影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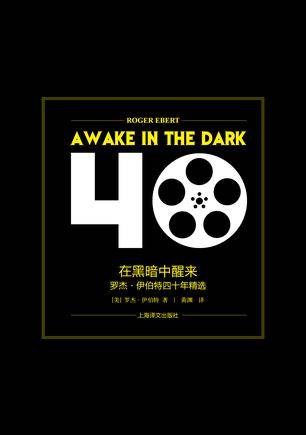
《从黑暗中醒来》
罗杰·伊伯特是独一无二的,和同辈人相比,或许他不如乔纳森·罗森鲍姆对世界电影所知广博,不如戴夫·柯尔的影史功底娴熟,也不如J.霍伯曼对各种文化潮流与政治气候的精辟见解。
然而伊伯特自有其安身立命之独门秘笈——他绝对是当代影评人中最高明的高空钢丝杂技表演者。有的影评人装作对评价的对象不甚了解的样子,屈就很少看电影的读者;有的影评人写的东西又只有他的同行才能理解,伊伯特认为这两种人都是不诚实的,前者是木偶,后者是在「浪费邮票钱」。
那么他自己呢?用他1991年在《给我自己和其他某些影评人的备忘录》中的话来说:「每天为日报写影评,那是一种在底线和更高的目标间寻求平衡的行为,是一种在下列两个问题的答案间寻求平衡的行为:1.这电影值得我掏钱看吗?2.这电影会增加或是否定我关于人性的认识吗?」
千万不要小看了伊伯特笔下这种超强平衡能力的意义,影评人职业之危如累卵,在于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在拿职业声誉作赌注,任何一篇评论都可能让他在不经意间失去大量读者乃至饭碗,而他一生中要写好几千篇。

伊伯特获普利策奖
在成为影评人的第八个年头,伊伯特就得到了普利策奖,那一天距今又过去了三十七年了,他仍未中断写作,仍然广受欢迎。那么支撑他的动力只能是爱,对电影的爱,和对写作的爱;以及对各种类型、各个国家、不论高雅或通俗影片的好奇之心与广博趣味,保证了他的爱永不枯竭。
或许这是因为他来自于一个电影曾经举足轻重的年代。在他之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詹姆斯·艾吉和曼尼·法伯,是他们将影评提升为新闻事业中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分支,电影评论开始具有优美的语言和自觉意识,并且懂得欣赏B级片和先锋电影的价值。
而在伊伯特刚刚踏足新闻界的那几年(六十年代中期),电影以及影评空前并且绝后地成为全美国知识分子的兴趣焦点,德怀特·麦克唐纳、斯坦利·考夫曼、宝琳·凯尔、安德鲁·萨里斯等人借助《时尚先生》《新共和》《纽约客》《村声》成为美国电影文化的中心。伊伯特这一代影评人,有机会从以上这些名字那里借鉴文风、模仿口味、汲取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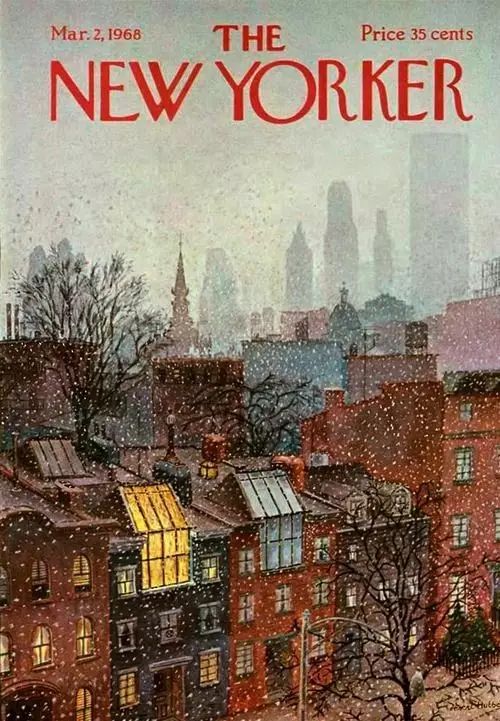
60年代的《纽约客》
这一代影评人出生于「婴儿潮」的前后,普遍结合了知识分子趣味和迷影情怀,伊伯特作为其中之代表,并没有艾吉、麦克唐纳等老派报人那般下笔优雅,也没有「教母」凯尔的辛辣与「教父」萨里斯的渊博,何况凯尔和萨里斯还各自拥有自己的体系和信徒,前者是无师自通,自成一脉,后者借鉴了法国人的体系并将之美国化。

「教母」凯尔
那伊伯特有的是什么呢?正如大卫·波德维尔在《在黑暗中醒来》前言中所说:「他将惊人的能量、敏锐的判断、广博的知识、探索的眼光和敏捷的幽默感融入了他关于电影的评论文章中,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洞察力的影评文字。」
伊伯特对电影媒介本身的跨度和力度拥有高超的洞察力,并能将之转换成可以感染读者的热情。总体上,伊伯特是温和的,但在谈论烂片时,他也会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刻薄。
他的娓娓道来、庖丁解牛让大多数读者有一种和熟悉的人对话然后恍然大悟的感觉。伊伯特又善于最大化地利用各种现代化媒介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观众抵御好莱坞日益单一的品味倾销。
他曾对同龄的「新好莱坞」导演总是不吝慷慨的赞词,罗伯特·奥特曼、马丁·斯科塞斯的成长与屹立,离不开他笔下的保驾护航。所以在书写「新好莱坞」的历史时,我们完全可以说伊伯特的评论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章。
伊伯特1942年出生于伊利诺依州一个小职员家庭,据他回忆,马克斯兄弟的喜剧片《马戏团的一天》是他看过的第一部电影。青年时他是学校的游泳健将,高中时得过美联社的体育报道奖。

《马戏团的一天》(1939)
伊伯特原以为自己将来会是英文教授或政论作家,成为影评人纯属意外。1966年,他被介绍加入《芝加哥太阳时报》,第二年中断芝大博士学业和正在写作中的关于爱德蒙·威尔逊、保罗·古德曼和德怀特·麦克唐纳这三位不同领域著名批评家的论文,成为报社的全职影评人。
这一年正好是「新好莱坞」出世的一年,当时在美国影评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多是像《纽约时报》波斯利·克洛瑟这样的老古董,他们将拘谨的道德口味置于电影故事和风格之上,完全无法领会《放大》《毕业生》《逍遥骑士》这批电影的优点,报纸需要伊伯特这样的青年影评人,能顺应反叛与抗议的时代精神,并宽容性爱与暴力元素的表达。
历史证明,伊伯特对《邦妮与克莱德》《2001漫游太空》等在当时掀起巨大争议的影片的评价是富有远见和经得起考验的。

《邦妮和克莱德》(1967)
如果仅仅拥有以上特质,伊伯特当然还是优秀的影评人伊伯特,但他不可能成为今天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伊伯特。而这能成为现实,首先要拜「电视影评」所赐。
更甚一步,也要归功于他对互联网的娴熟利用,他是最早将自己写过的几乎全部影评搬到互联网上供读者检索的影评人,他还维护着一个更新频繁、点评热烈的泛文化博客,使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每一代的影迷中。
其实影评人上电视不算七十年代的新生事物,早在1948年ABC电视网就有过一档影评栏目,后来CBS也开过。朱迪思·克莱斯特靠上电视也让她一度成为地方级明星,那时伊伯特还未入行。
但将电视影评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还要自伊伯特和他的同城搭档吉恩·西斯科1975年登上PBS在芝加哥的地方电视台WTTW,联袂主持他们每周一次的节目开始算起。这个节目后来几易其名,播出平台也换了好几次,但两人合作的模式始终如一,直到西斯科1999年因病去世。

伊伯特和西斯科
这档影评节目的形式并不复杂,伊伯特和西斯科会在半小时内依次点评四、五部电影,给出大拇指向上或向下的评价,若遇到两人意见不一,还会像说相声似的即兴辩论一番。
电视的威力使伊伯特和西斯科成为整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对影评人。艾迪·墨菲认为他们有能力杀死一部电影,当然他们也曾有过不少次拯救无人关注的优质小片的壮举。
伊伯特和西斯科,从身形来看一个矮胖,一个瘦高,两人的抬杠从荧屏上延续到荧屏下,他们会暗地竞争排名顺序和幕后猛料,录影时经常会因为争执不下导致一天也录不完。年轻时的伊伯特十分好胜,他希望证明自己是比西斯科更好的作家、更好的谈话者、更风趣的人……
有些观众对电影和影评都不感兴趣,他们是冲着看两人吵架打开电视机的。人们把他们看作影评界的劳伦与哈台,或是鲍勃·霍普与宾·克洛斯贝。根据统计,两人的意见吻合率其实高达70%,但观众只记得他们的争吵。
有一个经典段子,西斯科对伊伯特说,你不要穿棕色的毛衣上镜,因为别人会把你当成一团移动的烂泥。
伊伯特立刻利用西斯科稀疏的头发反唇相讥,你们知道吗?宇航员在太空唯一能看见的两件东西是什么?中国的长城,以及西斯科的额头,你实在困难可以把眉毛往上梳啊,而且西斯科的发迹线太过辽阔,已经申请了自己的邮编。

在高峰时期,伊伯特电视节目的收视人数保持在800万至1100万,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数字。他的电视影评生涯持续了三十年,直到2006年因癌症被摘去下颚,从此无法说话,才离开荧屏。
伊伯特在电视上的走红导致了同行的争议。电视节目是肤浅的,这毫无疑问。比划一下大拇指算什么影评?电视树立的影评新标准会将对电影的思考缩减成非此即彼的喜好或憎恶,电影和影评不该如此简单。
还有人认为影评人上电视胡扯几句,再加上点未上映的电影片段,这不等于是为制片厂打免费广告吗?而制片厂从营销角度看来,只要影片和明星上了电视,都会吸引到观众去看,至于这两个影评人在那说好说坏,有时未必那么重要。
伊伯特的反驳是,既然片厂没有付费,这当然不是广告,而且他们的差评的确会对影片产生负面效应,如果曝光就算免费广告,那传统的报纸影评难道不也是广告?
1990年,《时代》周刊影评人理查德·柯利斯和伊伯特在《电影评论》上爆发了一场论战,尽管从规模和时间上来看,这次笔战比起宝琳·凯尔与安德鲁·萨里斯六十年代关于「作者论」的那场旷世大战,好比科威特战争之于二战,但新一代影评人拥有的「飞毛腿」和「爱国者」却是前辈们所没有的。

理查德·柯利斯
柯利斯在《全是大拇指,电影评论还有未来吗?》的文章中,将西斯科和伊伯特比作罗马皇帝,拇指向下就是定罪,向上表示缓刑。
他认为,由《星球大战》带动的大片潮,本就使电影观众越来越懒惰和失去对电影美学的前瞻,电视影评无疑助长了这种快餐化的趋势,会令过去半个世纪由艾吉、法伯、凯尔、萨里斯、霍伯曼、柯尔们树立的优美影评范式走向灭亡。
伊伯特在紧接着的一期《电影评论》上撰文回应,这篇《全是评星:对电影评论的批评还有救吗?》认为,柯利斯提到的现象不是倒退,反而应视为进步,因为影评的影响力更大了,地位更高了,而且全国各地的报纸上依然有很多资深影评人在活跃,柯利斯的末日论根本就是危言耸听。
不论伊伯特对影评状况的判断是否准确,他的确是在亲身践行自己的观点,无论在电视上多么受人欢迎,他都首先以报纸影评人自居,四十多年笔耕不辍,患癌症后也从未中断。
在互联网写作上,伊伯特几乎也是所有影评人中最勤奋的一个。如果在烂番茄上搜索,能找到伊伯特写过的7000多篇文章,这未必是他的全集,但已经意味着他平均每两天就要写一篇。
作为电影「白银时代」的亲身经历者,伊伯特显然对电影文化在票房大片时代的没落痛心疾首,再也不会有狂热影迷在普通电影院的门口排队等待观看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和戈达尔的《周末》了。

《去年在马里昂巴》(1961)
伊伯特说:「对于许多电影爱好者乃至最狂热的爱好者而言,早期经典电影仍然是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作为一家日报的影评人,我不想一辈子只把眼光放在当代影坛。」
于是,他在《芝加哥太阳时报》开设了「伟大的电影」专栏,隔周重温一部经典电影,并结集成同名文集。他的举动说明,向影迷推介、分析影史佳作,应是影评人最重大的使命之一,也是最能让影评人一展毕生所学的最佳演武场。
伊伯特挑选的这一百部电影包括了从《四百下》到《阿普三部曲》,从《彗星美人》到《甜蜜的生活》,从《潘多拉的魔盒》到《天堂之门》,国别、类型、题材的涵盖都尽可能的广泛。伊伯特笃信,好的影评人、好的影迷,都应当是口味广泛、不拘一格的。
这或许是伊伯特的最重要启示之一:人一生用来看电影的时间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应当更多地观看能扩充人生经验、挑战自我、充实想象力的杰作,而尽量远离那些看过之后会给我们自身带来折损的愚蠢影片。
所以,影评人决不可满足于超市导购的角色,他更应担当起尽责的博物馆讲解员,引领更多的人认识电影艺术的百年精华。
伊伯特善于透过影片来透视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比如他在评论安东尼奥尼的《奇遇》时说:「为什么我们不再有《奇遇》这样的电影了?因为同样的问题已经没人再问了。‘活着是为了什么’已经被‘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

《奇遇》(1960)
但他也敢于将个人的视角置于时代之上,例如在评论《乱世佳人》时,伊伯特写道:「(影片)从感性的视角展现了美国内战,‘古老的南方’相当于阿瑟王的宫殿卡梅洛特。内战的目的仿佛并不是为了去打败南部邦联、解放黑人奴隶,而是为了给斯佳丽·奥哈拉小姐以应有的惩罚。」
对于初学影评写作的人来说,伊伯特的文章不啻于最佳的教程,它并不卖弄高深的术语和黑话,用受过普通教育的人能读懂的浅白英语写就,但又不失幽默和偶尔为之的刻薄。
如果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入手分析某部影片,伊伯特的经验似乎在告诉我们,先抓住影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或一处最具冲击力的剪接。
例如他是怎么分析《白日美人》的:「影片中从未出现露骨的性爱场面。片中有一幕场景最为著名,凡是看过的人都一次又一次地提起;但在这一幕中,我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明白。一个嫖客带来一只小小的漆盒,他打开盒盖,先让另一个妓女看盒里的东西,又让塞维丽娜看。作为观众,我们始终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只听见盒里发出轻轻的嗡嗡声。第一个妓女拒绝满足那个嫖客的神秘要求。塞维丽娜也拒绝了,但接下来镜头切换得十分暧昧,随后的一幕暗示我们可能已经发生了某些事情。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字面意义上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象征意义上的真相,那就是盒子里装的是对于那个嫖客来说极其色情的东西;这种真相才是布努埃尔所关注的。」
《白日美人》的核心精神已经被这短短的一段话抓住。

《白日美人》(1967)
伊伯特并非事事都有先见之明,例如他对电影胶片是否会为数字技术所取代的判断就与后来的事实相差甚远,但他坦然将当初预测错误的文章收入书中。这些带有明显历史局限的思考,正巧成为最鲜活的一手记录,大约伊伯特自己也没想到这点吧。
所以,我们阅读罗杰·伊伯特,并非仅仅是在阅读罗杰·伊伯特,我们同时也是在阅读一份跨越近半个世纪、直面当代电影巨大变化的文化史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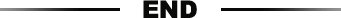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这是日本电影历史上最生猛的一段时间
这是德国电影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写影评的五个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