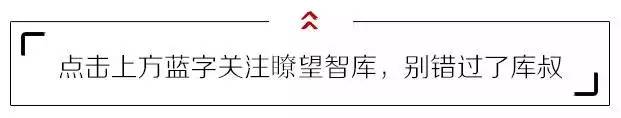

岁末年初,从同属北京旧城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传出两条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界人士振奋的消息:东城区在未来五年拟投入1662亿元,实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非文保区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优化提升“三大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南锣鼓巷等6片历史文化精华区的打造;西城区计则划投入190亿元,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一批重大文物建筑特别是纳入文物登记的会馆和名人故居实现腾退亮相。
2014年2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北京时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伴随着“金名片”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政府部门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重大项目资金不足、社会资本积极性不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等现实问题。在业内人士看来,打造好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不应用简单的经济学眼光去看问题,应该算大账、算远账,算好文化账和政治账。
文︱新华社
记者李斌、罗晓光、孔祥鑫、张漫子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算大账、远账”
新年伊始,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步行街上具有220年历史的三庆园戏院高朋满座,政府人士、学术界代表,与谢辰生、傅熹年等文物保护专家在北京西城委2016年会上共话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
在这次年会上,西城区区委书记卢映川向社会宣布:
“西城区计划投入190亿元,用5年左右时间,使一批重大文物建筑特别是纳入文物登记的会馆和名人故居实现腾退亮相。”
作为古都北京的发祥地及核心地带,西城区文化遗产丰富,拥有18片历史文化街区,三级文物保护单位181个、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2项、名人故居院落96处。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西城区将对安徽会馆、浏阳会馆、谭鑫培故居、龚自珍故居、万寿兴隆寺等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会馆、名人故居全部实现腾退保护,做到应保尽保,最大限度发挥文物的文化价值。
而在2016年岁末,东城区正式发布实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非文保区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优化提升“三大行动计划”,预计总投资1662亿元,
打造南锣鼓巷、雍和宫-国子监、张自忠路南、东四三条至八条、东四南、鲜鱼口等6片历史文化精华区;新建3000个公共停车泊位;增加1万个共享车位;还原公共绿地36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3%……
“保护古都是东城的重大责任。”东城区区委书记张家明把保护“金名片”作为东城区全区工作的重中之重,“未来5年,我们将对全区43%的用地空间进行整治式更新改造,整治胡同环境,调整商业业态,优化停车管理,最终让胡同回归宁静,让历史融入生活。”
政府部门对经济效益低、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的投入缘何如此巨大?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而言,投入上看你是算今天的账还是算明天的账?如果只算今天就赔死了。”
王凯说,“对北京这张唯一的中华文明‘金名片’的保护,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文化账、政治账,不仅要算小账,更要算大账、远账。就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早在201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项资金”,每年投入10亿元,其中1.5亿元用于支持市属重大文物保护项目,8.5亿元用于支持区县所属文物保护项目。
根据“十三五”期间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2016年,在文物及历史名城保护工作方面,北京修订文物资金管理办法,开展主题性文物修缮,加大对核心区、“一轴一线”、西山文化带、长城保护带等投入力度:投入10亿元,促进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投入6.5亿元用于历史文化名城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北京市与首都功能核心区财政管理体制。
2
“保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稳定投入”
走进位于北京西城大栅栏街道的杨梅竹斜街,既有古朴传统的北京四合院,又有现代时尚的文化创意小店;既有从明清延续至今的胡同肌理和街区风貌,又有东西方多元艺术文化元素,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交织融合在这条只有496米的街巷里。
杨梅竹斜街的独特气质源于北京市西城区启动的“大栅栏更新计划”。作为大栅栏街道的一条特色街区,杨梅竹斜街留住历史、致力创新的保护修缮探索创新出历史文化街区城市软性生长的有机更新新模式。但该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者们却有很多“难言之隐”。
“居民拆迁腾退后,这些直管公房的房屋产权无法划到公司名下,就无法实现流转,这些腾退的房屋只能是账面资产。”大栅栏琉璃厂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王志忠说,由于直管公房体制机制的障碍,当年杨梅竹斜街项目没有社会资本愿意接入,最终只能由区属国有企业广安控股接受,至今,杨梅竹斜街项目改造投入已近13亿元。”
王志忠说,缺少了国有企业的介入,安徽会馆的腾退就没有杨梅竹斜街这么顺畅。作为北京最大的会馆,安徽会馆素有“京城第一会馆”的美誉,系清朝同治年间,李鸿章兄弟为扩充军事势力而建,占地9000多平方米。安徽会馆重新修缮的总投资需要100多亿元,目前尚有缺口25亿元,虽然几经努力,至今依然没有企业愿意参与。
旧城改造更新,事关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产业提升等方面,资金需求量巨大,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回报机制,社会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十分单一。
位于东四六条65号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崇礼旧宅同样面临着融资的难题。这座被誉为“东城之冠”的清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的宅邸,三门三院,环以围廊,配置以左右数座跨院,规模宏大、设计严谨完美,居北京明、清官邸之首。由于历史原因,这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院子住进了不少居民,成了一个大杂院。
“只要有10个亿,我们就能把这个‘东城之冠’恢复出本来风貌,让这颗明珠焕发光彩。”东城区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荀连忠摆摆手说,“但是钱从哪里来?我们也和社会资金谈过,没有谈成。”
王志忠表示,以大栅栏地区为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复兴工作任务艰巨、周期长、标准高,希望文保资金的投入能够固定住、持续化,也希望通过向民间资本转让产权或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要让旧城焕发生机,关键在于机制体制的创新。”
长期关注北京旧城改造与更新的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如果在短期内,如果无法彻底解决民间资本回报问题,就应该发挥政府的力量,保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的稳定和持续。
3
“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更具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在许多业内专家看来,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正是因为放在了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中理解而显得格外耀眼夺目。打造“金名片”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具有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走近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的乐春坊一号院,曾经日渐凋敝的大杂院经过重新翻建而焕然一新,错落有致的房屋让院落充满生机与活力,富有创意的房间格局让面积有限的房间内处处充满着生活气息。
“我们并不急于让这个项目尽快入市产生经济效益,未来几年,我们还要对周边的院落以此为标杆进行腾退改造。”西城区副区长徐利曾经在什刹海街道工作多年,他对于旧城保护与更新的工作充满感情,更充满激情,“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干出一个项目是一个项目!”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如果按照传统思维去考虑资金平衡,去计算投出产出,这个经济账根本无法算平。”
徐利说,打造“金名片”需要巨大的投入,对此要有明确政治态度和清晰的政策倾向。现在各方的投入还是过于零散和碎片化,甚至可以考虑明确将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在许多业内专家看来,将北京作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提出来,这在历史上没有过。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历史资源是财富,不是包袱。我们曾经视‘财富’为包袱。所以才一方面保护维修抢救,另一方面城市古都风貌的破坏也在加剧。”
著名文物专家、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说,名城保护要更新观念,保护也是发展,恢复北京旧城是更高层次的发展,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他建议把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情况纳入到北京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看来,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甚至应该上升到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底蕴。要想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特色,历史文化是最鲜明的标签。”
把历史文化遗产提升至“金名片”的高度至今依然让许多业内人士兴奋不已。从初步认识,到局部探索,再到整体布局,“金名片”的保护正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
也许,读懂“金名片”里的政治经济学,解决了认识的问题,投入问题和融资问题也就不再是个问题。
附文:
这张习总极为重视的“金名片”,这三年北京做的咋样?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 3周年到来之际,新华社记者对自称是故宫“看门人”的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先生进行了专访。
文︱新华社
记者李斌、罗晓光、孔祥鑫、张漫子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故宫博物院是“金名片”最耀眼的标签和代表
记者:单先生您好,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总书记所说的“金名片”?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级博物馆,是“金名片”的一部分吧?
单霁翔:
我认为“金名片”,应该包含两层意思,除了指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包括为传承、保护和利用好这份文化遗产所做的努力,从而使更多精彩的文化成果惠及社会公众,让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厚重影响世界。
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拥有三项世界级文化资源。第一项是9000余间房屋组成的紫禁城古建筑群。
故宫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北京城有一条清晰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楼,共7.8公里,这条中轴线上最气势磅礴,最完整的一组大型古建筑就是紫禁城古建筑群,因为紫禁城及其周边文物古迹和传统胡同四合院的存在,北京的城市中心才显示出与世界上其他首都城市中心格局不同的文化魅力。如果说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是一张金名片,那么故宫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标签和代表。
另一项是故宫的藏品。
故宫博物院不仅文物藏品丰富,而且它是以珍贵文物占93.2%的“倒金字塔”藏品结构,迥异于世界其他博物馆以资料为藏品之最、珍贵文物占很小比例的“金字塔”结构。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清宫旧藏,这也就奠定了其在历代文物上的优势。从品类来说,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可分为绘画、法书、碑帖、铜器、金银器、漆器、珐琅器、玉石器等25大类,品类完整。从历史脉络来看,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重要类别都是历史序列整齐,例如馆藏陶瓷可以举办中国陶瓷发展史,玉器收藏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末在时代上没有断档,这一点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可以媲美。
第三项资源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观众数量都在千万人次以上,近四年参观人数更是超过1500万人次,比同属世界五大博物馆的卢浮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均高出数百万人次,当之无愧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只有传承、保护和利用好故宫博物院的文化遗产资源,将更多精彩的文化成果奉献给广大社会公众,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活起来”,才能无愧为“金名片”的美誉。

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
依托两大文化工程,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是这一代故宫人的“故宫梦”

记者:故宫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整体情况如何?
单霁翔:
2012年开始,故宫博物院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发现文物建筑、藏品和观众接待等各个环节均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有的方面相当严重,需要及时加以解决。随后,故宫博物院提出开展“平安故宫”工程的建议,并于2013年4月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根据《“平安故宫”工程总体方案》,“平安故宫”工程的保护对象为:一是占地112公顷、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的木结构宫殿古建筑群的安全;二是180余万件故宫藏品的安全;三是每年约1500万中外观众的安全。通过“平安故宫”工程的实施,将有效解决故宫博物院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火灾、盗窃、震灾、藏品自然损坏、文物库房、基础设施、观众安全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目前,该工程的七个子项目均正在有序进展。
未来,故宫博物院将继续抓紧推动“平安故宫”工程的实施,以彻底解决故宫博物院存在的安全隐患,守护故宫平安。
国务院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中长期目标,在2020年,即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基本实现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稳定的健康状态,全面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故宫人的“故宫梦”。这个梦想要实现,既依托于两项重大文化工程即“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和“平安故宫”工程的顺利完工,同时需要不断提升博物馆专业化功能、发挥博物馆社会化职能,实现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

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对文化遗产宽容、对历史城区尊重,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记者:作为业内著名专家,您认为历史街区、名人故居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如何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单霁翔:
城市文脉是城市的个性和品牌,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现实基础和文化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通过和修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的提出、《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发布,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实施等,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撑。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强化了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责任,并引导公众积极参与保护。
但是,体现并延续城市文脉,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在所谓的“旧城改造”中,一些城市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不仅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使很多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史文化名街被夷为平地。第二,一些城市在尊重历史的幌子下,陆续推出了许多由传统街道改造而成的“仿古一条街”,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沦为失去真实价值和历史信息的“假古董”。第三,一些城市将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居民全部迁出,把民居全部改为旅游和娱乐场所,超负荷旅游和商业开发,破坏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文物“原真性”。第四,不合理定位改变历史文化街区环境。例如,过去一提到什刹海,人们就会想到湖水、胡同、四合院;而现在,却是酒吧、餐馆和旅游商品。第五,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注还很不够,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
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家又称为“家庭”,人们的生活中需要一个可以与自然沟通对话的庭院空间。然后,一座座传统民居院落相依形成一条条历史街巷,一条条历史街巷并联又构成一片片历史街区,从而形成既秩序井然又气象万千的历史城区风貌。传统民居院落体系,既合理安排了每户居民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日常生活中通风、采光、日照,以及舒适性、安全性、私密性等居住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日常的社交空间,创造和睦相处的居住氛围,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哲学思想,经过历史的长期演变,成为最适合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家庭特点的居住形式。
所以,对于历史文化街区,需要以院落为基本单位,实行“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以遏制采取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方式对文化的破坏,保持原有院落布局和街巷肌理。“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即根据居民生活实际需要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而定,不求一律,不求同时,不求全部。强调小规模的、连续的渐变,采用适当的规模和合适的尺度。这就需要深化和细化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做到在不断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建筑主体始终是平缓朴实的传统民居院落;居民主体始终是和睦相处的老邻居们;生活环境始终是自然和谐的传统风貌。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成败关键在于决策。作为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的决策者,各地方政府领导要本着对历史、对城市、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组织开展对所在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和调查,把握五个方面:一是探索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战略布局,明确城市功能定位;二是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三是要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同时,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四是要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社会公共形象,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动员;五是要建立健全法制体系,做好其他法律与《文物保护法》的衔接与实施。
目前,不少城市管理者不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一味的追逐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尤其是为了提高建筑高度和土地利用强度,采取大拆大建方式,使城市历史风貌遭到破坏。“危”“旧”不分的做法导致旧城内历史街巷不断消失,割断了城市文化的血脉,历史城区也就失去了时间厚度,失去了文化的底蕴与根基。城市管理者应该转变思想,认清城市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文化遗产的唯一性,自上而下的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包含对文化遗产的宽容,对历史城区的尊重,对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追求。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故宫人”一以贯之的理念

记者:近年来,北京在处理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遗产保护利用这一关系时受到一些专家质疑,您怎么看?在维护古都风貌,统筹保护、更新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方面,故宫是如何落实“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一理念的?
单霁翔:
不少世界遗产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都有着美丽的城市天际轮廓线,展现着城市的永恒魅力和文化风采。故宫占据着北京历史城区1.12平方公里中心地区,也影响着北京城市中心地区的空间形态。有人将北京历史城区的空间形态描述为“盆”的形状,皇城地区是“盆”底,由中心向四周高度逐渐增加,过了二环、三环,高层建筑开始密集起来。北京历史城区的保护,历来强调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高度。但是,缺少了城墙的北京旧城,等于缺少了控制其高度的重要参照物,原来作为城墙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市区的主要街道,不但不具有维护历史城区氛围的保护作用,反而成为一些高层建筑“争奇斗艳”的舞台。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活跃,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压力也在加剧,人们普遍担心这个“盆”底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