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悬疑小说家在广州老城区散步,总能发现有意思的事。比如卖红包的店里,一位怕蛇的老板坐在蛇年春节装饰的中央;比如街边有一扇窄门,二楼是情趣用品店,一位老先生坐在凳子上守着一楼的门口,购物的人要怎么经过他;比如海鲜市场中最隐蔽的那条小路,走进去看到几只断手断脚的鳄鱼。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史迈一边走一边侧过头望我,用欣喜的语气问,“是不是总觉得这些地方会发生点什么?”
那时史迈参与编剧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2》正在上映,她主要打磨片中的两个反派角色。与此同时,她的第二部女性悬疑小说《河流之齿》出版了,这本书在只有样章和大纲的时候,就卖出了影视版权。她的第一部悬疑推理小说《鱼猎》在2021年出版,还在准备影视改编的过程中。她正在写的第三本小说,依然是多位女性主角的悬疑小说,这些故事总是从一场死亡开始。
2022年年末,史迈在北京度过了第七个冬天,那时她在写第二本小说,却觉得自己整个人生要完蛋了,坠入了“沉船一样的打击”。当时史迈刚参与完一部她已经投入近三年的真人电视剧剧本一稿的创作,她的首部小说获得了豆瓣阅读第三届长篇拉力赛的悬疑组潜力作品奖,也卖出了影视改编权。破釜沉舟地写、心怀痛苦地写,在此前的工作和生活中,她一直绷住那根弦。
到31岁,那根弦终于断了,她像逃离一样带着行李来到了广州。
南方植物的气息感染了史迈,她在街头看到巨大的榕树树冠,植物的生命力能把城市的水泥破开,老城区的骑楼会突然冒出一棵树。这让从小受惯了“权威”“规矩”的她很惊讶,“竟然还可以这样?”

▲
春节期间,广州永庆坊附近一个菜市场的入口处,一个水产档口摆放着新鲜宰杀的鳄鱼 图/史迈
到广州的第一个月,《雄狮少年》的导演孙海鹏找到了史迈,那时《雄狮少年2》的剧本刚写完一稿,他想找人再改。打磨、开会的过程,就是两个人在荔湾老城区逛公园、咖啡馆的过程。在另一个选题策划的工作中,她和孙海鹏去佛山龙眼村调研,正碰上龙舟饭,在本地人的催促下,他们两个外地人扛起烤乳猪跟着龙舟饭的队伍跑,这让一度在痛苦中做编剧工作的她再次感到惊讶,“还可以这样的?”
自从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编剧系读硕士以来,史迈就抱着“拿到署名,人生将会改变”的念头在写。在编剧团队里,她没有五险一金、拿着微薄的工资,但始终全心投入影视项目。她一度以为只有痛苦才能写、才能活。搬到广州之后,远离了敲锣打鼓的外界杂音,她在舒适的状态下做着编剧工作,工作结束后,她继续写那本难写的悬疑小说。
直到《雄狮少年2》上映后,孙海鹏在采访中说史迈的最大特点是松弛,这让史迈后知后觉地感受到,几年的广州生活和《雄狮少年2》的编剧工作带给自己的改变。
南方的气息也渗入了她的第二本小说。史迈的悬疑小说都是发生在三四线城市中的女性的故事,第一本关于校园性骚扰和性侵,第二本写的是代孕和非法取卵。这些生活和社会新闻中的女性创伤,在南方潮湿的气候中催化成生命的苔藓。
在《河流之齿》中,故事从一场死亡带来的出走开始,丈夫找寻失踪的妻子姚蔓时,百思不得其解,妻子能有什么秘密呢?“小城市的女孩,命运大都相似,在公园的滑梯上度过童年,在粉笔飞扬的课堂里度过青春期,然后考一个不远不近的大学,找一个体贴的男友,像父母辈一样步入婚姻。”而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女孩,“一个和他一样普通的人,一个能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人,一个能陪伴他走过事业低谷而不抱怨的人。姚蔓就是这样的人,和他的期待相当吻合。”
姚蔓出走、找寻十多年前好友李远期失踪的线索。连警方也放弃了的多年悬案,始终放不下的只有另一个女人。史迈在小说中系统性地展示了互为镜像的两位女主角,像是彼此错开的命运。姚蔓作为小城普通家境的孩子,选择了最安全的女性生活路线,李远期则展示了一个贫困的女儿是怎么一步步被生吞活剥的。

▲
《河流之齿》
但史迈在小说里为角色留下了希望,人生不只是走出和留下,也有新生。而写作也让史迈抻开女性命运在她身上留下的相似折痕。
以下是史迈的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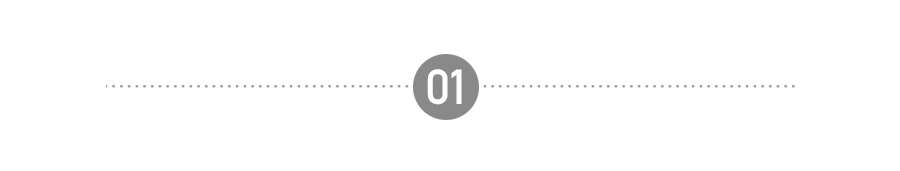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我总是觉得整个人生都要完蛋了”
刚到广州时,最冲击的我的当然是植物,哪怕柏油马路铺压着树的根,树照样给你顶起来,这里的树长得无法无天。这里还有很多“天”字开头命名的楼,但凡站高一点,你会看到贼破贼老的楼和贼高贼新的楼在一起。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城市真好啊,生龙活虎的,没人管你没人在意你,身边的人也许是小喽啰,也许藏龙卧虎。
离开北京之前那半年,我在疯狂内耗,非常焦灼。每天起来我的身体都是麻的,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我的人生完蛋了”的感觉。我开始写第二本小说的时候非常痛苦,一天写五个字,或者一天疯狂写六七千,到晚上再读一遍,然后删掉。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觉得我在浪费好不容易得来的人生。当时也有很多声音,有老师对我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前三本书,如果前两本书写得太慢或太差,就不会有人再给你机会了。
一不小心就要完蛋了,“不怎么样,你就完蛋了”,我感觉整个人生就像一个无法停止的黑洞。
那时我住在环球影城的对面,隔着我的窗户,霸天虎过山车几分钟出现一次,每天都能看到游客尖叫。但我住了很久都没有去玩一次,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想等我写出来了再去玩,害怕一旦放松下来,老天爷就会惩罚我,觉得我不努力,所以我就该写不出来,我就应该失败。我老这么自己吓自己,朋友后来觉得我都有点毛病了。
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痛苦中,最后那种痛苦让我觉得我应该先不写了,应该先想想该怎么生活。我来广州也可以说是逃跑。2022年11月我到广州时还是夏天,我最痛苦的夏天到冬天的那半年,好像一下补回来了,好像又重新从夏天开始过了。
其实我当时看《雄狮少年》时,给我最大的震撼不是画面,而是我第一次在动画电影里看到现实主义故事,因为都做动画电影了,人们往往要往大场面、往玄幻、往离奇得实拍拍不出来的画面做,但是这个电影拍“下下铺”。那个下下铺一出来,我当时就说创作者“穷过,吃过苦”。天台舞狮的画面出现时,我很想哭。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神性的是,太阳出来的那一刻,电影给了广州人的群像。你只要在广州早上起来过,你就能看到他们,那个镜头让我觉得很和善。

▲
《雄狮少年》剧照,天台舞狮
从北京搬到广州,不仅是生活环境转变,我对创作的态度也变了。我觉得外界给我的手,终于不是出拳的拳击手套了。
《雄狮少年2》出来后,有人说那么多编剧,能好到哪去?主编剧是4个,联合编剧有10个。影视行业有不成文的说法,编剧越多剧越烂,这意味着要么出问题了一直换人,要么一大堆人争执不下。我自己也是在一期导演的播客中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这个做法其实并不特别符合所谓影视圈的潜规则。他具体说了4位主编剧做了什么贡献,点名道姓地说10位联合编剧的贡献,比如你是配音演员,但修改了几句更符合人物生活环境的台词,只要对最后成片有贡献,都应该署名。
这个点,没有任何一个编剧不会羡慕,因为我们这种年轻编剧,在之前的一些编剧项目里,没有署名就没有署名,也得认,已经给你钱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按照
(《雄狮少年2》)
这种署名标准,编剧行业不会这么苦的。作为编剧,在这个电影或电视剧里,有那么一个印记,证明你跟这个项目有过联系,就已经很知足了。
在之前的编剧工作中,我对团队协作是很害怕的。我害怕那种你多写了一点、我多写了一点,大家争来争去,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比起编剧,我还是想写小说,因为小说写坏写好都是我干的,不需要跟别人扯皮。我也参与过让我怀疑整个编剧行业和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项目,以致现在别人让我回去做编剧,我都很抗拒。但跟导演合作了《雄狮2》,我觉得是治愈了我一些的,整个2024年到现在我的状态变好了,我觉得之前的伤口在愈合。

▲
史迈(左)和孙海鹏(右)在广州西关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其实我在一些看起来是人生大事的选择上都是很离谱的,以前我根本不想读研,就想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找个电视台工作,但听到说研究生毕业每个月可以比本科生多拿800块钱,当时我家庭变故,家里非常缺钱,我想要那多的800块钱。考研选中国电影资料馆是因为它在北京,当时听说学生可以免费看电影。读研期间就进了工作室写剧本,进去的时候25岁,靠“署名”撑着干活——那时候吊着我的是一个署名的作品。我很多晚上都不回宿舍,就睡在公司沙发,我都不敢让老板和同事知道,怕他们觉得我太装模作样。
最后离职的点也很离奇,我一开始都没敢意识到我的年龄,不敢想我要29岁了。这时候很多压力向我涌来,我很逃避回家,总觉得是不是得给妈妈一个交代了?当时跟妈妈许诺说每个月能多拿800 块钱也没有实现,那时候还在一直用花呗。妈妈问我在写什么,我也没有面世的作品,有些项目做了一两年,说黄就黄了。其实我更大的是沮丧,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突然这么一个念头来了,2020年年末我提了辞职。
我辞职后,有朋友说豆瓣有个比赛,让我写小说,我就开始写了。白天我还是在继续参与那个参与了几年的编剧项目,晚上赶回去写《鱼猎》的连载。这个比赛持续了100天,每周要写几千字,工作再忙我也写下来了。就那么一根弦绷着。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最后一次更新,那是比赛截止的最后一周,凌晨我在北京西站见短暂换乘的妹妹,我特意背着电脑。
那天凌晨5点,我见完她之后,还没有咖啡馆开门。我到处找桌子,在北京西站附近找到一个卖家具的广场大楼,有很多家具展示的桌子,但不让坐。我继续转转转,终于找到一个咖啡馆,我坐在那个咖啡馆写完了最后一篇。当时觉得终于结束了,嗯,接下来要面对我乱七八糟的人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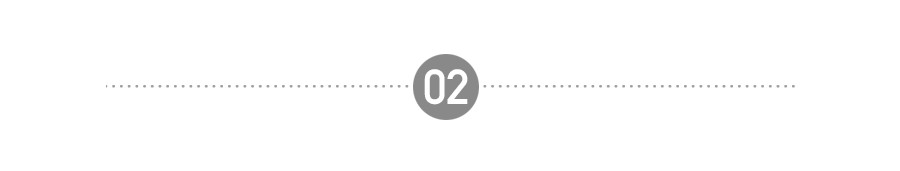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抻开女性生命的折痕
从小到大,我在山东老家坐公交车时,车厢把手上面都是无痛人流的广告。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很恐怖的广告语在盘旋,大概意思是,三分钟能干什么?三分钟吃个苹果都不够,但三分钟能让你流掉一个孩子。以至于让很多女孩,包括我,一度觉得人流是个很简单很神奇的事情,好像打个喷嚏就没了。
长大后,我在新闻上看到节育环,我去问我妈,说你安过吗?她说安过,后来取出来了。我当时非常惊讶,这个东西就在我妈妈的体内,凭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如果不是社会开始谈论,我可能至今都不知道。
后来,我有次去医院,地上有很多彩色的代孕、捐卵的小纸片。我原本是作为病人去医院接受照顾,但我拿起这些代孕卡片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身上被贴上了超市价签一样的价格条。我想,如果是一个男的看到这些卡片,他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再穷的男人也不可能贴上这样价签,但它是贴在女人身上的,子宫就是那个商品,女人的生育能力是可以被量化的。
当我要写小说时,我就想写这些压在女人身上的血印子。完成了《雄狮2》的工作后,我再写小说时,很明确我要写双女主,写的内容不能太脱离我的生命体验,我要写贫穷。把贫穷和女性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如果按照以前的经验,很容易滑入到卖身。但当下最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女生怎么在不自愿的情况下一步步成为生育的容器,但是别人又觉得她们是自愿的。
我以前上班时,和一个男生有过非常激烈的争执,他说为什么不能代孕?这样很多贫穷的女性就有赚钱的渠道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自愿”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让社会达成一种不用讨论的共谋,让人们觉得她们活该。我查很多新闻和历史资料,发现很多人真的是自愿的,原因可能是她们要换手机,甚至是男朋友要换手机,或者要给自己交学费、整容,或者仅仅是想换一个包、换一双鞋子。捐卵和代孕被包装得非常漂亮,说这就是女人自己的金矿和银行,甚至都说你不会疼,会给你打麻药。很多人就会被说服,如果是在我非常缺钱的极端情况下,我也可能会被这样的东西蛊惑。
当我要写时,我想是否找了一个过于庞大的敌人?写第一本《鱼猎》时,我知道该怎么办,主角要为朋友复仇,有非常具象的仇恨对象。可是这个故事怎么办?她救了她的朋友,她说出真相,这个世界就会好吗?直到真正动笔的那一刻,我都在犹豫要不要写代孕取卵。我想,我够资格写吗?如果真的要写,我是不是应该做更多调研?我是不是应该认识、采访更多有相关经验的人?

▲
《鱼猎》
写《鱼猎》时,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审视。可是第二本我有足够的时间停下来审视,我每写一句、每写一个人、每写一个画面,都在审视自己,都在骂自己。
我意识到自己问题在哪,同时我还不能停下来,因为有很多我想表达的东西。哪怕现在我的笔力不够,我的观点不是最正确或者最有力量的,我只能一边暴露一边写,最后感觉像用了一车布料做了一件小孩的衣服。我想象的那个东西可能更大、更厚实,可是我也觉得传达了我现在能传达的东西。我写的时候又是觉得要完蛋了,很怕大家失望,可也安慰自己,没有那么多目光,而且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讲要写。
我的人生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我在读大学前后遇到的人非常不一样。比较庆幸是,当我不再去扮演一个好学生、好女人的时候,我才开始写作,省去了理会杂音的过程。小时候我特别听话,非常崇拜权威,容易受到权威声音的影响。在我长大的地方,“尊卑”是很清晰的。我们过年要磕头、女人不上桌吃饭这些事,我小时候是不知道的,但我仔细回想,好像大家都默认了,逢年过节就是男长辈先坐下来吃,女的直接端碗就在厨房吃,还要全程递烟、倒茶、搬椅子、照顾小孩,因为我在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小孩,是一个被照顾者的角色,我沾着光,享受了上桌吃饭的权利。
在我要过渡到那个围着他们打转的角色的过程中,我刚好断裂成了两块。《鱼猎》里面有个情节,俞静翻开那个红色本子,那个本子的内容和她设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对世界的比喻。在我小时候,这个世界就是那个红色的本子,很贵很光亮,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可是你打开之后,一切都颠覆了,你就回不到那个没有翻开的世界里了。
我喜欢的韩国文学,比如金爱烂的《滔滔生活》等,还有对我产生很多影响的女性文学,我觉得她们就是写自己被压出来的血印子。那些小的东西,在我们过去的阅读中是被排斥的,是没有看到过的。我近些年开始阅读,有一些小说其实也不好,但是我就愿意看,我惊讶,原来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写出来。
我在观看我自己时,都能感觉到一些东西在我身上的折痕,29岁那年压出了一本《鱼猎》,31岁那年压出了一本《河流之齿》。我不能说就停留在这儿了,我所产生的每一笔、我所诞生的每一个想法,包括我遇到的人,都是我想写的题材。
但你说,我现在有安全感了吗?觉得人生不会再完蛋了吗?其实也没有。我还是觉得下一个完蛋时刻在等着自己。但是因为已经活过这么几次了,那么痛苦来的时候就不要害怕,痛苦会帮我。不用那么害怕绝望,人生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完蛋了也没关系,完蛋了还可以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