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力”这个词,是最近一次国际书店论坛的主题,这三个字的结合虽然新奇,却能让人一下子就明了,并不禁开始思索:书店,尤其是带有鲜明个性的独立书店能给城市带来多大的影响?这显然是难以被量化的。但不能否认,书店与城市共生共长。
日本著名独立书店COWBOOK创始人松浦先生写过:书店的意义不只是卖书,最重要的是跟周围产生关联,努力成为社区所需要的分子,让自身具有社会性。
三年前有媒体做过统计,广州有接近十五家知名的独立书店,当然还有更多的书店隐于市,顽强地生存着。走访这些书店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带我们认识了广州。

客家围屋的概念被运用到广州方所书店的设计上,前后书廊有意识地将人流聚集在了外环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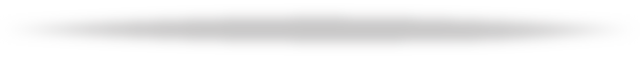
走进广州的方所,你会发现书店的中央并不是书,是美学商品、植物和咖啡区,书被分流到了两侧,从一旁走入,才是另一个世界——客家围屋的概念被运用到书店的设计上,前后书廊有意识地将人流聚集在了外环里。
方所甫一出世,便是热话。在这个将近两千平方米的空间内,书店成为了一个整合不同业态的综合体,有质感的文创产品,精致的咖啡和体现生活情调的植物与书籍一道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时,这种复合业态的书店经营模式还是非常新鲜的尝试,大家没想到,原来书店还可以这样“玩”。
方所创始人毛继鸿不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但是他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获得了灵感、历练和成就,这里创新、包容的精神给予了他无尽的滋养。他在广州所获得的,也希望回馈给广州。
他经常这样对外讲述自己最初的情结——“每个村口都有一棵老槐树,邻里之间闲了就去蹲着,有人过来交换信息。”那是他对中国传统公共空间的定义,潜移默化地成就了如今方所的定位。

方所商贸处副总监廖婉蓉最欣赏的是广州人务实和低调的特质,“一个小小的铜壶,即使不会为了卖高价钱,大家也会想着怎么做得很精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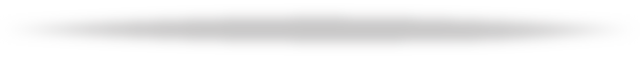
“人一直都是需要跟人交流的”,方所商贸处副总监廖婉蓉就这个说法展开,“所以你看方所的logo,就像个房子一样。”在她看来,方所是一座桥梁,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跟自己有关联和有归属感的东西。“即便你当时心情很不好,无所谓,可以在这感觉到人、书和空间的温度。”
2013年,廖婉蓉从台湾第一次来到广州的时候,觉得每个地方都“好有趣”,大声骂人的书店老板,仍然作为民居使用的历史建筑,每一处地方,都有鲜活的城市气息扑面而来。
往来不同城市,她最欣赏的是广州人务实和低调的特质,“一个小小的铜壶,即使不会为了卖高价钱,大家也会想着怎么做得很精致”。
与这种务实的工匠精神相伴,是具备实力却不张扬的城市特质。

方所每周都会邀请名人来做讲座,采取的不是零散的演讲活动,而是以方所书院的形式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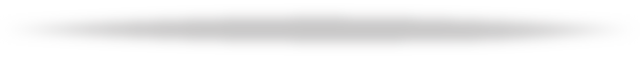
方所每周都会举办“创作者现场”活动,活动不注重新书签售,反而更鼓励各领域的文化名人专注讲自己的故事,并且提供其与读者深度交流的机会,玛丽·尼米埃、奥利维埃·罗兰、白先勇和柴静都曾经是座上客。
在方所以前,广州很少有这样重量级和高密度的文化活动在书店举办,方所开启了这股风潮,书店的层次逐渐变得丰富起来,读者的品位和鉴赏力也越来越高。
最让廖婉蓉惊喜的一点是,国内外的作家、学者来到这里后,都对广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她经常看见有读者私底下自己和国外的作家交流,“他们沟通起来很顺畅,读者看起来虽然朴素,但问的问题都好深入”。她记得有一次陈丹青参加完活动后直言“好开心”,“能让学者觉得好开心的时候真的不多。”
如今仍然喜欢和路边的阿姨闲扯的她,感慨说“这个城市有温度,很贴近你,但不代表她没有态度”。
图书销售仍然是方所着力的主业,人文、文学和艺术书籍是选品力度最大的种类,书店内30%的面积用来陈列艺术书。而且方所追求外文书籍的引进速度和国外同步,相对于网上书店快速低价的销售策略,方所明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吸引那些对于版本和装帧有讲究的读者。
这样的读者并不少,廖婉蓉从数据上给出了例证,图书收入构成了广州方所店营业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其中七成就是来自人文、文学和艺术书。
经常有人质疑这是个浮夸、烦躁、庸俗的时代,但方所的生存、在广州的扎根,本身就击退了这个说法,仍然有很多没有人放弃去思考、去感受和去追求。

1200bookshop是广州的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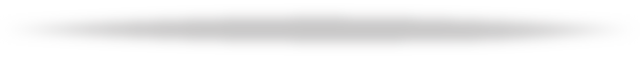
在广州,每个独立书店都有自己的属性,方所是多种文化形态的综合体,学而优书店学术氛围浓厚,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禾田书房优雅别致。对比起来,1200bookshop则更加温情。
书店的名字来源于店主刘二囍自己的经历,2013年徒步台湾,行程一共1200公里。那次环岛行彻底改变了他,当地人慷慨地收留他做沙发客的经历让他决心创立广州这座城市的24小时不打烊书店。
和营业时间一同改变的,还有他对书店的定义——“现在书店和阅读已经是两个体系了”,门外传来了一阵阵钻孔机的声音,他特意提高了音量。
“也许就是有人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躲着,可以看书,可以落脚,书店是线下的空间,不再只是传统书店的纯阅读模式。”
三年前,在书店里偶遇的从东北走到广州的驴友启发了刘二囍,他希望更多人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于是他陆续请来了自己的朋友、书店里满肚子故事的顾客,在城市的深夜开讲自己的经历,这个环节慢慢变成1200bookshop最具特色的深夜故事活动。
讲演的人都不是明星和名人,在这里,保安、独立舞者、单车环游世界的清华学生、以书店为家的流浪儿童、流浪汉等等,才是深夜的主角。

1200bookshop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是免费提供给刚到广州无处落脚的背包客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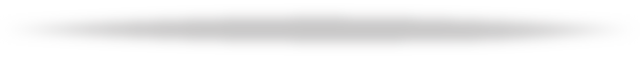
出乎刘二囍意外的是,深夜故事从一开始就很受欢迎,听众的座位一直挤满,不断有读者慕名而来,经常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忠实读者。在广州,这盏深夜不灭的灯已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日本NHK电视台曾经为书店拍摄纪录片《Lighting up the City》,在里面接受采访的客人,有专门从家里开车40公里过来的外地人,也有专门在附近买了房子只为周末来看书的客人。
刘二囍说,不同于其他容易产生距离感的文化活动,深夜故事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诶,我也行啊?”正如他一开始所构想的,书店已经开始变成一种新型的空间,陌生人之间重拾了互动、交流,每个人在其中都获得了地位对等的平等感、发自内心的尊重感,这也许是比如今大部分关系都更牢固的情感联结。
刘二囍和毛继鸿一样,都不是地道的广州人,但是他们对这座城市有信任、依赖和期待,因此在开书店这件需要托付感情的事情上,他们都是舍得付出的人。
张珊珊是天河北分店的听障员工,半年前她经过朋友介绍来到这里工作,第一天上班送错东西的经历让她一度非常紧张,但是对方的温暖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氛围,“温暖,干净,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如今1200bookshop已经开设了四家门店,暂时刘二囍还没有把书店开出广州的打算,他觉得其他地方没有自己的“根”。
书店怎样在城市生根?一个城市的文化,除了历史赋予的累积,也会在当下不断碰撞出新的文化,在1200bookshop,书店与城市已经交融出一种新的特质,让人感觉心里柔软、可以依靠,这或许就是“根”的所在。

浩天书店是广州最怀旧的书店,店主浩叔是广州本地“土著”。在这里,没有畅销书,只有泛黄了能闻到岁月味道的旧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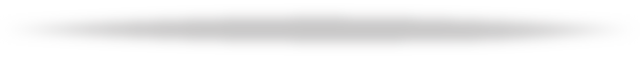
无论是方所还是1200,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开在市区的中心,线上和线下的人流让他们拥有足够的关注度,但在城市还有另一面,有不少靠店主一人之力支撑的书店,它们藏在老城区的街巷拐角,这些旧书店有小古堂,浩天书店,也有已经结业的文津阁,都是不少老广州的记忆。
找到浩天书店的路并不容易,从公交站下来还要走一段弯曲的路。循着手机地图,从街角拐进去,很快就来到了广州有名的古玩街文德路,这里的骑楼底下藏着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开始繁盛的字画店铺,相邻间还散落着如今在市区少见的士多店。
下午五点刚过,浩叔和他妻子正在吃晚饭,置之高阁的电视机固定在一个频道上,头顶上的白色吊扇呼呼作响,旧书和木板做成的书架散发着九十年代才会有的质感。
在将近40平方米的空间里,书架和旁边的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浩叔翘着腿,坐在门口的藤椅上,身上是已经洗旧了的米色汗衫。

在将近40平方米的空间里,书架和旁边的地板上都堆满了浩叔淘来的二手书。想了解广州本土文化,浩天是不二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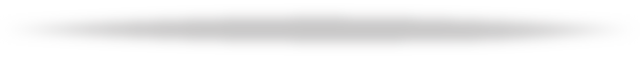
浩叔全名吴浩,文德街就是他出生的地方,70年代末卖书还是很赚钱的生意,高中毕业的吴浩开始在江夏村一带摆地摊,直至他知道广州有自己的“鬼市”,也就是天光墟,转而开始在那里淘宝,做转卖的生意。天光墟,是取“夹缝之墟,天光而息”的意思,据说在清末民初已经开始流行,贩卖的是衣服、家具、电器等各种旧货。
这些货品大多来源于回收站、厂家的清仓库存或者其他自用的二手货物中取得,繁盛时期,人民北路、光塔路、海珠桥、荔湾路和西门口一带都是天未亮就开始热闹的墟市。
三十多年的淘货生涯,浩叔早就总结出经验——天光墟是“早去抢靓货,迟去抢便货(抢便宜的货)”,因此他经常调好凌晨3点的闹钟,铃声一响,浩叔就踢踏着拖鞋、带着手电筒出发。
海珠桥是他最爱去的目的地,从头走到尾,这里翻翻那里翻翻,一般选到合适的就会下手,他有自己的“盘算”,直接交易就完事,不会和摊主多作交谈,他说这是“行规”,害怕卖家识货坐地起价。
因此书店里除了旧书,还有各种各样的旧物,老广州的画像,老式收音机,洗脸盆,建国初的徽章等等,都是他这么多年来淘回来的货物。也因此,走在他的店里,会收获和在商业区、市中心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拆迁和租金上涨的原因,浩天书店经历了数度的变迁,从江夏村兜兜转转,最后回到了浩叔的根——文德路。但如今生意已经不比当年,面对每月五千块的租金,营业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成本。
和浩叔的交流明显和其他店主的感觉很不一样,在他身上写满了典型的老广州人印记,他们精明,在商品的选择上有自己的技巧,在做生意的最初随势而动;执着,数十年来只投入做一件事情,对于自己成长的地方有着执念,在求新、求变的速度上他们缺乏、也不希望变得那么灵敏。
时光的印记就这样刻在书店的门面,许多寻访此店的读者,都很惊喜见识到自己从未遇见的广州:旧海报,机械钟,老式收音机,天光墟的故事……浩叔有感,“多数年轻人只是从父母那里听说过去的事情,所以应该有更多的途径,帮助他们了解历史,旧书店就是其中的一种途径。”

于年轻人而言,那是顽固地坚守“一天在世,一天坚持”的老一辈人和渐渐消逝的老广州,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书店让他们重新构建了对城市的认知,但毫无疑问,这些是广州最有价值的历史回忆。
每本书都拥有自己的世界,书店则是所有这些世界的入口。电子书可以给我们提供文字,却不能提供观察城市的入口。但书店可以,书店以文化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构建社会图景,构筑城市的气质,让我们体验那种只可意会的“荒地般的自由、寂寞和宽容”。
在广州的这些书店流连,既可以体会到先锋的文化概念的冲击,也可以从旧书店的坚守中读出市井味、老广州味,凌晨再黑,也总有一间书店可以收留你。
广州的书店形态远不如此,更珍贵的是,“书店给人心理上的面积,比实际上的面积大很多。”在这个维度上而言,书店力是对城市人思维、思考力的锻造,这种新的连接模式,是新型的文化空间——在阅读关系之上,重新构建了人和社会的联系。
书店和读者相互成就,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广州气质。
(摄影/郭嘉亮,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