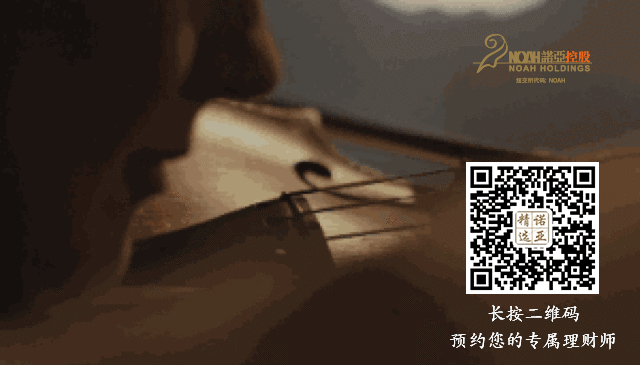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一键预约理财师
现在市场上流行一种观点:目前A股和债券都处在一个不舒服的位置,配置哪个都有风险,似乎股和债都不香。
从历史估值看的话确实如此。
A股经过过去两年的连续上涨后,尽管进入3月以来回调明显,但目前的估值水平仍然处于历史均值的上方,难言便宜。而作为债券市场最重要的估值指标,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在3.2%-3.3%的区间内徘徊许久,而过去10年间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均值为3.5%,目前的估值水平同样略高于历史均值(债券到期收益率越低,所代表的估值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然而,如果想深一层,就会觉得上述结论有些瑕疵。
对于股票这种资产而言,均值回复的力量确实很大。我们以市盈率(每股价格/每股盈利)这个最被广泛使用的估值指标为例,分子中的每股价格从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看,取决于模型中分子端的盈利和分母端贴现率水平。贴现率=无风险利率+风险溢价,由于长期看风险溢价保持不变,因此可以认为贴现率的波动主要由无风险利率主导。无风险利率下行时往往也对应经济的下行期,企业盈利同样下行(非周期股除外),而企业盈利的下行幅度往往大于利率的下行幅度(例如极端时期可以盈利下降80%,而利率水平却很难同步下降80%),因此市盈率的分子端,也就是每股价格长期来看是盈利主导,因此再除以分母每股盈利,长期看会保持一个相对恒定的比例。
而国债收益率的估值逻辑却有些不同。本质上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水平代表了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水平,经济向好,投资回报率高,国债收益率就高,反之就低。由于经济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如果长周期下经济持续走低,国债收益率的中枢水平也会出现明显下降。也就是说,观测国债收益率的均值水平更应该从中短周期的视角切入,过长的时间窗口的均值水平反而会带来误差。
从实际情况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长期国债收益率确实出现了下台阶的现象:在过去10年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第一个5年的3.7%的均值下降到第二个5年的3.3%。如果排除2013-2014年这段时间,央行打击影子银行而造成的“钱荒”环境,被动拉高了利率水平,以及2017-2018年去杠杆对于利率的干扰(利率与经济增长背离的两段),这两段时间的国债收益率均值水平则进一步下降至3.6%和3.2%。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做线性外推,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过去靠地产、基建拉动的增长模式逐步淘汰,“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速大概率将进一步下降,未来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均值或降至2.8%左右的水平。
这样看来,目前3.2%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或许已经反映了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的估值水平。
如果说前面讲的是一个长逻辑,解释了长期债券为什么香,但却无法说明短期配置债券这类资产的价值,那么接下来再来说两个短逻辑。
在讲第一个短逻辑前,先来看一张图。
可以看到,历史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铜价基本呈现同涨同跌的趋势。换句话说,如果预测对了未来铜价的趋势,就可以基本把握国债收益率的走势。那么
铜价作为国债走势指示剂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铜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金属,由于在电子、电力、交通设备、机械制造、建筑、有机化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能够很好地反应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向来有“铜博士”之称。我们以铜价上涨为例,一般可以反应两个事实:
一是实体经济开始复苏,投资回报率开始回升。
二是通胀预期开始上升。
而这两点正好也是决定长端利率上涨的因素,经济复苏和通胀回升都是债券投资应该回避的阶段。
未来铜价怎么走?
从需求看,决定因素在中国,2019年精炼铜的消费量占到全球的50%以上,而美国不到的中国的1/6。
从供给看,决定因素在以智利为代表的南美国家,其中2020年智利一国的铜矿产量占到全球的30%。
中国自从去年4月份渐渐走出疫情,恢复生产以来,铜价就迅速上升,并在今年的三月份达到高点。但从今年以来的数据看,国内经济却出现了明显放缓的现象。未来随着地产、基建投资的进一步走弱,对于铜的需求大概率是边际减少的。而美国尽管有天量的基建政策出台,但由于其本身对于精炼铜的消费量和中国相比就不在一个数量级,如果中国需求下降15%,就需要美国需求量翻倍来弥补。
另外,美国基建投资并不是在一两年内就完成,而是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平滑了未来对于铜的需求增长量。因此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铜需求的上升在边际意义上很可能并不能弥补中国对于铜需求的下滑。因此从铜的总需求看,边际上升最快的时段很可能已经过去。
从供给端看,尽管最近智利受疫情感染人数上升关闭边境,但疫苗的推广令疫情进一步失控的概率不大,供给端还是会保持相对平稳。何况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智利的铜矿产量也仅比2019年小幅下降2%。
从库存情况看,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和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三大交易所的库存量自2月以来整体上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其中更能反映国内需求的上期所库存反弹尤为迅速。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无法统计到隐性库存,也就是生产商、贸易商和消费商手中持有的库存。但根据期货公司的草根调研,隐性库存的水平也不低。因此总体上来讲,铜库存的水平已经度过了极低阶段。
因此在供给稳定、需求边际下降、库存上升的背景下,铜价上涨对于债券利率的推升压力将逐渐回落。
另一个短逻辑在于信用利差。
过去十年以来,信用利差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信用利差走阔的时期,往往对应着长端利率的下降。这一方面与经济状况相关,经济下行时,企业违约往往比较严重,信用利差出现走阔。另一方面,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讲,经济下行时,机构往往倾向于放弃风险资产(高收益信用债)进而转向配置避险资产(利率债),这样也会扩大信用利差,同时压低长端利率。
那么信用利差在未来是走阔还是收窄呢?
我们发现信用的松紧程度能够很好地解释信用利差的走势。在信用逐渐收紧时,往往伴随着信用利差的走阔,而目前的信用状况就处于逐渐收紧的阶段。因此,未来企业违约以及配置上对于安全资产的需求都会加剧信用利差的走阔,同时引导长期利率的回落。
结论已经很明确了,无论是长逻辑上经济下台阶带来的长端利率中枢水平的下降,还是眼前商品价格回落压力以及信用利差的继续走阔,都应让我们站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上,对于未来的债券市场(利率债)不再悲观。事实上,上周五公布的PPI数据超预期并没有引发债券市场的下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反而还出现了小幅回落。这种对于利空的不敏感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来自债市的暗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