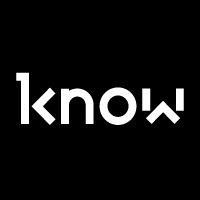KY作者 / 罗勒
编辑 / KY主创们
最近收到一条很长的留言:
“KY,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关系里出现了一点点让我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对方没有及时回复我的消息,我就会十分愤怒,开始质疑他是否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爱我、那么重视我了,甚至和他大吵大闹……我常常都会因为类似的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忍不住全盘否定我们的感情。
但不多久,比如,当对方开始及时地回复我的时候,我就会立马觉得他还是很爱我、很在乎我的,之前可能只不过是在忙手头上的工作。我还会为自己之前怀疑对方、否定彼此的感情而感到懊悔和愧疚,觉得自己不应该因为一点小事就患得患失,不应该对他发脾气。
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太作了’——喜欢的时候,就觉得Ta是完美伴侣,对他痴迷、对他百依百顺;不喜欢的时候,又对他厌恶至极、恨之入骨,只想立刻一拍两散。最近,他提了分手……说自己太累了,他只想要一段比较稳定的感情,不想这样时好时坏。可我也不想这样,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办?”
有着这样类似困扰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他们对另一半的感情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荡——时而将对方视若珍宝,时而又将其视若仇敌;并且,他们对自己感情的这种“摆荡”束手无策,也往往因此很难拥有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
尽管,这样对待感情的方式,总是被笼统地概括为“作”,但其实,这背后可能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动机。

情感的反复,
可能源于“理想化与偏执化”的扭曲
理想化的扭曲(idealized distortion),指的是人们把他人过度理想化,认为对方是完美的,是真诚地、善良地爱着自己的;而偏执化的扭曲(paranoid distortion)指的就是人们偏执地认为他人是无情的,甚至是会欺骗和伤害自己的,即便事实并非如此(Clarkin,Yeomans, & Kernberg, 2006)。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理想化某一些人,比如,美好的初恋情人,又或者偏执化另一些人,比如,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然而,不同的是,有着理想化与偏执化扭曲的人,他们的理想化与偏执化都是极端的,并且是在对待同一个人时交替产生的感受。
正如留言中所说,他们会在理想化伴侣的时候,把对方认为是完美的,而在偏执化的时候,又认为对方一无是处,并且关系里的一些小事,比如对方是否及时回复自己的消息,就会激发他们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来回“切换”。
事实上,这种理想化与偏执化的扭曲,是一些人应对内心负面感受的防御机制(Clarkin, et al., 2006)。
人们之所以会形成理想化与偏执化扭曲这样的“防御机制”,与他们童年的不良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不仅如此,这些“负面的感受”,比如内心的焦虑感或不安和痛苦,有时候可能也并不来于当下的这段关系,而是童年的痛苦经验,它们仿佛久治不愈的伤口,持续地隐隐作痛。
甚至可以说,真正让他们的陷入情感反复、“时好时坏”的,可能并不是表面上对方是不是及时回复了消息,而是过去的经历在他们内心里遗留下的焦虑、不安和痛苦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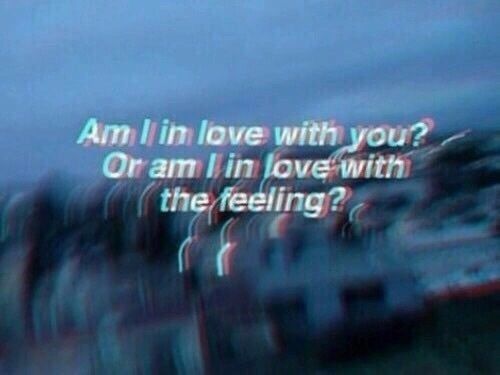
那么,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人们形成这样的理想化与偏执化的扭曲呢?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当我们还是个婴孩的时候,由于认知与心理功能尚未发育完全,我们对于外在他人的认知是局部的、碎片式的。比如,当照顾者(主要是母亲),回应我们的需求时,我们便会认为Ta是“好的”,而当Ta未能回应我们的需求时,我们便会认为Ta是“坏的”(Klein, 1935)。
随着在与照顾者的互动中积累了足够多的被满足/关爱的经验,以及认知能力的发展,我们才有了对“外在现实与内在感受”复杂性的理解力和容忍力。
意思是说,我们才能够逐渐认识到真实世界并非是非黑即白的,“好与坏”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才能够理解“一个我认为的好人、爱我的人,也可能做出一些让我感到不满的事”,并且在照顾者偶尔无法满足我们的时候,逐渐学会去忍受这种暂时的不快。
由此,我们也才拥有了一种对他人的完整的、连贯的认知(anintegrated concept of others)(Klein, 1957; Clarkin, etal., 2006)——在成年之后,当面对所信任的人偶然做出的令我们不满或失望的事情时,我们对Ta的态度与看法也才不会轻而易举地被颠覆。
相反,如果我们在幼年时期,没有得到照顾者足够的关爱与回应,甚至持续地被忽视或虐待的话,我们对他人的认知便会停留在之前的“分裂”(splitting)状态(Klein, 1946),即在绝对的“好与坏”之间来回摆荡——当对方做出让我们满意的举动时,我们便会“理想化”,而当对方令我们不满时,我们便又立刻“偏执化”对方。
不仅如此,幼年时得不到回应与关爱,还会在我们心中留下持续的焦虑、不安与痛苦等负面感受,这便是前文所谓的“久治不愈、隐隐作痛的伤口”。
在过去那个“创伤性”的环境中,理想化与偏执化扭曲的确是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与保护作用的,比如,它使得人们在得不到满足与爱的时候,可以通过理想化在内心拥有一个的完美照顾者的陪伴。
不过,当人们不再处于那样的情境时,就需要有意识地去觉察自己的这种理想化与偏执化的扭曲,并且管理和调节与之相关的情绪和行为。因为显然,这种模式,对关系有着巨大的破坏力。当偏执化扭曲发生时,对关系是充满毁灭性的。
缺乏主动控制力(Effortful control),
“情感反复”便转化为损害关系的举动
人们之所以能够有意识地调节和控制自己,避免让情感的反复伤害到彼此的关系,就需要依赖于一种被称为“主动控制力”的特质。
主动控制力,指的是人们能够在面对一些情境时,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的“首选”(dominant)反应,而选择做出“次选”(subdominant)反应的能力(Rothbart &Bates, 2006; Eisenberg, 2012),它涵盖了人们对于自己注意力、情绪、行为等的自主调节能力,是个体自控力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当面对对方在某件事情上无法满足我们,比如,没有及时回复消息时,我们能够主动地控制,有意识地让自己从“关注对方没有回复”(首选反应)转移到“想着Ta平时有空的时候都是会及时回复消息的;Ta很坦诚,有什么事情也会直接表达;Ta一直以来都很爱我”(次选反应)。
抑或是,我们会在对方没有回复时,感到愤怒。而愤怒可能会让一个人做出冲动的、破坏性的举动(首选反应),比如疯狂打电话联系对方,逼迫对方给解释,威胁要分手等等,然而,主动控制会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愤怒的同时,选择不做出冲动的举动(次选反应),比如,试着等到对方回复自己时,在询问刚才不回复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这种主动控制力不仅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避免“一叶障目”,让人们主动地去看到对方当下的行为之外的“整体”,避免自己因为偶然的事件就全盘否定对方;也能够帮助人们调节和控制冲动的行为,避免因一时情感的波动而做出伤害关系的举动。

这种主动控制力的形成与发展,被认为受到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那些在基因上表现出某种与血清素相关的多态性(serotonin-related polymorphisms)的人,更可能天生缺乏这方面自控的能力(Eisenberg, 2012)。
另外,中科院对双生子的研究证明,那些从小接受更多温暖平和、更少敌对严厉的家庭教育的孩子,能发展出更好的主动控制力(Fei, et al., 2011)。
研究者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孩子能够在与家长的互动中,观察学习家长们“主动控制”的行为模式(Eisenberg, 2012),比如当父母被孩子惹怒之后,仍能心平气和地与之讲理,孩子便可能从中习得面对愤怒所能做出的次选反应。
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也会困惑:如果自己也是这样容易情感反复,时而将对方理想化,时而又将对方偏执化,并且常常都控制不住做出伤害对方和彼此关系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如何应对情感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