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内参导读:虽然时值五月,2017年还未过半,但央视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已然成为今年当之无愧的现象级节目。它不仅如一股清泉浸润了国人因忙碌和浮躁带来的文化焦虑,对于电视内容制作行业来说,其在文化类节目模式上的突破和创新更是带来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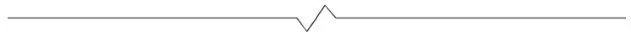
今年4月,在戛纳电视节期间,央视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收到来自法国赫夫·休伯特电视制作公司的邮件,询问《朗读者》是否有出售节目模式的意向,并称《朗读者》是他们公司近年来看到的最让人眼前一亮,最令人兴奋的文化类节目!


业内人士深知,文化类节目并不好做,《朗读者》为何能享此盛誉?在5月23日举行的《朗读者》第一季研讨会上,业内专家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朗读者》在文化类节目创新传播上的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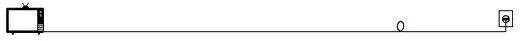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院
研究所所长赵白生

三秀合一的《朗读者》以老为新,以智创新,品静养心。
“老人秀”、“智肌秀”、“静心秀”是赵白生为《朗读者》下的三个定义。
老人秀:在赵白生看来《朗读者》的节目中一共有20多位老人,这些老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宝,“老人秀”就是以老创新。因为温故知新,节目在旧和新之间的关系平衡上,拿捏的非常好。
智肌秀:就是秀出“智力的肌肉”。赵白生解读央视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龙头,就必须要有龙头节目,在龙头节目中必须要包含抱负和理念。我们作为大国公民要养成阅读的习惯,保持强烈的求知欲。《朗读者》在这方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通过阅读培养大国公民智力的肌肉,是以智创新。
静心秀:在《朗读者》的首期节目中,许渊冲先生虽然在舞台上很激动,但是他中英法翻译第一人的名头是几十年来静心做一件事才能取得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人心越来越浮躁,读书使人心静,《朗读者》是在培养国民深度安静的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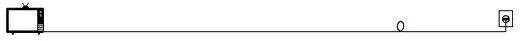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传媒中心秘书长冷凇

一、《朗读者》理清了电视、广播和手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电视节目融媒体化的成功尝试。
在冷凇看来,新型传播方式的兴起并不能构成唱衰电视的理由。在大众媒介中,电视由于线性播出反而有瞬间爆点,所以一个收视率再低的节目,它在播出的时候,全国也有百万人观看,这是任何一个网络节目都比不了的。但融媒体时代下的电视不光要看,也要听,更要拿起手机拍摄转发和移动端的分享。
而《朗读者》恰恰具有了移动欣赏和跨屏多屏联动的属性,理清了电视、广播和手机三者之间的关系。
电视重品质,重审美,有画面,广播重便利,重想象,手机重分享,重解读。错过的电视内容,可以在手机、网络、广播中重新实现。《朗读者》将三者以电视为龙头统一在一起,是一次融媒体的盛宴。
节目中最为难得的是所有的小段落都可以拆解为短视频传播,节目通过每期的主题词,把嘉宾进行创意性的组合,突破了传统的歌手与演员,科学家与作家的壁垒,突破了传统的名人光环效应,设立了自己的独特符号。
电视、网络、手机形成了传播的闭环,这是所有的节目都没有达到的一点。除此之外,《朗读者》通过嘉宾人生分享,传承经典美文,万众得到心灵震撼,形成情感共鸣的内线闭环。两个闭环造就了一个现象级的节目。
二、《朗读者》是电视艺术美学近年来的标杆。
冷凇认为把开放语境的诵读和私人语境的内心剖白完美结合是《朗读者》特别棒的一个创新点。在一般的访谈节目中,上千平米的录影棚,几百平米的舞台,很多观众的情境下,嘉宾是不可能说出心里话的。《朗读者》通过客厅、书房、剧院三处场景结合,营造出温情的半封闭的空间,为嘉宾提供了吐露心声的环境。
访谈的本质是提炼、追忆和升华,董卿的访谈艺术十分高超,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人生节点的抉择时刻,把抉择时刻的这个点放大,让人物在大是大非、巨大困境面前形成记忆突破,这种感受和朗读美文的体验相结合,引人入胜。
同时董卿在节目中写真微电影的部分,是一个浓缩的精华,无数名人名言与董卿大气端庄温婉的气质相结合,形成听觉、视觉上的双重美学享受。
在素质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表达,中国人在表达方面的能力是欠缺的,讲述中国故事,朗读是最基础的。《朗读者》促成朗读习惯的回归,完成了素质教育中这一块的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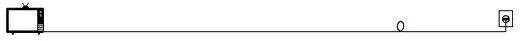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新媒体新闻部主任杨继红

电视应该回归到识别感、回归到人格魅力、搭建交互的入口。
杨继红认为《朗读者》的成功在于其栏目策划之初,就对思想内容、目标受众、节目样式、制作风格等定位非常清晰。一般的栏目都在完成很多期之后才明晰定位。《朗读者》从亮相就已经表达了精神内涵,而率先完成的精神定位正是它成功的一个妙招。
并且《朗读者》是一个兼具文本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节目。每一次朗读都成为一种文本,一个适合在未来的媒体端、移动端持续发酵、引领传播的文本。而原来的文字作品加上朗读者的朗读创作,和朗读者自身的新闻故事、背景故事,生命历程,全方位融合就具有了文献价值。
杨继红说,在今天做新媒体的时候,经常会被质疑,是不是把移动端做大了,引流了电视的观众,其实从《朗读者》的反向可以看到,新媒体所获得的份额也可能倒流回电视,大小屏的互动应该是一种内容的双向流动。
电视首先应该回归到它当年的识别感,观众能找到它,认得它,等待它;第二电视回归到人格魅力时代,董卿就是《朗读者》的精神形象和符号,而更多的节目都应该具有极具识别性的个人魅力。第三电视要搭建交互的入口,让用户从一个围观者变成一个使用者,开掘用户价值,搭建它的交互入口,设立它能够与用户和观众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线下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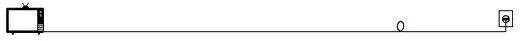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

《朗读者》用文化节目的一种探索,一种姿态,回答了市场的严峻问题。
俞虹说,一个电视节目自从出来之后,就一直被大众文化学者批判,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快餐化、碎片化、浅薄性、工业化生产的产物,它是以大众文化的消费为主体媒体形态。因此它和文化、和雅文化是有距离的。虽然内容人做了很多努力,尝试了无论是散文、诗篇或者其他很多文化形式的各种节目,在市场上又很难得到认可。
就在电视目前这样的媒体形态,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在不断的叫衰叫微的背景下,《朗读者》用文化节目的一种探索,一种姿态,回答了市场的严峻问题,电视究竟能不能做文化节目,怎么做文化节目,这是一个内容问题,还是一个形式问题?
《朗读者》在锐意创新中,回答了形式就是内容,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天然的、清晰的切割下。单看节目形态似乎主要是访谈+朗读+轻解读,但其实应该从董卿的开场白甚至是一个导语环节算起来,这才具有一个节目的完整性。
《朗读者》非常强化形式感,这种形式感几乎无所不在,董卿在导语说完之后,开始走进访谈室,这一段距离,这一段时间,在某种角度是一种停顿,它表达了一种尊重,让受众有一种期待。同时制造了大众传播中访谈双方的私密感和亲近感。那道门,在观看者和访谈者中,形成了一道有形的墙,却消解了访谈双方心理交流和传播当中无形的心理的墙。
在内容方面,《朗读者》充分地利用了网络空间和多方面的视听传播,社交媒体,而且用了很多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主题化的传播方式。《朗读者》一期要进五六个嘉宾,这本身也是一种碎片。但是它一个个碎片被关键词串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美丽的有意义的审美整体。
真人秀的出现似乎将主持人边缘化了,但《朗读者》,中央电视台,给了有能力、有情怀、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主持人足够的空间、平台和信任,让她施展自己,以她为主体的进行主创。
这样就使主持人、制作人一体化,她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最后一个环节的呈现者、冲刺者,更是一个节目完整的主创人员,一个核心人物,这一点能带来好的节目或者好的东西,《朗读者》能够成为一个样板,成为一个个案,这是它最大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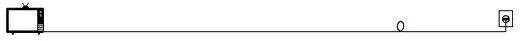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康震

《朗读者》用朗读传承经典,用经典升华你我,用你我诉说故事,用故事凝聚大国。
为什么要朗读,就是每个人都很想诉说,而且不仅想诉说自己,也很想秀自己是怎么表现经典的,并且希望用这些东西的效果来激励其他人,是放巨大的善意,这就是朗读的本质。
文本的选择与《朗读者》的高度契合是其具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濮存昕朗读的宗月大师,表达的就是一个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光明,这个人是他的拯救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一个故事。
还有就是邹市明和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孩子,我记得有一个片花说这是史上最难录的一期,因为孩子太难录了,但展现出来的那篇文章《猜猜我有多爱你》,非常让人感动。我觉得邹市明很不容易,他的老婆也很不容易,然后念这个《猜猜我有多爱你》,就满足了他要诉说我们又很想倾听的需求。
其实这就是创新,本来文本是传统的,邹市明作为一个拳击选手也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接到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了。
《朗读者》把朗读和诉说叠加在了一块,给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故事,因为是真实的故事,朗读经典才更感动。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清华大学的老先生们,一百多岁了,在读《告全国民众书》,这个非常震撼,非常真实的历史,那些老人家们,让人觉得那些庞大的有生命力的,巨大的群体依然存在,而且影响着我们,我觉得这就是创新,甚至在情感的方式上都创新了。
《朗读者》用朗读传承经典,用经典升华你我,用你我诉说故事,用故事凝聚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