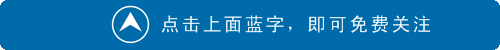
土 家 野 夫
又名野夫,中国自由作家,著名编剧。代表作《江上的母亲》2010年获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2015年根据野夫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改编的同名电影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并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一个被警察剃光头发的大学生,发配回乡教书,这成了当年酉阳的重大社会新闻。李亚伟的所有家当几乎都被他卖光换酒了,扛着剩下的一箱图书,在乌江边像战败的项羽和石达开一般沮丧。那个年代,没有自由择业一说。不服从分配,就意味着自绝于党和人民。
他只好豪迈地来到酉阳乡下的丁市中学报到,第一次领工资时,他才惊喜地发现,他是全校稀有的本科生。他的工资竟然多到排名第四,他再也不用售衣沽酒了。20岁的他被安排直接教高三,有很多18、9岁的女生,看着这个打扮不俗的男老师,“隔着操场远远地爱他”。
也许因为明珠暗投的失意感,他依旧天天喝酒。每月工资只够花七天,然后就在小酒馆赊账。赊到小老板都要跑路了,只好独自喝寡酒。男生都喜欢这个不拘一格流里流气的老师,开始轮番从家里给他带下酒菜。他的卧室从来不锁,凡是见到桌上新添了卤肉,立刻会在班上不点名的表扬,以资鼓励这样的尊师行为。
领导之外,同事都喜欢这个毫无师表可言的年轻人。他带着大家打牙祭,说脏话,跟半老的女教师调情。丁市很小,当他奇装异服地出现在小镇黄昏,半街的寡妇都要引领翘望。眼看着校风就要被他带向邪路,书记语重心长地跟他谈心,意味深长地张罗为他介绍对象。
青春的寂寞慌张,谁都难免渴望红袖添酒。那对象是小镇储蓄所的员工,已然是全镇的形象窗口。一来二往散步吃饭,便含蓄暗示亚伟谈婚论嫁。书记的意思也是早结婚,早结扎,省得祸害人间。他那时已有云帆之志,自信不属于那块小土地。一听要进入下聘过礼的节奏,立马夹起尾巴跑得飞快。

初入社会的我辈,那时都对曾经的大学生活怀有依恋。更不要说还有风琴恋人,还有万夏等等坏种,仍在南充那个城市。他在1984年初回到南充师院,他的故事还在母校流传,学弟学妹像迎接金三胖一样热烈。万夏为他背诵了胡冬那振聋发聩的全新风格诗歌,两人开始商议成立“莽汉主义”诗派;中国第三代诗歌因此而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莽汉主义似乎没有宣言,只是在他们的一些酒桌讨论中,确立了基本的方向——那就是对第一代革命抒情诗和第二代朦胧诗的反动。莽汉主义诗派集结了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梁乐、李亚林、二毛和胡玉这些坏小子,因为共同的坏水,很快形成一种鲜明的风格。他们大胆引入口语和污言秽语,以戏谑、反讽和自嘲的态度,调侃当时的世态和各种虚假的人生。
那时他们还没有接触到美国的“垮掉派”,但在精神趣味和态度上,已经天然地与金斯堡之流一脉相承。他们的诗歌充满酒色和暴力,玩世不恭地调戏着主流社会,非常冷幽默地颠覆着“上流正派人”的三观。应该说,他们是诗歌界的王朔,他们比王朔还早地打碎了文坛的假正经和伪崇高,对诗坛普遍流行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反攻倒算。
在我这个同代人看来,当时全国涌出的上万个诗歌流派和社团中,真正形成独有风格,且能在历史中站住的诗派,莽汉主义几乎是独领风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开创了这样一种诗风,更多的是开创了一种真正诗意的活法,一种处世态度和立场。我几乎熟悉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基本用他们旁门左道的半生,实践和印证了他们当年的“莽汉”主张。
尽管两年后,他们便自己解散了这个诗派。但是一些诗人和作品,则永远地伫立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历史之中了。
1984年,21岁的李亚伟,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像一个发情的公兽一般,日夜挥洒着他的才情。
《硬汉》这首诗,几乎可以看出莽汉主义的基本风格和方向。他写道——我们这群不安的瓶装烧酒,这群狂奔的高脚杯,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
事实上,他从这一年开始,再也难以安分于他的乡村教师生涯,并不断用诗歌发起对高等教育和体制思维的嘲弄和对抗。《中文系》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被广泛传抄和朗诵的作品。我无须在此摘录其中的金句,这首诗几乎颠覆了整个大学中文系的传统教育方式,其反叛精神和讽世态度,足以影响广义的89前后两代大学生。
围绕这一基本主题,他写出的系列诗歌,可谓满目珠玑。《毕业分配》《读大学》《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司马迁轶事》《老张和遮天蔽日的爱情》等等,皆是特具这种揶揄风格且批判性极强的诗作。
那一年他苦哈哈地在中学讲台上,一边教孩子们弹吉他、饮酒,一边自顾自地胡乱恋爱着。医专女生、母校学妹、银行柜员以及乡村寡妇,都可能成为他笔下广义的女朋友,而唤起他强烈的诗性。他在古代和外国的一些诗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悲剧性缩影——他们这些骑着马,在古代彷徨的知识分子,偶尔也把笔提到皇帝面前去玩,提成千韵脚的意见,有时采纳了天下太平,多数时候成了右派的光荣先驱……
我和他在那一阶段,都在基层教育的职业中苦闷着,那是一个很容易颓顿的年代,牢骚满腹乃至自暴自弃地生活。他在《给女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若干年后你要找到全世界最破的,一家酒馆才能找到我,有史以来最黑的一个夜晚你要用脚踢,才能发现。不要用手摸,因为我不能伸出手来,我的手在知识界已经弄断了,我会向你递出细微的呻吟……

实际上他差不多只教了三年书,但影响了一大批学生。若干年后,这些成长为父母的弟子们,还喜欢回忆李老师的各种趣闻,甚至模仿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活法。他从1986年开始便不想上班了,回到酉阳县城以众筹的方式开了该县第一个火锅店。尽管这个餐馆半年后,便被自家兄弟伙吃垮。但是这一谋生方式,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中学书记无法容忍他的不务正业,各种干预,扬言要修理他。他直接赶去书记门前,狠撒了一泡长尿之后,书记的火焰顿时熄灭。之后,他获得了他游手好闲的自由,不断冲州过府,去成都和万夏杨黎等人厮混,并流窜各地以诗会友。他像武林高手出山访道一般,横行各地踢馆拜码头,结交各色英雄美女,将完全决裂于朦胧诗的一种狂放诗歌的种子,撒遍三江五湖。
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面对一场浩大的邂逅,我们不在乎吻着的是谁。草原上风和日丽,风把草原吹过去,地主从盆地跑过来。时间跑过去,人跑过来,一声碰撞就爆发了土地革命。拖拉机朝前开,一路上发动人民……
他就这样一路醇酒妇人地醉着,再也不想回归山中。他宁可在重庆帮周忠陵看租书店,和刘太亨混大学舞厅,与廖亦武何小竹扯卵谈,也不愿回到讲台上去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先生。其诗云——一些事情正在远处发生,我栽种,收获,用植物和动物杂交。我读了许多先贤的书,农闲习剑,将诗与命混为一谈,以墨汁和云酿酒,幽居在事物里……

1987年他来到武汉,如前述我们杯酒订交。他在武昌范道鉴的蜗居里一呆数月,开始猛追我们武大法律系的系花。他的情诗也是一绝,迥异于全世界的温情脉脉,像一个强奸犯一般的粗鲁——夏天你身材零乱,美得武断,在远方不断地花开花谢……此时月亮露出失身的欲念,美得像你熄了灯的瞬间,任我放进口中或送至刀下。森林充满失去树木的机会,到了冬天,你已含而不露。
系花是那种非常理性和务实的美女,在看穿了他的穷愁潦倒之后,含蓄地拒绝道:我只怕你是买得起马,却配不起鞍。他已经习惯了类似的嘲讽,只能在诗中自嘲——我们怀抱美人和疾病,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我们是已经厌倦流血和劳累的一伙,结庐隐居,在大白天指鹿为马,暗中又将鹿藏起来,把马放在南山。用植物的茎和叶入药,并轻轻呻吟。夜晚,我们家伙一硬心肠就软……
在1989年那个著名的初夏之前,他一直过着这种流窜作诗的生活。混火车票,闯海南,到各地诗友之家换穿干净衣服,几乎成了一种常态。有一次廖亦武赢了一笔诉讼费,请他大吃大喝;他至今记得他连吃了五盘回锅肉的快感。这一阶段,他的诗主要由酒和色这两大主题构成,当然还有打架——我不揍这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
那年六月,他原本在他表弟——莽汉派诗人梁乐在十堰的家里,避开了那场风暴。廖亦武来信要他回重庆,说著名外籍诗人戴迈和到了,万夏他们一起要开拍一个诗歌短片。于是他就去了,一起筹划要拍的却是老廖记录那场悲剧的一首长诗。那时已经是全国开始大搜捕的时刻,他们接近顶风作案的行动,很快被有关部门侦知。他和万夏老廖等六人,在劫难逃,分别住进了重庆的局子里。
在经历了最初的“走过场”,戴反铐,无数提审之后,他这种混江龙一般的角色,很快成了号子里的老大。老大也没有太多特供好处,憋得久了,还得自慰发泄青春的愤怒与压抑。被看守发现后,臭骂他“到这里来了,还想搞享受”。于是,拖出去一阵电击,差点治好了他这打小落下的恶习。
经过五次起诉,法院还是无法给他们认定一种罪名。白白关了两年之后,通知他老家的公安前来接他回去。漫漫还乡路,这个一直坚持着诗和远方的汉子,终于还是被押解回家了。路上第一餐,两警官关切地问他“要喝一口吗”,他久渴的饥肠在一口一两下肚之后,竟然马上就被麻翻了。
既然无罪,那还得把他安排到酉阳教师进修学校。大家私下拿他当英雄,谁也不敢安排他工作。他就这样晃荡着,很快写出了他的牛逼组诗《红色岁月》。这是一组至今尚未得到诗界真正重视的诗,当然他也从来不把诗界当一回事。他在其中一首中写道——我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骑马站在赴试的文途上,一边眺望革命,一边又看见一颗心被皮肤包围后成为人民中的美色……
那时,无罪被关押没有国家赔偿,但是工资还得给他补上。两年青春,换来了两千多元的积蓄,相当于政府帮他强行存款且没有利息地还给了他。但这已经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大的一笔款了,他怀揣着这笔巨款,决心再次走向远方。

1992年,二渠道民营书商开始在这个国家暗中发展起来。和他同时出狱的同案万夏和刘太亨,已经开始当枪手,帮那些书商撰稿,过上了天天酒肉的生活。他们帮他介绍客户,根据甲方要求,他这个伟大诗人很快编写出《十大军事强国》《兵器谱》等等下三滥巨著。但是,他拿到了最初的几万元,这让他对生活重新恢复了一点自力更生的自信。
北方传来消息,二渠道书商的据点在北京的惠侨饭店。在那里,书稿好卖,价格不菲。他依旧一身破衣烂衫,像一个访民一样闯入了首都。那些书商每个人长期包一个房间,收购书稿,在床上摆摊批发图书,巨大的现金流在滚动。他挨户去发名片,兜售他的选题。胖哥陈琛正在点钱,他离开后,胖哥才看清楚他的名片上的大名。
胖哥也是当年主编《现代诗》月刊的行内人,急忙追到走廊上逮住他问:你是四川写诗的那个李亚伟吗?答曰是。如雷贯耳的名字,竟然成了如此落魄的卖稿人,胖哥立刻把他拖了回去。好酒好肉之后,胖哥问他想挣多少钱,他说挣五万,就回家写诗。胖哥大笑,劝他留下做书商,百倍于撰稿。他说没钱做书,胖哥叫来东哥一起给他投资,他很快自编自印,做出了《李鸿章家书》《左宗棠家书》。卖完几弟兄分账,转眼拿到了十万。胖哥问还回去写诗吗?他说钱这么好赚,日马不走了。
那时的二渠道,还真有江湖古风。诗人们凭借神交,就这样古道热肠地互相拉扯着上道。到我出来时,他们依旧这样提携了我。后来,亚伟、胖哥和郭力家三人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过起了同居生活。我也经常去借宿客厅里,四兄弟天天大酒,各种乐趣。有一年,胖哥拉着亚伟合作投资一套书,几十万被人骗了,胖哥日夜焦虑,深觉不安。亚伟郑重地请胖哥喝酒说:这几十万也是赚来的,没了就没了,我不能看你这样,咱们兄弟还得快乐生活才是。
亚伟的大度和大方,江湖有名。大起大落过的人生,荣辱沉浮贫富都已看淡,任何时候的出手开言,都透着清贵之气。当然胖哥也是那种负责的人,他找来了东北多年的老兄弟马辉,这个满身刀伤的诗人,竟然帮他们讨回了损失。其中的故事,留待以后写马辉这个长白山老怪时再叙。
赚钱买房,结婚生子,开公司发工资,喝酒泡歌厅,我们这群曾经的诗人,在90年代的北京,开始过上了优裕而庸俗的生活。有时大醉醒来,看着满地狼藉,我们空洞的眼神互相质询——这就是我们曾经想要的日子吗?
2006年,名满天下的他,终于出版了平生的第一部诗集《豪猪的诗篇》。这是中国诗人少有的能够纯粹走市场销售几万册的书,精选了他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他在封底说——我喜欢诗歌,仅仅是因为写诗愉快;写诗的过瘾程度,世间少有。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在这一年,我们先后撤离了京城,离开了书业以及日渐朽烂的都市生涯。他在版纳,我在大理,我们如愿而偿地过上了在云南当一个小诗人的生活。他的诗集不断推出,不断获得各种大奖小奖。有的奖品是一匹马,他也骑不走;有的是一块内蒙的荒草地,他也拿不回。
他写诗如篆刻,很慢很慢,半天下来,烟茶换了无数,划掉几十行,留下了两三行。他的诗如何好,留待理论家评说。我只想说,他是当代少有的几个创下了个人语言风格的诗人。他魔幻的想象力,奇异的修辞,神奇的语感,都是我辈望尘莫及的。更重要的是,我称赏的诗人,是那种真正诗意生活的人。他无论是对母语空间的拓展,还是对自由空间的抗争,都是对诗人这个词的一种示范。

我没有能力和耐心去一一分析他作品的独特之美,我更愿意记录他的前世今生,为这个庸俗的时代,留下一个真正诗人的活法样本。我们经常戏称他为李二白,他则自嘲为李有才。但我深知,遥远的未来,人民肯定记不住这个诡异的时代,曾经有过多少位主席。但是,一定会有他和一些诗人的名字,永垂不朽。
2017年正月初二
这是第229篇文章
值班编辑 | 小窗
-END-
文章皆为作家原创作品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欢迎将原文转发朋友圈
回复作家名字查看历史回顾:
蒋方舟 费勇 李海鹏 慕容雪村
冉云飞 土家野夫 王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