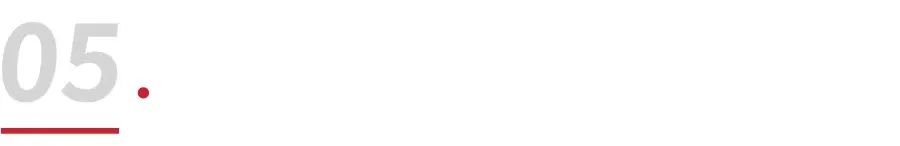随着新质生产力赛道不断提速,新科技的创业浪潮正在来临。其中尤其以低空经济、机器人等为代表,不断引领着一级到二级市场的资本热度,成为最受追捧的创投方向之一。
从概念到实践,从科技成果到商业落地,新质生产力如何与新商业双翼齐飞?
12月6日,
首钢基金十周年庆典活动
先锋圆桌论坛,砺思资本创始合伙人曹曦对话万勋科技创始人王峥,粤十机器人CEO江俊东,沃兰特航空合伙人、高级副总裁黄小飞。话题涵盖了机器人和eVTOL的历史性、结构性机会,市场教育和成本控制的挑战,创业中的关键抉择,等等。




机器人走进服务业是历史性、机构性机会
曹曦
:
三位都是创业者,大家在原有的商业系统里发现了什么样的变量和机会促使了这次创业?
王峥:
一个是服务业的迅猛发展。随着消费升级以及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服务的新需求增长非常大。另一方面是人口结构的调整。现在老龄化非常严重,有服务业的需求,却没有人承接,劳动力的缺口明显。所以机器人走进服务行业、离开工厂,是个历史性、结构性的机会。
现在刚性的、传统的机器人结构承接服务需求还有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创新则能够有效填补空白,解决问题。
江俊东:
我们集团(前海粤十)已经服务了中国接近40%的冷库,熟悉冷库这个特种应用场景的Know-How和运营。我们看到的痛点是冷库业和运营方面临劳务短缺、成本过高以及安全问题。机器人在这个行业的渗透率特别低,需求特别强。
集团原来主要做软件、供应链,有很好的商业生态和闭环,所以我们选择孵化一家低温机器人平台,结合集团资源一起解决冷链特种行业的痛点。
黄小飞:
我们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是观察到了四点现象。
第一,中国跟美国在低空经济领域有数量级的差距。我们的民用直升机只有美国的2%,机场只有美国的5%,能载人的机场只有美国的1%,而人口是美国的4倍,这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是不匹配的。
第二,最短的短板不复存在了。我们之前的短板是航空涡轮发动机和材料,电动化给我们送来了电极、新能源产业链和复合材料。
第三,低空经济有三个痛点,头痛、脚痛、心痛。头痛是指安全问题,脚痛是起降点不够多、距离远,心痛是成本太高,赚不了钱。
第四,每个产业都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要素,我们这个行业需要的是天、地、人、机。天是空域,地是起降点、机场,人是产业链的工人,机是产业链的配套。低空经济的要素在过去两三年时间里发生了10倍级的变化:10倍级的成本变化,10倍级的安全效率的提升……10倍级是破解企业发展的关键,能够吸引不同领域的人才、资源涌入,共同实现一个新领域的突破。

行业颠覆,从安全、降本、增效做起
曹曦
:
各位公司产品的创新点是什么?给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
王峥:
万勋是做柔性机器人的,传统意义的机器人使用钢性关节、电机驱动,应用在服务业时就面临几个重要的问题:安全性、任务适应性,以及成本。
我们从最底层的材料开始创新,把最传统的石油化工用碳氢链直接做成高分子材料,通过算法、智能的灌入产生精确、可控的运动,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机器人应用做了很好的整合。我们带来的新的技术框架是底层创新,从材料一直做到智能,给行业带来成本近乎10倍的下降,提供更好的安全性、户外长期使用的环境抗性,更适合大范围的商业化服务场景推广。
江俊东:
冷库内外的巨大温差是最难解决的痛点。我们第一款产品是无人叉车,常温的无人叉车已经比较卷了,我们则是第一家解决巨大的冷热交替环境中温差问题的企业,能够保证在冷库和常温交叉穿梭中的稳定运行。
我们现在也在研发狭小空间的半人形搬运机器人。目前冷链这个特种应用环境很难招到人,北上广深一个冷链叉车工一年的工资大概15万,我们的产品可以给业主和运营方大大降低成本。未来,我们希望全面替代特种应用的劳务工,给行业带来安全、降本、增效。
黄小飞:
我们希望带来的也是一款安全、皮实、好用的飞行器。安全是指采用最严苛的标准。皮实是指在基础设施不完善、飞行员不熟练的情况下,派遣可靠性要达到99.8%,每1000次航班不能超过两次的延误和取消,能够准时出行、高效出行。好用是指多应用场景、多用途,白天运人、晚上运货、平时低空观光,应急情况下还可以处理突发事件。
5分钟能够飞20公里,单座成本60块钱,一公里两到三块钱,如果这样的成本结构大家可以接受,我们放到景区,叫空中观光,装上货就是航空物流,放到市中心就是空中出行,飞远一点,城市之间就是短途运输。这是我们希望交付的产品。

用最小成本实现最大的商业交付
曹曦
:
目前大家的公司和产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为什么?
王峥:
让新技术在不同场景里被客户接受,这个早期曲线是比较难的。但接入后快速打开商业化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这个过程既考验初心,也考验企业执行力。
江俊东:
最大挑战是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商业化进展。
我们有场景,也做过很多前期的调研,有很好的商业化路径,但实际交付中存在客户教育的过程。我们的做法,第一步是转化存量,第二步是商业BD。我们公司没有太烧钱。
黄小飞:
如果去年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会是缺钱。今年的多轮融资缓解了这个情况,也让我们有了资金储备支持第一款产品商业化。
现在则是落地的难点,也即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和运营的第一公里的衔接。好的产品不仅是制造出来的,同样也是客户使用出来的。我们典型的特征是有半条命在供应商手里,供应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主机就会出问题。
从几个维度看,如果这个产业是千亿级,靠我们、供应商,还有股东的投资,基本能做到对存量的替代。如果万亿产业,空管效率会成为行业实质性的障碍和准入门槛。如果是十万亿或者更大的产业,成本就要大幅下降,降到两三百万买一辆自动驾驶的飞行汽车,那供应链会是极大的挑战。
另外,还有无人驾驶的实现。我们不能让每个人都去学一本飞机驾照,目前看起来它不比汽车自动驾驶简单,有很多复杂的地方。我们也期待跟AI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克服难关。

最正确的决定
曹曦
:
公司成立以来做得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是什么?
王峥:
彻底放弃做定制化,转做标品,这也是一个企业能够规模化、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江俊东: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做资本运作,小步快跑,现在也融了七八轮。手上有钱,就能更好地融资,才能把团队、产品打磨好。我们从去年8月份开始不断拿了一些产投,包括北京机器人基金、顺创产投基金等,这一方面意味着业务协同,一方面让我们心里不慌。
黄小飞:
如果只说我们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天起,就在做一款最小可交付的产品。我们选择了复合翼构型,以及世界上起飞重量最大且客舱空间最宽阔的设计,目标够坚定,没有走弯路,所以只用同行1/3的时间,1/3甚至1/10的钱,做到了现在的进度,最大化了资金效率和时间效率,让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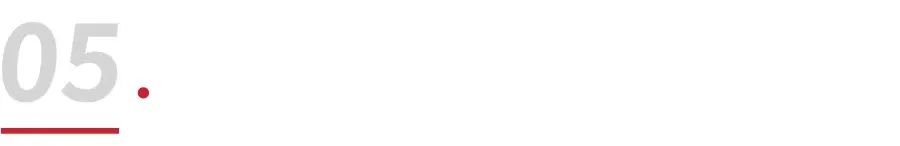
最难的是教育客户的过程
曹曦
:
新兴技术和传统产业是经济的一体两翼,各位的公司在跟传统产业融合或合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峥:
我们是一家技术创新型、平台型企业,对接的产业比较宽,没有特别深挖某一两个场景。我们有自己的时间常数和迭代周期,有对技术发展脉络的把握,但是不同行业的时间常数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何用我们的团队和自有组织流程去适应不同行业客户是有挑战的。
客户对我们技术的认可是可以教育的,但是他们原有的时间常数是不可教育的,我们只能适应,逐步迭代跟不同行业客户适配的不同方式。
江俊东:
我们这个行业很垂直,也特别传统,客户主要是一些国央企业、冷库业主和运营方,在无人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上他们越来越接受。目前最大的难点是智能硬件方面的市场教育。虽然已经有很多在合作的冷链园区业主,但是最难的是还没有合作的,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断教育客户的过程。
我们聚焦的产品是冷库使用频率最高的无人叉车。它一天要进出冷库100多次,这个场景选得很好,我们也很有信心把渗透率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做到很高。
黄小飞:
我们的供给端既有传统的航空供应链,也有新能源汽车的供应链,两方的历史性汇聚使得eVTOL成为可行。
我们作为新兴产业,像小马拉大车,要带着整个生态前进。相对汽车供应链,我们仍需要针对空中场景进行适应性的改造,确保产品更加安全可靠。这其中的每一点不适配,既是产品研发上的压力,也是整个行业发展前行的机会。
我们的产品还没出来,只是验证机在飞,就已经积攒了800多架意向订单,金额200多亿,一架飞机2000多万,约等于一个规上企业的产值。我们相信这个量会给供应链和投资人极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