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三观》剧照
母亲为这个一辈子的邻居哭了好几天,一直念叨当年自己没有卖上血,觉得又惭愧,又后怕。她甚至懊悔,自己当年没有把那件藕粉色的西装直接送给三姐,要是那样,三姐就不会出丑,就不会去卖血,就不会染病,就不会自杀。
我的家乡在中部某县的一个村子,村里有五十多户两百多口人,大部分同宗同族。村子离县城三十余里,二十多年前,村里人去一趟县城,要翻过两座大山,野树、藤子,长得漫山遍野,弯曲在茂密树林中的小路,没有路灯,更没标识,不识路的人,在哪个岔口走错了,想再出来,就难了。所以很多村里的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
山上的地,可以种土豆、红薯,稀少而狭小的田里,湿润些的,种水稻,旱些的,则种棉花,变钱的路子少,辛勤劳作一年,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也都勉强。
那时候村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早起红薯熬粥配咸菜,傍晚则吃上一顿掺许多白菜的煮“豆皮”。“豆皮”是村民的主食,用大米做成,把大米碾碎,掺水,做成浆,在铁锅上摊成薄饼,再切成细丝,晾干,像面条,但更有韧性,耐煮,吸水,半斤大米做的豆皮,能煮满一锅,够一家四口吃饱一顿。当然,晚餐要安排在日落以前,太晚了点灯费油,太早会饿到睡不着觉。
一周吃得上两三次米饭的是富裕人家,一般的人家则只在农忙或者重要节日时吃米:将大米掺水放锅,煮到七八分熟,连汤带米捞起,倒入筲箕过滤,汤则渗入下面的铁盆。滤过汤的米放篦子上,继续蒸熟,米粒饱吸水分,一小把米能蒸出大碗饭;滤出的米汤可直接掺点糖,做成婴儿的流食——这样的大碗米饭,不过是干一些的粥,不顶饱。
遇到镇上赶集的日子,凌晨一二点,公鸡还未打鸣,人们就从床上爬起来,走上三四个小时的山路,黎明时赶到集上,占个不好不坏的位子,卖点小东西,换几个零花钱。
因为穷,二十多年前,在这个村子,除了老人和孩子,壮年的劳动力,几乎全都在卖血。
三姐是我家隔壁的嫂子,她的丈夫是我的同族三哥,他们是靠“换婚”在一起过日子的。
三哥是镇上小学的数学老师,学校多年来招不到老师,随时面临撤销,远近好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年轻读书时,三哥考上过县城的高中,因为住校需要买饭吃,家里负担不起,在学校读了两个月,他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退学回家,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后来小学的老教师要退休,附近几个村的支书联名推荐,上过几天高中的三哥便当了村小的代课老师。他负责教三个年级的数学,一节课算一块钱工资,每周十五节,寒暑假没工资。即使这点钱,也很让村里人羡慕:“三哥口袋里的钱,就像地里的韭菜,月月割了月月又有。”
但三哥家,还是土坯墙、青瓦房,卧室里扯了张旧床单,做成挂帘,前面放农具粮食,后面藏着两口子的床。居中的一间算堂屋,供奉神像,摆着饭桌和几把椅子,地面是夯实平整的硬土,墙根处的老鼠洞,堵了又开。家里唯一的两个电器是:一台三叶吊扇和一台硕大的老式收音机。
三哥的两个儿子住在剩下的一间房里,屋里有一排矮矮的书架,上面整齐地摆了些书:《名优教案与课程设计》、《农家耕种百事通》、《中考宝典》,屋子里没有衣柜,孩子们的衣服都堆在两个装过教材的黄色纸箱里。
若遇上下雨天,家里漏水,三姐就拿着几个脸盆和塑料桶,在几个房间之间来回跑,隔着屋子,我都能听到她大声埋怨:“怎么又漏了?真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上次屋上的瓦又没检好!”
在娘家排行老大的三姐,每日天还未亮,就从河边打回两箩筐猪草;家里三分山地里,土豆、红薯、莴苣、白菜轮着种,人不歇,田也不歇;两亩水田,年年产的水稻棉花都比别家多。学校放了学,三哥也放下课本,扛着锄头去地里。在村人眼里,三哥家“文武双全”,即能教书,又能种地,一些农耕稼樯上的问题,大家总是喜欢向三哥问上两句。
“三哥,你看明天会不会下雨,我家稻田旱得快见底了,是不是得抽水浇地了?”
“不忙,等两天有梅雨要来了,不缺水。”
“三哥,下半年我家跟着你种新品种,那个产量高划得来啊!”
“嗯,这就对了,这个品种很适合我们这里的气候,病虫害也少。”
“三哥,这两天天气好,你家怎么还不移栽棉花苗?”
“马上北方有大风来了,棉花苗一移栽,吹得七倒八歪难得成活啊!”
三哥的回答总是很让人信服,他的奥秘在于——时常听收音机里农技员的讲座。
即便再勤劳,三哥家的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的:三姐常年穿一件洗得褪色的蓝布褂,颜色深一块儿浅一块儿,像癞痢头上的伤疤。三姐走亲戚前,总是先来我家,向母亲小声地借那件藕粉色的西装:“婶,把那件衣服借我穿穿。”
二十多年前,免费的义务教育还未完全实行,三哥家里的两个男孩到了读初中的年纪,学费、书本、伙食,都需要钱。我的母亲时常与三姐一起,去后山砍掉那些茂盛的野树,将柴薪装上板车,拉到镇上,卖给中学和卫生所食堂,每次换个十块钱。我的学费,就是母亲这样凑起来的。
每年收粮食,村里有开着拖拉机来收粮食的贩子,但三姐为了多卖点钱,都去镇上的粮食收购站。天还未亮,三哥将谷子、黄豆装在板车上,腰上系根纤绳,弓着身体,额头青筋暴起,三姐和年长的孩子跟在后头推车,二十里山路,来回一趟,耗上整天的光景。傍晚,他们回到家,一家人瘫坐在地上,喘粗气,擦汗,急切地数钱。
那一年,三哥的大儿子宝成即将考高中。村民都说读书太费钱,若不出头,就是血本无归,不划算,种地还能长庄稼。
三哥三姐可不这么想,为了给宝成凑学费,三姐跑了好几趟娘家。终于,有一天三姐兴奋地跑来我家,笑得眼角挤满鱼尾纹。她拉着母亲:“婶儿,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家的好路子,来钱快得很,我就说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孩子以后是有大出息的人!不光是读高中,以后两个孩子读大学都没得半点问题,只要他们有那个本事我就愿意供!”
原来三姐在娘家打听到,近年来附近的村里兴起去省城卖血:“有人专门领着坐车,住旅社,输完血就能拿到钱,一茶杯大小的血,能卖三十五块!身体好的,一个月能卖三趟血呢!”
三姐带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人们都沸腾了,急切地打听,做好了打算。几个胆大的邻居跟着三姐,走她娘家人那边的关系,第一次去了省城,隔天傍晚,一辆拖拉机就进了村子,连续地鸣着喇叭,将卖血的几个人直接送到三姐家门口。
三姐朝围观的人群大声地炫耀:“这趟去省城,我算是面包车、大客车、拖拉机都坐过了,哪一个都比板车快多了,去县城原来只要一眨眼的工夫,人躺着还没眯上眼就到了,真快活!”
同行的人也附和说:“卖个血,很简单的,我们跟着三姐的娘家人那边一起,带上身份证,先在那边村里排队,人家免费给抽个血,第二天等通知,血合格的人,下午就能一起坐拖拉机去县里,那边有大客车等着我们去省里。”
还有人从怀里掏出几张十块的钞票,得意地在大家眼前抖了抖:“在省里的旅馆里抽完血当场就给钱了,一人还有一杯糖水喝,甜得粘牙,哈哈!”
抖钱的人继续回应着别人的问题:“一间房里住八个人,都是我们附近村里的,跟在村里一样熟!”
三姐他们的第一次卖血“出征”很顺利,每人都带回35块钱,真真切切。那天,大家聚在一起看热闹,兴高采烈地谈论在省城的新奇见闻:楼房很高,旅社的厕所能冲水,输血有护士。
人们再也不怀疑,从此,村人们脱贫致富,找到了新路子:省城卖血赚大钱。
卖血成为村里热门的话题,那些曾经谈论小麦长势、关心棉花价格的人,都在盼望着赶快卖了血,挣上一笔。
每当“血头”来拉人的日子,四十五岁以下的男男女女,每家每户的壮年劳动力,七八十个人,早早地就在三姐家门口的空地上,排起了两列长队。
“血头”是一男一女,都是三十出头,男的精瘦,梳三七分头,腰里别一个大挎包,穿皮夹克,警惕地看着排队的村民;女的则穿着白大褂,手指上戴着黄灿灿的金戒指,她喊序号,面无表情,语气烦躁。两人面前各摆一张桌子,用于登记。
需要登记的内容包括:人名、性别和卖血量,村民们顺从地回答,点头哈腰,生怕遭到拒绝。“血头”说:“卖200CC是15块,卖400CC有35块!”很多人犹豫一会儿,咬咬牙,头一甩,做出一副豁出去的模样,大声宣布:“我卖400!”
“卖血一月挣得比种地一年还要多,以前埋头苦干,都白过了!”三姐站在人群中夸张地宣传着。连村民眼里的“知识分子”三哥,也抵不住诱惑,加入了卖血的队伍。
三姐终于扔掉了那件褪色的蓝布褂,穿上一件新买的藕粉色风衣,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每月卖血,收入稳定,三姐走起路来腰杆直挺,说话的嗓门,再也不是她到我家来借衣服时的音量。
三哥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依然读初中,大儿子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他们花了高价,把他送进一家收音机里每天宣传的厨师培训学校——学厨师,包吃包住,顿顿管好,不用风吹日晒,前景也是一片坦途。
村里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摆脱了以往那种极度贫困、拮据的状态,好像家家的日子都宽裕了。农闲时节,村口树荫下打麻将的人多起来了,连围观的人也开始下注。
有人去过几次省城,熟悉了情况,干脆在旅店附近找了工作,或是在饭店里做洗碗工,到了卖血的日子,就径直去旅店。
我的二叔家里,卖血后的第二年,就买了一台拖拉机,开在乡间的小路上,突突地轰响,显得很是威风。他以前种地为生,后来在镇上给人拉货,送砂石、砖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村里同龄孩子的妈妈,每次卖血回来,总是捎回香喷喷的枣糕,我跟着吃过,质地软糯,味觉甘甜,刚闻着味儿,就恨不得立即吞下去。
看到这些人,母亲总是羡慕不已,念念不忘的,就是去卖血。
母亲一直没卖血,是因为她高血压。
早年父亲在部队当工程兵,懂水电,转业进入镇上供电所,是镇上聘用的农电工,拿固定工资。父亲的工作是农电线路维护,抄表,收电费,负责的区域包括临镇四个村及十余个自然湾,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镇上的宿舍,每月回来几天看看家里。
有工资,有庄稼,日子也不是过不下去,母亲平时一个人忙农活,照顾我和弟弟两个孩子,父亲实在担心她身体吃不消,一开始就坚决禁止她卖血:“如今这社会又不是吃人的社会,只要一家人有饭吃,能省的地方尽量省着花,用不着去卖血换钱,那终究不是个路子,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无非就一年要磨破好几双鞋子,我宁可一年四季打赤脚,也不让你去卖血!”
当然,我家的日子也实在不宽裕,我和弟弟很少有新衣服,还都是母亲娘家的表哥穿剩下的。有的衣服拿回来时,已经褪色,母亲将衣服洗干净,在山上采来红色的野果,煮出红色的浆水,当染料,浸在旧衣服上,所以,我儿时的衣服,大都是红色。
所以,母亲偷偷地托三姐排上了号,还是去卖血了。我依然记得那个飘满轻雾的三月清晨,母亲告别我,她去省城卖血了。
父亲照例不在家,天还未亮,母亲就早早地起床,在厨房里弄得叮当作响,煮好了一锅“豆皮”,喊我们姐弟俩吃了早餐,她才出门。
那天母亲穿了那件常借给三姐的藕粉色西装,脸上挂满笑,临走时,她搓搓手,望了望外面弥散的薄雾,转过头来对我说:“灯儿,妈妈走了,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枣糕。”
我看到母亲步履轻快地走远,跟其他卖血的村民汇合。拖拉机载着满满一车人,轰隆隆地驶向雾气迷蒙的远方。
这次卖血,母亲差点丢了性命。
后来听村里同去卖血的人说,在省城旅馆的简陋房间里,母亲刚刚抽出400cc鲜血,忽然,体内出现血压波动,她脸色苍白,头晕眼花,捂着心口,疼得说不出话,额头冒出大颗的冷汗。母亲的反应,把正在谈笑的其他人也吓傻了,不知怎么办。所幸,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才把母亲抢救过来。
身体舒缓过来后,母亲才对追问的医生承认自己有高血压。
“不要命了,完全乱来!”医生震怒,指着母亲,大骂一通——他不是关心这些卖血者,是怕出了人命,影响这门营生。
母亲红了眼眶,流出泪来,她既担心被父亲责骂,也想到要是自己一命呜呼,我们姐弟两个没人养会很可怜。她还很愧疚,怕自己惹怒了“血头”,让村里其他人卖不成血,断了大家挣钱的好门路。
母亲只好彻底断了卖血的念头。只是后来,看到卖血的人家给小孩买了新鞋、添置什么新家什,母亲的眼神便充满失落与无奈,总要念叨:“都怪妈不好,要是我也能卖血,灯儿你也能沾沾光,妈妈有高血压,让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
过年时,小伙伴们吃苹果、穿新衣,我总是躲得远远的。我家那件藕粉色西装,也再没人来借了。
三姐是村里卖血时间最长的人,前后近六年,她几乎每月都去。
几年以后,三姐的大儿子宝成从厨师技校毕业,被学校推荐到大酒店工作,然而,并不是当厨师,而是做客房服务员,用人方说,先做一年。宝成的弟弟,初中没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了,哥哥的经历让他觉得,读书没用的。
三姐全家都失望极了。
宝成压力很大,他知道自己读书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母亲身上抽出的鲜血。他接受了酒店客服的工作,当着很多熟人的面发过誓:“一定要混出个模样!”
后来在酒店客房服务时,宝成认识了一位出手阔绰的老板,那人怂恿他,到南方去挣大钱。出发前,宝成给家里发了电报:“妈,老板跟我买了去云南的机票,我们去缅甸做生意赚大钱,等享儿福!”
三姐接了电报很欣喜,把宝成的话反反复复讲了好几天:“我儿子都坐上飞机了!”、“马上就要跟着大老板出国做大买卖了!”、“我儿子终于要出人头地了!”
但才半个月,村委会接到了政府的电话:宝成在云南瑞丽一个小镇上贩毒,被警察抓了,请村委会和三姐配合调查。
后来宝成说,一下飞机,老板就以方便统一管理为由,没收了他的身份证和钱,到了瑞丽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去缅甸做什么玉器生意。
宝成这事让三哥三姐在村里抬不起头,三姐处理完大儿子的事情,就去了省城,跟着娘家亲戚收垃圾废品。
二十多年后,母亲和那些卖血的村民都已年过半百,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的人再也干不了重活,提一
桶水,就得靠着墙角歇半天;有的人吃不下饭,身体疼得睡不着觉,
整夜辗转、翻覆;三姐也病了,从省城回到家中休养,一待就是大半年。
回村后,三姐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她开始连续地恶心呕吐,去医院做检查才得知,她得的是丙肝,检查出来时,已经是晚期,很可能就是当年卖血时染上的。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三姐当年卖血染上了病!
那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也惊慌起来,大家相继都去做了检查。结果令人震惊:全村七十名老人中,五十余人感染上丙肝,其中十余人已是肝癌晚期,甚至有夫妇同时感染。
三姐来找我母亲,坐在一起说话,拉家常,记得那时,三姐说话的声音已相当虚弱,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很吃力。她伸出枯瘦的手,拉着母亲,诉说当年的贫穷与窘迫——有一年,三姐回娘家,依然穿着那件向母亲借的藕粉色女式西装,有邻居问起来:“怎么一年到头总是穿同一身衣服?”三哥为人老实,径直回答说:“只有这件借的衣服才合身。”三姐说,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状态,对于当年的三姐来说,卖血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
“哪里想得到会搞坏了大家的身体。”三姐心里对大家有愧疚,“这一辈子,不服,不服啊!我总是不认命。如今,我病得最重,都是孽障,该偿债了。”
母亲听得泪眼婆娑,说了一大堆宽慰的话,让三姐把心放宽些,好好休养身体,等着享儿女们的福,还说,卖血的事情,没人怪她,大家只是随大流,想多挣点钱。听完母亲的话,三姐灰白的嘴唇轻微抽动几下,想说些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
回家不久,三姐就自杀了,她趁家人熟睡时,吞了一把安眠药。入殓时,我看到三姐已经失去生命气息的脸,蜡黄枯瘦,但却平静安详,像经历了彻底的解脱。
那一年,三姐刚刚五十一岁。
母亲为这个一辈子的邻居哭了好几天,一直念叨当年自己没有卖上血,觉得又惭愧,又后怕。她甚至懊悔,自己当年没有把那件藕粉色的西装直接送给三姐,要是那样,三姐就不会出丑,就不会去卖血,就不会染病,就不会自杀。
编辑:朱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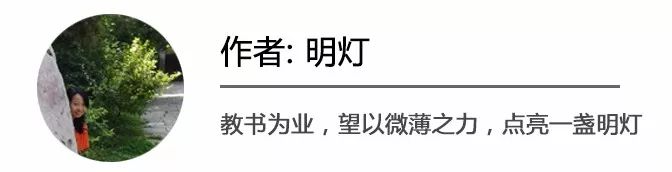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email protected],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推荐文章(点击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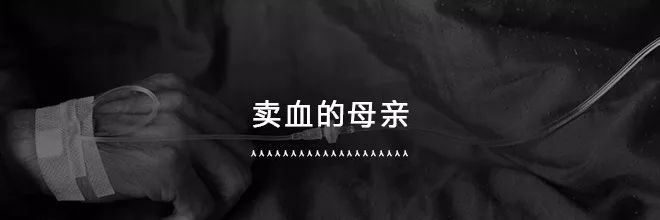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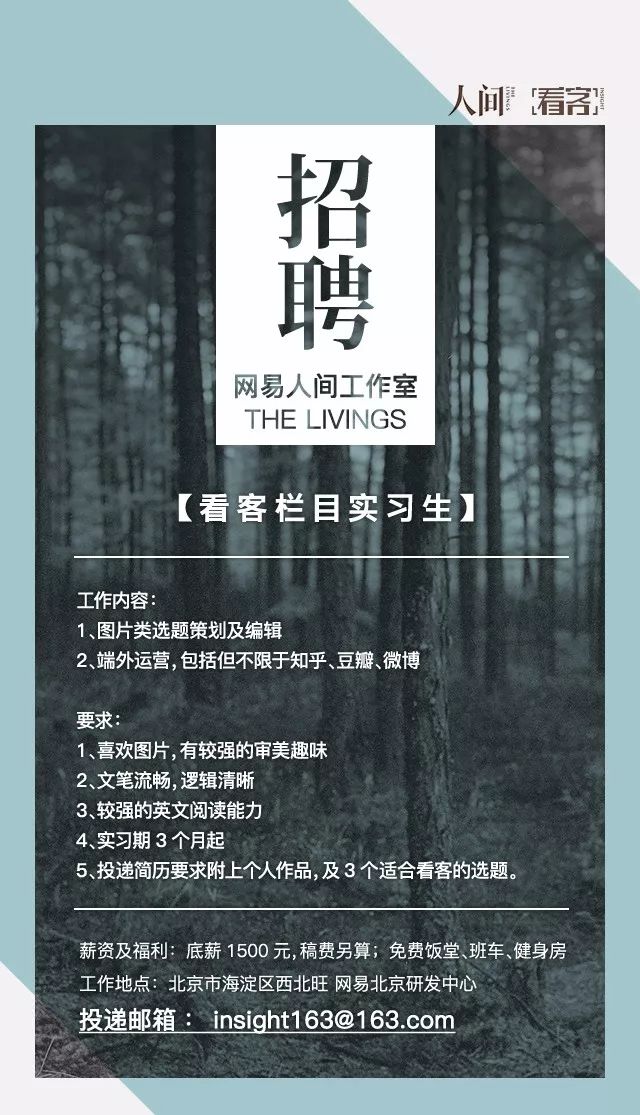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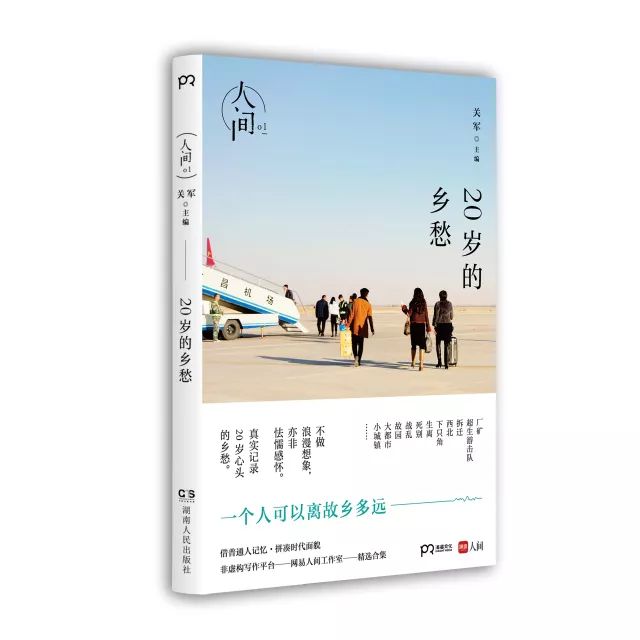
人间首部合集《人间01: 20岁的乡愁》
点击即可购买
点击以下「
关键词
」,查看往期内容:
祭毒
|
坡井
|
南航
|
津爆
|
工厂
|
体制
|
年薪十二万
抢尸
|
形婚
|
鬼妻
|
传销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血潮
|
失联
|
非洲
|
何黛
|
饥饿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