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曾经在2017年的贵州大数据峰会上提出:“如果不让孩子去学会琴棋书画,三十年后,将找不到工作。”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却有那么一群徜徉在艺术海洋里的孩子只能浪迹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用他们或饱含沧桑,或清冽美好的歌喉,吟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谣,来换取微薄的收入。
甚至,他们经常坐着火车去各地演出,一去就是好几个月,因为只有多去一些地方,才能赚到钱。
拥有艺术,却没有固定的收入,这是他们最大的痛苦。
1978年出生的叶三,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在她的新书《我们唱》里,讲述了一群让70后80后耳熟能详的音乐人的故事,包括老狼、张楚、李志、赵牧阳……他们的年少轻狂,他们的青春无奈,他们的追梦艰辛和苦苦挣扎,在叶三的笔下变得缓慢而温情,激烈而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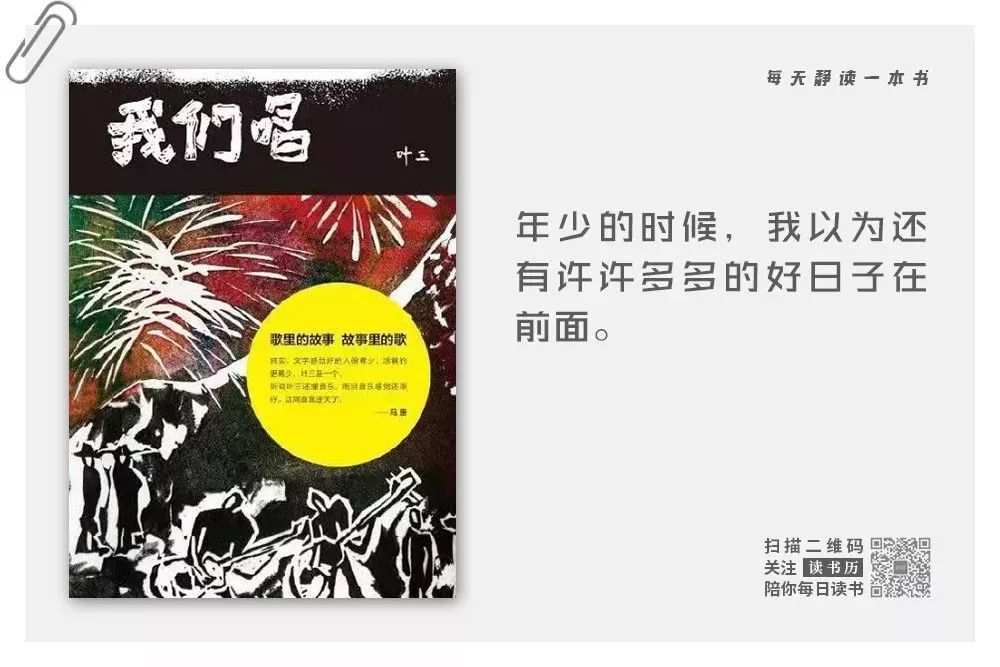
哪里有生活的疼痛,哪里就有回忆的丰润。那些曾经被音乐点亮的日子,是时光留下的无尽温情。
⒈
梦想来源于现实,又毁于现实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可以唱着自己的歌。他们是中国爱乐乐团的乐手们。作者采访了爱乐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大鹏,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大鹏是家里唯一一个学音乐的人,至于自己为什么要学大提琴,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仿佛只是因为被别人赞美“我觉得你拉得很好呢”,就坚持了下去。
大鹏初一就考入了北京艺术学校,那是外地来北京的艺术生眼中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最佳路径,即使每年学费两万五,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笔小数字。
艺术学校的学生都是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直升,课程安排也是文化课和专业课平分,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其他时候就是练琴。大鹏和他的同学们都特别刻苦,甚至有些每天六点就起床,当大鹏还没有吃早餐,人家已经背了两百个单词。
大鹏的整个少年时光,都是在练琴、比赛拿奖、继续练琴中度过的,当时,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是他唯一的目标。
然而,当他最终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然后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时,迎接他的并不是想象中辉煌灿烂的星光大道。
中国爱乐乐团是体制内单位,大鹏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面对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等生活现实。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不得不去参加各种企业在年底为职工和家属举办的音乐会,或者为电影音乐、流利音乐录音,甚至为娱乐节目伴奏。
这和当初的梦想差得太远,以至于大鹏就算知道不该说丧气的话,还是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在毁掉音乐家。
这就是音乐家的现实,和大鹏有一样烦恼的,还有小管,和小管的大学同学们,中央音乐学院大二学生,主修中提琴。
1995年出生在音乐世家的小管,从4岁开始,每天都要练一个半小时的琴。刚开始,是为了完成任务;后来组乐队,在酒店做驻场演出,一天三小时,收入一千元。
刚开始所有的演奏曲目都由小管负责,全是古典四重奏,后来酒店换了经理,要求改成流行音乐,加弹唱,小管气愤地说:“把所有的档次全部都给拉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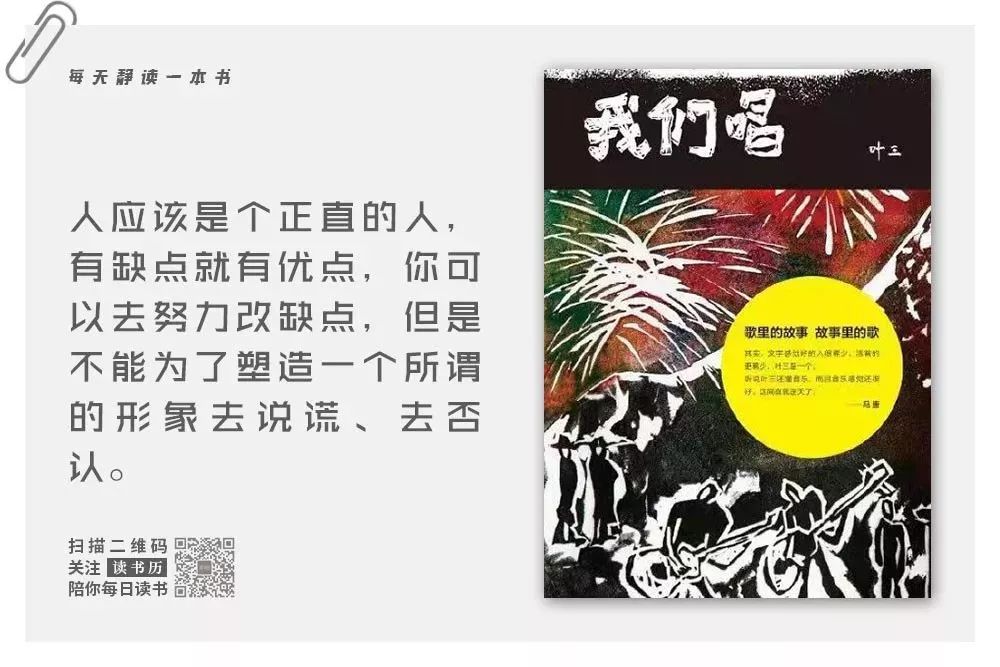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开始时告诉你要有梦想,然而却又冷酷地告诉你这梦想太过浮夸,到最后想要它的方式来让你忘掉最初的梦想。而它的方式就是,用现实告诉你,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其他都不要多想。
梦想成为了一种刺眼的存在,可生活就是这么的实在。
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大鹏选择接受,他不抱怨,他看得清现实,也明白古典乐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他十分清楚自己无法改变现实,在个人生活所迫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勇敢地面对。
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和他一样,当梦想遭遇了生活的风雨,还是不得不挺起胸膛,迎风而上。
小管却试图改变,他努力地寻找音乐和生活的关联,想要把古典乐的阳春白雪在生活的下里巴人之间找到平衡点,让自己的梦想不至于沦为家里的笑柄。
他和同样学习西洋乐的表姐一起开了个工作室,想要开发出一整套的,融合了多种元素,比如摇滚、戏剧、流行、爵士等多种形式的,能够用简单剧情串联起来的幽默音乐。同时,工作室也教一部分喜欢音乐,有时间、有能力去学琴的成年人。
几个月后,小管的工作室已经开办了四期音乐沙龙。第四期沙龙的地垫在鸟巢,是与鸟巢文化中心合作的,主题为“三重奏”……
不管是大鹏还是小管,他们音乐家的梦想都根植于生活,却又被生活毁灭掉,只留下苍白而孱弱的努力,坚守着属于自己的舞台。
梦想和青春一样,都是一种信仰。追逐梦想的人都一贯地坚定,即使路上有太多的艰难险阻,即使荆棘密布,他们还是相信梦想之花永远不会凋谢。
⒉
坚持还是放弃,梦想不只AB两面
如果说大鹏和小管坚守的古典乐,太高高在上,曲高难以和寡。那么作为相对来说能够被更多人接受的朋克,“生命之饼”的吴维面对的生存现状却并不比大鹏和小管他们更好。
喜欢画画、整天在街头过着混混生活的吴维,是偶然听到了Beyond的歌曲后,立马被深深地吸引,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朋克的。这个时候的他,连黑豹、唐朝、崔健都一无所知。
看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招生广告,甚至连贝斯都不认识的他,马上找了个朋友咨询,就买下一把雅马哈的贝斯,报名去了北京。
这样的吴维,在学校里没有人搭理他;也是在这里,打开了吴维的全新世界。他听老师推荐的乐队,买回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和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吴维回到武汉,然而却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于是,两个月后他又折返北京迷笛学校,认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他们结伴去了西昌,遇到了“山鹰”组合,写出了他的第一批“作品”——《拯救创作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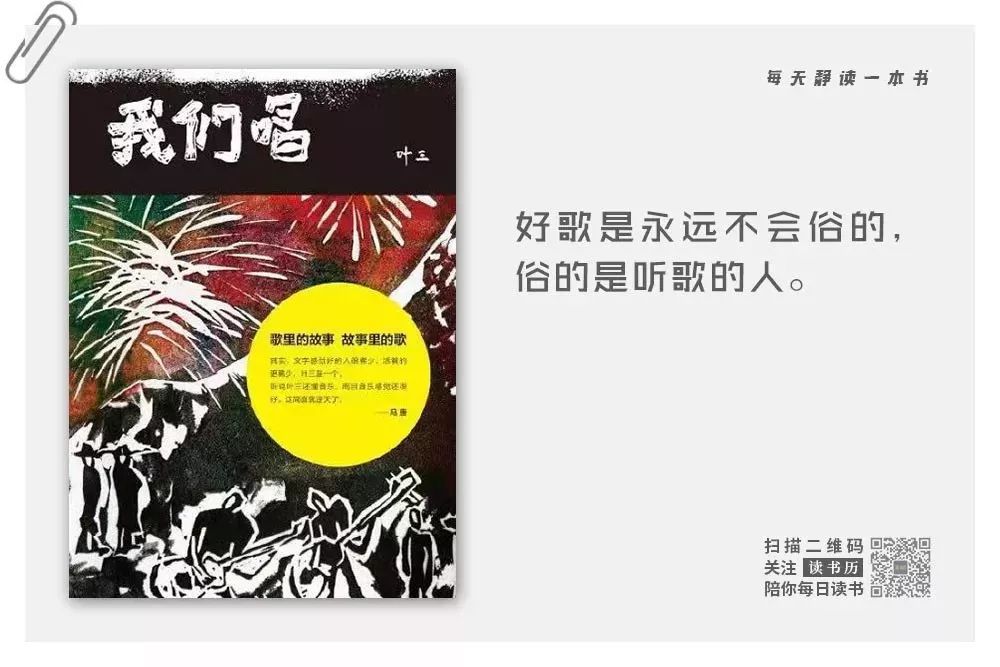
然而,在西昌,是没有人听这样的音乐的,于是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了武汉,找到迷笛学校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成立了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吴维担任主唱。
“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字,灵感来自几年前他偶然看到的一句话:“擎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
所谓的梦想之路,不是梦也不是想,而是一条路,只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才能慢慢地接近梦想。
能充灵饥的“生命之饼”在现实中却举步维艰。
排练了几个月的“生命之饼”,参加了武昌米高Disco迪厅举办的一场大型演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当吴维上台,对着观众大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观众呼啦一下子涌上舞台,又唱又跳,把摄影师都给吓坏了。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认为他们是来捣乱的。这是“生命之饼”的第一次演出,不算成功,但是吴维不在乎,因为这次的演出让吴维结识了武汉更多的乐队朋友。
后来在酒吧演出,没有遇到能够欣赏的人;然后去北京,然后开始巡演,但是即便如此,演出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收入。因为朋克音乐风格本身的粗糙、不悦耳和政治风险,很少有商业演出愿意邀请他们,而出版专辑和巡演最多只是做到不会赔钱。
然而这些,吴维都不在乎,他在“生命之饼”的主页上写过:“它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做着让我们觉得舒服、高兴而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搞朋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觉得过瘾。”
是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表达,需要一些方式来宣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只是现实,太过残酷,不喜欢人们如此张狂。
再后来吴维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在北京“开心乐园”办了一次演出,“生命之饼”压轴,前面的十几个乐队都是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的特色,让还没有上场的吴维,失去了兴趣,就算坚持到最后,也只是用16秒唱了一首歌,走人。
这年,“生命之饼”发表专辑《50000》,因为是公开出版物,歌词不得不删改了很多,从此,吴维打消在北京发展的念头,彻底回到武汉。
然而这一去也并不是处处天堂。
对朋克的偏见,大众的不接受,让吴维难以前进,他试图调整方向,想把“生命之饼”打造成为一支国际性乐队,去世界各地演出。
然而第一次走出国门,原本计划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最后却只演了泰国;第二次国外演出在美国,华盛顿DC音乐节邀请“生命之饼”,吴维想趁机在东海岸巡演,然而在上海飞底特律的时候,因为签证问题,还被警察拿枪指着……
吴维的梦想在现实面前变得弱不禁风,“生命之饼”前行的路上荆棘密布。然而这就是乐队的现实,和“生命之饼”一样,很多乐队的现状都不乐观,吴维的追梦之旅只是一小段。现实对他们的残酷压迫,比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但是吴维曾经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就不愤怒了,因为他把愤怒和不妥协全部放到了音乐里,“反抗精神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在中国,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明白这点的吴维们,即使生活潦倒,即使被全世界抛弃,有喜爱的音乐陪伴,生活也变得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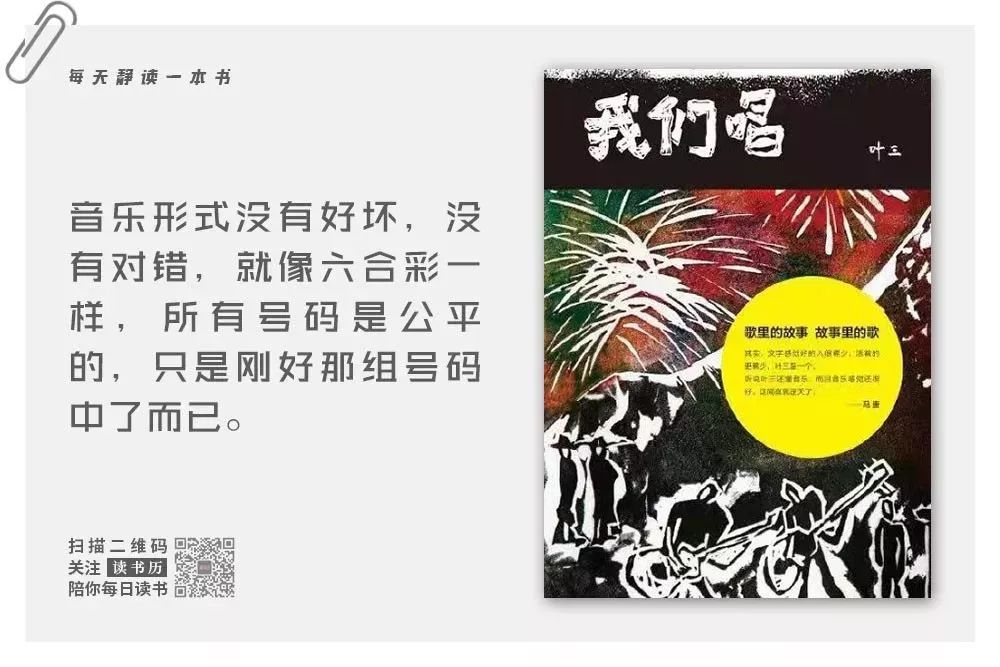
有梦想的生命,就是总有雨露浇灌的花草,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里,如此的鲜活,如此地美好。
⒊
没有妥协,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虽然现实残酷,但也有温情的一面。
老狼就是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第一次唱就红了,一首《同桌的你》在全国各地响起,白衬衫、牛仔裤成了文艺男青年的标配。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可以歌唱属于自己的青春。
不同的年代会造就不同的音乐,老狼和他的伙伴们处在真实的、浪漫的青春记忆中,而他们之前的青春记忆都是苦涩。处在这样的好时代里,还是得看清自己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只是,红了的老狼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是不写歌,但唱的每一首歌都只是在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单纯而有情怀。
他结婚生子,满足于现实安稳的生活,只是他知道这样的自己会慢慢失去激情,于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参加一些活动,推荐新人、唱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歌唱属于自己的记忆。就像高晓松评价的那样:“别人都是在唱歌,他是在歌唱。”
和老狼一样,用歌唱表达自我,找寻自我的,还有张楚。
张楚8岁开始到西安父母家,全新的环境里,孤独的他用爸爸的收音机听短波,看《世界之窗》和《译林》。被鼓吹远处的自由和西方文化的痛苦让张楚开始了自我的迷失。
不过从一开始创作,张楚就十分清楚地知道,音乐是他表达自我的最好方式。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感悟,去提炼,去创造。他也确实做到了。1994年,张楚和窦唯、何勇、唐朝乐队在香港红馆演出,全场一片沸腾,缔造了中国大陆摇滚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后来一路辉煌,一路迷茫,也一路追寻。
2001年到2005年,张楚从北京回到西安,开始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在租住的房子里,没有创作欲望,没有表达欲望,不跟别人交流,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虽然他生活并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也不高,不算缺钱,但始终没有安全感: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认为自己指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文学化的真理,却没有人去看。他试图找到一种让别人接受自己认可的真理的方式,却总找不到出口。
终于,时间给了张楚最好的答案,他逐渐认识到他对这个世界而言,该融合的就得融合,该自我的还是得自我,但不要去折磨别人,强求别人接受。
“有了艺术观就不再需要世界观。大家都是平扥的,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真理,可以自由选择”。
想通了的张楚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现在的他觉得那几年的自己都活在尖锐里,身处摇滚青年的圈子里,生活也很摇滚,但却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摇滚。
他不像李志,从一开始就清醒而敏锐,智慧而明智。喜欢唱歌,就去做歌手;没有天赋,勤奋就好了;管它网络还是音乐创作,讨论社会现实才是必须尽的职责……
人就应该正直,努力去改正缺点,但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而去说谎、去否认——没有谁纯洁无瑕。
尝遍人世的辛酸和无奈,享受过音乐带来的美好和幸福,在世事浮沉中逐渐明白,艺术和人生并不是势不两立。坚持梦想,找寻自己,才能让音乐和自己都精彩无比。
孤独的张楚、老板李志,身处好时代的老狼,被现实折腾的吴维和生命之饼,张玮玮和白银饭店……
很多年前,很多年后,他们都在那里;时光荏苒,他们变了,他们似乎又没变。圈里的故事,还在继续,没有那么多的光怪陆离,没有那么多的非此即彼。
时间总是仓促前行,留下一片狼藉和美丽,而我们只需带着对过去的回忆,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一路欢歌,直奔红尘万里。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对于这个栏目,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意见,欢迎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水木文摘”,在文章的留言区跟我互动。我会挑选最优质的留言,每期送出一本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