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选·美的第
991
篇文章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对美国教育中“阶层固化”的讨论,席卷了中文世界。《我们的孩子》,《乡下人的悲歌》……有多少新书得到译介,对美国社会上升渠道收窄、对贫者愈贫与阶级固化的焦虑,就有几分。
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燃烧到了教育领域。7月初,特朗普下令废除政府关于教育中种族平权的具体指引。这一指引是奥巴马政府对种族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具体操作指示,而其法理依据,源于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社会共识与1964年的《民权法案》。从1978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到2008年的“费雪案”,平权法案一次又一次被指责“逆向歧视”。而就在去年8月,还有消息指特朗普政府在研究打官司进攻平权法案。如今,这一议程似乎走出了第一步。
人们之所以关注教育平权法案的存废,是因为它关乎哪些群体能通过高等教育成为精英。平权法案规定就业就学制度中需要保证肤色和性别平等,而有人则认为这项法案制造了配额制度,从而偏袒照顾非洲裔美国人,使自己的孩子“分数高却上不了好学校”。
2016年大选中的另一大热门人物,民主党内的挑战者伯尼·桑德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批评教育问题:“我们曾经在世界上有最高的高校入学率。如今我们只排第12名。德国、丹麦、瑞典和很多国家都为年轻人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高等教育。他们知道为年轻人投资有多重要。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在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们看来,美国的高等教育收费极高,让出身贫寒的学生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债务,改善社会流动的效果有限,亟待一场激进的改革。
无论特朗普或桑
德斯的支持者,都将受教育与未来前景划上等号。桑德斯的理念反映出中产阶级的普遍担心。反对平权法案则折射着对机会争夺之激烈。在个人成功、种族平等和阶级冲突之间,我们如此推崇的美国教育模式,似乎走到了一个尴尬的路口。
问题是,在美国社会中,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地时间2018年5月2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视觉中国 图
当地时间2018年5月2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视觉中国 图
早在19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质疑过,高等教育的效果,可能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他通过研究写下了《文凭社会》一书,解释文凭“通货膨胀”的处境——美国大学入学率大大提高,大学里能学到的东西反而变成了套路,人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大学,只是为了一张名校文凭,而为了上名校,人们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却发现光名校毕业都不够用,还要继续读硕士、博士——就算博士毕业,也未必找得到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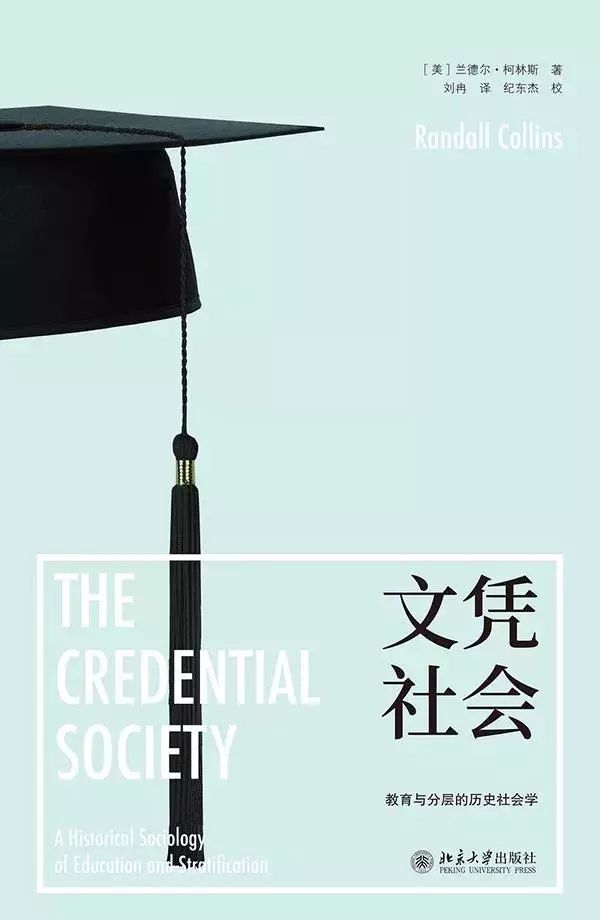
《文凭社会》书封
柯林斯认为,在美国社会中,长期有一种“技术主义”观念主宰着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教育带来知识,而知识带来职业能力,从而教育能把人“往高处带”。这种理论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在当代,因为经济和技术发展已经使得对体力劳动有要求的工种占比越来越小,而对技能和知识要求高的工种比例越来越大,所以教育水平必然水涨船高。
在今天,这种说法很成问题。如果教育水平和技能有关系,那么是否教育水平更高的雇员生产力就更高?而各种研究都证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进入一种“闲职”式的雇佣工作。怎么个闲法呢——人类学家大卫·格雷柏近来的“狗屁工作”研究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别看这些工作“狗屎”,要坐到这些位置上,人们依然要先经过多年高等教育,拿到一份学历。
讽刺的是,这些“狗屁工作”的技能,其实并不需要大学教育中的专业训练。而另一边,被视为社会精英的医生、律师等职业,在美国却不关大学教育的事——本科并没有这些专业,要成为医生、律师,你得考入医学院和法学院的研究生项目,再经历工作场所的大量经验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要挤破头去抢名校文凭呢?
首先,人们不见得讨厌“狗屁工作”——不需要太费力就能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仍然是很多人的理想;那么,既然很多人仍然需要“狗屁工作”,获得一份这样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获得什么待遇,就仍然要求人们去竞争。这就考验人们的社会能力和人脉关系;进一步说,因为“狗屁工作”没有什么技术门槛,所以能否得到工作,在工作中能否加薪、升值,就格外有赖于柯林斯所说的在企业职场中的“组织政治文化”。比较显白的话说,真正决定了人在“狗屁”的职场中位置的,就是一套“做人”的办法——拥有什么人际资源、如何调动人际资源、如何协调人际关系,等等。
而这些,与其说是在课堂上获得的“技术”,不如说是在高校的人际网络中学习的。在美国大学教育中,除了上课,还有大量的社团活动,人际交往、社交活动占据着学生的时间——而这才是高等教育对职场中人的真正意味。
这种状况下,文凭对于职场中人来说,就是花费无数时间精力买来的,证明自己掌握了“职场组织文化”的一块“敲门砖”。柯林斯将之称为“通货”,其实也就是货币。而当人们不断竞争获取这种货币,激发出越来越大的需求,而货币本身代表的“技术能力”又并不显著的时候,教育产品的供给就会水涨船高,人们竞相上游,而单个货币,即单个学位的价值就只可能不断降低——这就是高等教育的通货膨胀,它不只是一种现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货币链条。
诚然,“美国梦”仍在一些教育领域继续实现着:很多新一代移民自带高质量的教育背景,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接受教育之后,进入科技、互联网类的新崛起领域。这的确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与职场的关系,但总的来说,这并没有打破文凭膨胀的趋势。
自由市场的拥趸也许会认为,膨胀的泡沫最后自然会崩溃,无需过多干涉。但是,正如种种呼声中已经看到的,膨胀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庞大的产业,人们的学位水涨船高,用于教育的经费和债务也日积月累,社会的不公平在这种堆砌和泡沫中代代相传……但是,文凭教育的膨胀,也不可能从教育系统内部予以解决,因为它也是美国族群政治与政经结构的结果。
我们可以先回到《文凭社会》中的分析。柯林斯眼中的教育,与其说是阶级上升渠道,不如说是政治冲突与统治关系的承载者。作为一名历史社会学者,他笔下的美国教育系统,不是仅仅为了培养英才而诞生的,相反,它具有维持盎格鲁白人文化优势,保持统治身份的作用。
故事要追溯到19世纪末的美国。在那时,新一波移民高速增长,而与早年的新教徒不同,这一批移民中,很多人来自南欧、爱尔兰,信仰天主教。在盎格鲁-新教徒中产阶级眼中,这些天主教徒为主的新城市工人阶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代表着社会混乱、无秩序,他们觉得这些移民不务正业,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社会正统控制权面临挑战。
这种心态催生出了盎格鲁新教徒的两条族群问题解决之道,其一是种族主义的排外运动——美国最早的种族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段时间诞生的。二是教育改革——新教徒中的精英分子开始推动公立教育,旨在让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接受一整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用纪律约束他们的行为,不准迟到、不准旷课(为此甚至还专门立法),从而把他们变成可以接受的,行为举止和盎格鲁新教徒一致的“自己人”。从小学到中学教育的一层层公立教育系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套系统尚未影响到大学。大学文凭在早期美国社会中意义不大,它和中小学教育、学院教育,是完全平行的几个不同系统。
到了19世纪,新教的不同派别为了抢夺信徒,建立了大量的学院,作为自己宗教力量补充、更新、扩张的文化武器。这些学院扩张太快,开始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很多学院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倒闭者大有其是。于是,不少学院开始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因为“大学”传统上以大量仪式、社交活动闻名,这些元素正好和上层精英此时极为焦虑想要维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统治地位息息相关。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美国大学在19世纪末的崛起。它也逐渐建立起了和小学、中学教育的序列——大学开始把中学文凭作为入学的基本要求。
20世纪中叶,主流白人文化的社会控制,和愈发激烈的族群冲突之间激烈地对立起来。对饱受隔离、歧视和系统性压迫的黑人来说,教育系统是他们最不指望能够改变自身处境的道路。1960年代,是校园之外的黑人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带动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但民权运动中间的温和一派,为这两者之间达成和解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施行教育系统中的种族平权,改革者试图让黑人更多进入教育这个精英选拔系统,从而分享一些政治权力,减少激烈的社会冲突。
但讽刺的是,时隔多年之后,美国的公立基础教育水平饱受批评,从私立高中到私立大学的精英教育虽然在分数上体现对黑人的平等,学费却居高不下。好不容易进入这一系统的黑人学生发现,和自己竞争精英地位的白人学生参加各种昂贵的社交活动,兄弟会姐妹会,这些活动帮助他们拉人脉、找工作,黑人进入了大学却发现大学中还有一重门槛……教育平权并不妨碍盎格鲁新教文化继续维持对大学文化的垄断,而旨在解决种族问题的平权法案却更多停留在语言和数据上,格外尴尬。
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说,美国社会和欧洲社会格外不同之处之一,是它的社会斗争的基本单元由种族而非阶级组成。不像欧洲那样有成千上万工人参与激烈而鲜明的阶级斗争——美国的工人阶级直到二十世纪才登上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在美国也“晚育”得多。
这构成了美国教育问题的另一个死结:它是美国种族政治的产物,而之所以种族政治是美国的政治传统,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社会冲突被迫以碎片的、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
柯林斯对此有很独到的见解。在欧洲国家,现代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很大的国家官僚系统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全国的政治、商业、文化精英是高度重合的,基于大资本垄断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但是在美国,从19世纪开始,虽然呈现出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工人比例上升,工业的大资本垄断程度上升的趋势,但这些趋势没有在20世纪一直继续下去。这意味着,到了20世纪,已经成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在拥有一定的全国性的大垄断资本和一定数量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大量中小规模的地方商业精英,很多地方维持着非常“本地”的生活。
这种局面源于美国土地广袤、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使得全国性大资本寡头竞争的同时,仍为地方经济精英留下了空间;而早期的政治和商业博弈中,商业力量压制了政治力量,美国的中央政府难以足够强势——地方精英网络庞大,州权较大,地方自治力量强大;这种“去中心化”,在很多人看来是美国社会繁荣的保证。而这也意味着中央-地方的矛盾和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同时存在。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社会的纵向分层冲突——阶级冲突、种族冲突,被中央-地方的冲突横向切开、切碎了。本来,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交织,已经让阶级问题的动员力量有所弱化,加上地方与中央的“去中心化vs中心化”矛盾,各类问题就被导向了更多的出口。比如,处理族群斗争而形成的进步教育理念是很好的,但是为了在多元庞大的国家中维持全国层面文化通货的“流通领域”,他们要引入大量的积分、考评制度,这样教育一定会成为官僚化的,更加注重文凭的一条流水线,痛恨官僚主义的地方精英和普通人已经对这种建制力量极其不耐烦。但如果不这样做,指望地方精英改善不平等问题又太过困难,1957年因招收黑人而需要联邦政府派兵进入小石城的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种难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