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影片《涉嫌之人》剧情老套,背后法理却并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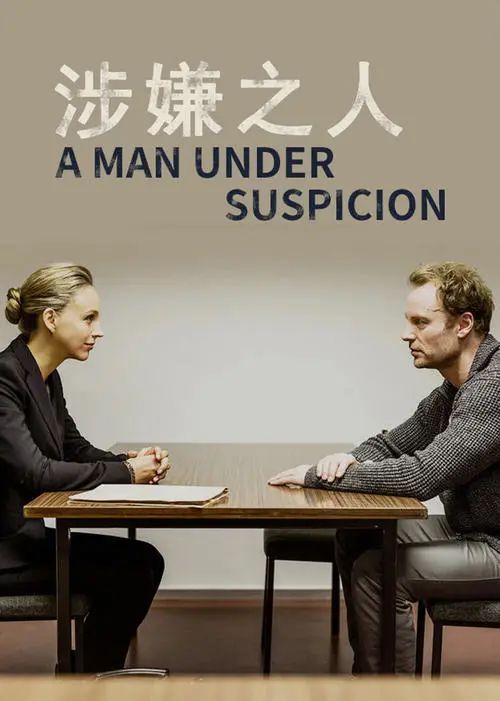
《涉嫌之人》男主托马斯是建筑设计师,妻子安雅美丽温柔,却在庆生宴后离奇失踪。托马斯是报警之人,也是最后和妻子在一起的人,自然被警方认定有犯罪嫌疑。
而恰在此时,康妮自称是安雅好友,主动证明托马斯与安雅于庆生当日爆发争吵,托马斯疑似出轨。
于是,貌似犯罪动机被发现,犯罪时空具备,托马斯嫌疑加重。于是,托马斯找到著名律师拉维妮娅帮助。影片开始展现法庭剧场的精彩博弈。
拉维妮娅是非常优秀的刑辩律师,与托马斯系旧识,案件又存在尸体未现的硬伤,不充分的证据体系被辩驳得体无完肤,庭审即将落幕,托马斯脱罪在即。
常看影视剧都会明白,越是铺陈得水到渠成,越是悬念翻转之时,这是影视剧和现实生活最大的不同。
胜利在望之际,律师和托马斯程序性会见,托马斯一个试探问话直接导致功败垂成。“找到尸体”、“一事不再理”,拉维妮娅是专业法律人,如何不知潜台词。于是,回看材料,发现问题,疑惧惊讶,直至当庭反戈。
于是,优秀美丽也感性的律师违背了著名的法谚“当事人不应兼做法官”,而这也难免让人想起争论不休的话题,“律师可否揭露人渣”?
究竟是什么让剧情急转直下,让精于算计的托马斯惴惴不安?也让专业的法律人出离职业伦理?违背“当事人不能兼做法官”的法则?
法律影片背后往往隐含需争议权衡的法律原则,本片背后的争议原则是“一事不再理”,这是在德国处于宪法位阶的重要法律原则。
“一事不再理”是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判决既判力的重要原则,宪法基础在于;人性尊严、行使自由权、法安定性、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
追本溯源,“一事不再理”源于罗马法之“诉权消耗”理论,旨在以判决稳定性维护法的安定性,衍生的是诉讼系属效力的形式确定力和判决既判的实体确定力。毕竟,一旦司法判决充满不确定性,法的安定性就不复存在,而司法公信力自然很难建立。西方谚语有云“诉讼应有结果,乃是共同的福祉”。
现代意义的刑事诉讼旨在发现真相和人权保障平衡,相关原则、制度无不围绕于此。
“一事不再理”原则侧重人权保障,所以托马斯处心积虑,不惜让自己经历诉讼,只为证据不足无罪判决后,以“一事不再理”寻得永久稳定。
托马斯的脱罪计划垒砖砌墙,确有建筑师精细设计的痕迹。
但也让人不免感慨,如果“一事不再理”被如此利用,成为实现实质正义的障碍,其程序正义的意义是否该打折扣呢?
必须看到,“一事不再理”诉讼价值不可忽视,它的价值在于禁止国家在某一事项上的权利反复施用。
但是,“一事不再理”也是双刃剑,用之得当维护判决稳定性,保障当事人避免反复追诉,也反促侦查和检察侦控能力双双提高;用之不当,也妨碍真相发现,放纵犯罪,影响实质正义实现。所以,像很多其他原则一样,“一事不再理”也存在诸多适用例外。
影片《破绽》的主题在于证据,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证据发现不能,任何努力都是徒劳。但是影片结尾处,真正将霍普金斯绳之以法的,除了枪支、子弹证据谜题的破解,也包括“禁止双重危险”的例外法则。
“禁止双重危险”是美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和德国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应。虽然“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侧重“危险”,关注“危险”附着,而“一事不再理”强调法律安定性,以判决生效为前提。
但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二者核心都是保护被告人不因同一犯罪或者同一事实而重复遭到追诉、审判及处罚,差别并不明显。
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解释上,正当法律程序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是以正当法律程序导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阐释了“禁止双重危险”的具体规则:经判决宣告无罪者不因同一犯罪再被起诉;已被判定有罪者不因同一犯罪再被起诉;不因同一犯罪而遭致重复处罚。
但是,司法原则明定确实,犯罪事实纷繁复杂,准确适用还颇多周折。对同一犯罪、双重危险如何理解,涉及诉讼客体、单一性、同一性等理论,学术上存在各种学说,兼之各国诉讼制度差异,诉因制度、罪数等疑难问题都会影响“双重”、“一事”的标的确定,实务中争议很大。有的案件经多次上诉,经最终判决后才形成原则适用的例外。影片《破绽》的编剧就是借助例外,制造了结尾处的再度悬念和精彩反转。
《破绽》中霍普金斯无罪开释,一颗子弹“解决”两个人,得意之外,又致妻子于死地。致使他如此得意的,除了证据的隐蔽,也有“禁止双重危险”的庇护。
在他的推理中,即使铤而走险致妻子于死地,即使年轻的检察官拿到子弹、找到枪支、成功比对、证据成链,一切也都无所谓,受害者只能在坟墓中哭泣。
因为,只要有“禁止双重危险”,年轻的检察官又能如何?
但是,霍普金斯忘记了,
“为自己辩护的被告,其人也愚”
。他虽然老谋深算,毕竟不懂“禁止双重危险”还有例外。
而例外之一就是
犯罪未完成的例外
,
即首次起诉时,较严重犯罪尚未完成,检察官可以在严重的犯罪完成时再行起诉。此时,形成的就是新事实、新指控、新审判,不属于双重危险。
这一原则在1912年Diaz诉美国一案的判例中就已经涉及。霍普金斯对法律的理解一知半解,年轻检察官当场解析:
她还活着的时候,你的行为是谋杀未遂,第一次庭审的危险因此而形成;但是你让她最终死亡,这是蓄意杀人,新的犯罪行为就此完成,新的证据因死亡而获取,再启的审判是新的审判,并非双重危险。
至此,冷酷无情的霍普金斯,伴随着妻子的死亡全盘皆输。
无论《涉嫌之人》还是《破绽》,我们都确切的知道真凶,也知道凶手的罪刑,所以无论是德国的“一事不再理”,还是美国的“禁止双重危险”,我们都可以直观感受原则适用不当可能衍生的后果,也感受以例外调适平衡的必要。
正如德国教授罗克信所说:只有将法安定性与追求诉讼公正二者之间加以权衡,始能维护法和平性。当事后发现的新事实已经对已生效的判决之公平性产生了无法容忍的显然错误时,则判决确定效力就应该止步。
所以,如何正确维护判决既判力,维护判决公正性,实现法安定性和诉讼公正之间的平衡,是司法制度设置调整的内容。
因此我们看到,在二战后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制度吸收引进英美法概念的基础上,德国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突破了传统上既判力理论,更为保障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