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药企经常背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做销售服务的企业,经常被倒票、回扣等等困扰。
广东药企的事件将行业的关注点转向药业的财税问题,从最初的福建到现在的大面积推广两票制,再加上营改增实施,各地飞检不断,有人预测,随着政策收缩,会有很多人退出。事实上就是如此,从以前私账之间的往来,到现在全部公对公进行,从业务一线的倒腾发票到现在提到买票就皱眉,不是票紧就是点高,甚至很多企业已经不再接受那些买来的各种油票和车票。票就是钱,这是真实写照。
媒体曝光的这些内容,在很多人看来,不足以算作多么值得关注的新闻。真的需要关注的,税务检查,这才是直击要害的。
从曝光的内容看,高开、购票、回流、利益输送,这些关键词,这个似乎不光是医药行业,大多数的非垄断行业的销售应该都存在这个问题。麻烦的是40%这个词,不由得多想一下,这个比例会不会引起更多的猜想。比如消费者在医院完成消费,心里可能产生一个概念,40%是被医疗机构和医生拿掉了,医生或许也有个平衡标准,测算费用分配的合理性。也会有企业叫苦,哪有那么多利润供分配?当然,也有一些独家的中成药,何止这些?
这些问题摆出来,又在侧面敲警钟,该怎么办?
合规,不是表面的公对公就完事儿,这可是系统工程,顽疾难改。首先,很多观点认为药价是层层加码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造成虚高,减掉中间环节就斩断了利益链。本人也是普通消费者,不止一次的实际体验,这根本没解决价格问题。两票制后,很多转为工业高开,财务成本增加,给工业带来很大的挑战。
有人问为什么要高开,最终源头在哪里?医院中标价,没有中标价,没有底价与中标价格的差,哪来高开?
回到原始话题上,合规的问题。不论是违背GSP要求还是虚入发票套现和平账,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目标的达成。首先,任何企业运营都有成本,大多数工业的利润已经微薄,在经历了新版GMP改造的投入后,况且还面临一致性评价的巨额花费。商业,这个所谓的中间环节,也没有想象的那个暴利,尤其是那些做调拨流通的,净利润率也就不到2个点。在零售环节,那些连锁和单体以及诊所,表面上看起来都在做高毛产品,实际上,除去店面和人工成本,还能剩下几何?最后的矛头指向了临床,指向代理商,两票制的革命对象。有好品种的代理商,前几年过的很风光,从整个分配链条上看,大多数代理商的所得相比流通和工业都要多。当现在面临各路检查,尤其是财务风险的时候,大家都迫切需要向合规靠拢,解决安全问题。
如何解决合规,开个咨询公司?这都成了笑话。大家都偏向于那个比较火热的名词,CSO,合同销售组织。国内大家熟知的泰凌、亿腾和康哲这些,临床做的比较成功的公司,已经成为CSO的学习楷模和代表。
本人认为,解决合规,很多代理商提出向CSO转化,只是为了让发票的后面有真实的业务发生,由底价高开返费用到佣金制转化。而CSO不应该单单是帮代理商实现合规,为了在合理的掩盖下进行利益输送,而是真实的为工业和终端提供服务嫁接,目的是通过营销服务实现销售最大化。药审制度改革,医保支付和临床路径,以及一致性评价等推动,作为提供销售服务的代理商,需要具备整合资源和要素的能力,充实自己的专家库资源,能够完成迎合临床需求的学术服务,从而形成工业、配送后的专职营销服务商(代理商CSO)。
行业巨变的结果,最终是要规范落地,务实合法。药品的竞争终究是要回归到品质的比拼和专业服务的较量。
随着经济和法制水平的提高,核心环节和关键人物的需求逐步转化,单纯的利益驱动逐步缩小。如果按照专业分工做一个流程的话,那就应该是工业到终端,中间以最优成本进行配送(医药公司或者快递公司),而营销服务则应该是第三方完成,包括市场调研、专家资源、临床学术培训、患者教育,零售渠道的服务管理、消费者传播等等。也就是,做生产的就做生产,保证品质,做配送的就做配送,保证时效,做推广的就做推广,保证营销目标的达成。拯救,有点言重了,实际上,很简单,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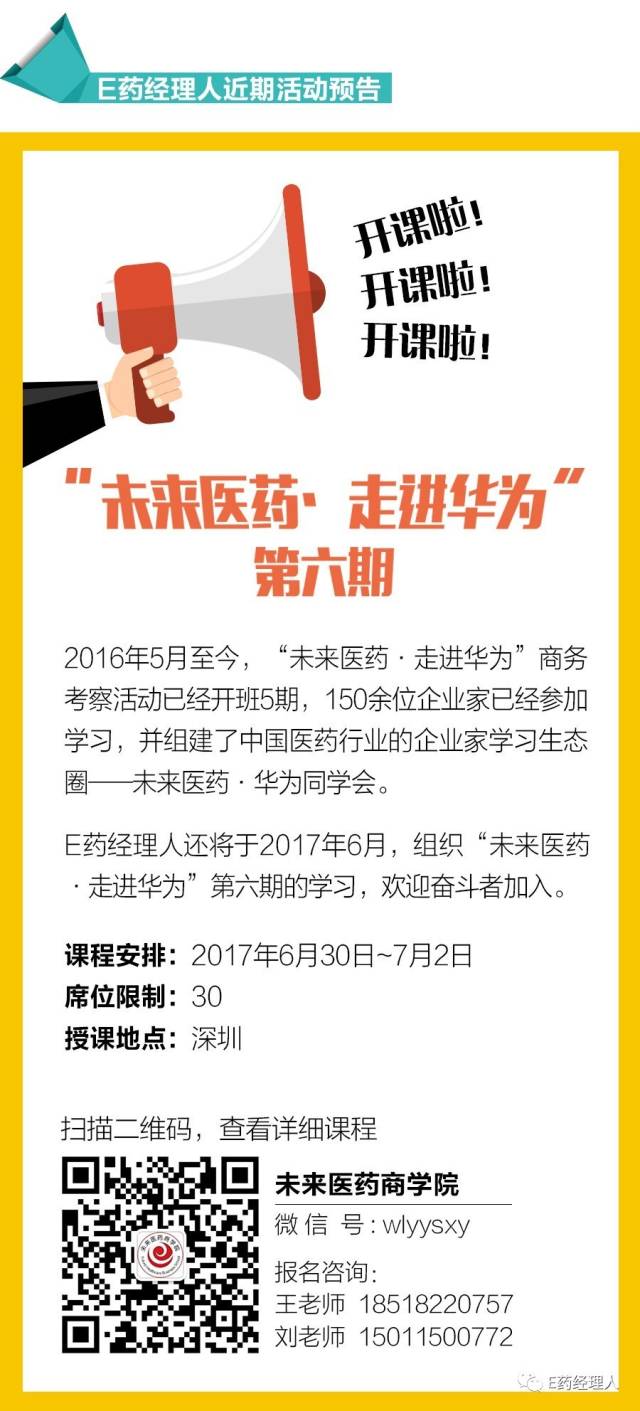
本文版权属于E药脸谱网(www.y-l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