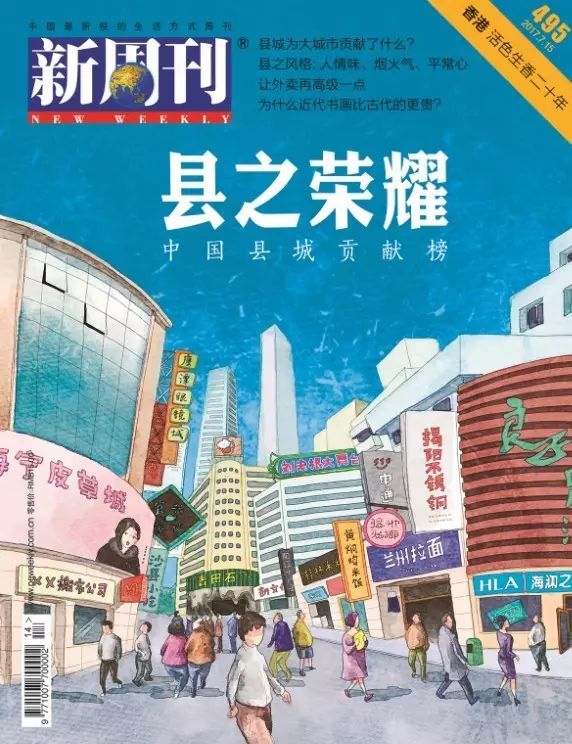许知远在单向空间。图/刘浚
多年前兴之所至创办单向街图书馆的许知远不会想到,他会像现在这样真正迈入商业世界。在无数轮怀疑与自我纠结后,他逐渐厌倦外界赋予他“经商的知识分子”这一充满矛盾感的标签。“我是个不靠谱的作家,也是个勉强的创业者。”对许知远而言,经营与写作更像互相逃避的方式。
文/罗屿
近一个月,许知远两次梦到了谭嗣同。在梦里,他和对方一遍遍讨论袁世凯带兵包围慈禧的方法与可行性。两人争论不断,直到许知远忽然惊醒。醒来的瞬间,他觉得有点好笑。由于给自己定下的宏大写作计划——用像史景迁一样的动人文字完成一部《梁启超传》,三年来,他一直陷在晚清的某种语境里。
同样是这三年,“文人、作家、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被外界冠以新的身份——创业者。2014年,面临资金困境的单向空间接受挚信资本千万美元投资,正式进入商业化运作。而在资本进驻之前,许知远和另外5位朋友于2005年共同出资,在圆明园一座院落里创建的“单向街图书馆”,即单向空间前身,更多呈现出自然生长的姿态。
许知远甚至在开店之初,并没有规划过它的未来:“我们都刚辞职,无所事事,喝得醉醺醺,纯粹出于一时之兴,决定开设一家书店,每人就出一点点钱,但我们都不会经营,想着过两年钱花完了,它也就死了。”
被许知远称作“偶然”的单向街,从一开始就带着创始人强烈的个人气质。它的店名取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同名著作《单向街》,这个忧郁作家曾是许知远最爱。某种程度而言,单向街不只是书店,更是一种场域与氛围。
从诗人西川的第一场读诗会开始,这里不断有作家、导演、艺术家光顾,举行座谈沙龙。许知远自己也常到这里逃离日常生活的逼仄。“冬日里晒晒太阳,夏天坐在院子里,听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

2014年,单向空间从圆明园搬到了花家地。图/许知远
由于创始人从未把单向街当作生意,以至于在经营两年后许知远他们才发现单向街这个商标在一年前已被他人注册,他们只好无奈地将“单向街”更名为“单向空间”。更严峻的考验是资金问题。从2005年到2014年,这个理想主义者营造的乌托邦几次因租金等问题生计维艰,按照许知远的说法,“总处于破产边缘”。
只是,许知远并没有如自己最初以为的,任其死掉,他想到的方法是,通过不断增加“股东”维持书店运转。他事后曾说,那些危难之时出手相助的,“都是了不起的‘股东’,依靠一种‘放任自流’来管理自己的投资”。
然而,在接受资本投资、不再“以自己的收入供养兴趣”后,许知远本人也必须收起随性,每天面对这个公司的日常经营。这让他出现了短期不适。据说有一段时间,在工作微信群,他一喝高就说自己焦虑。而媒体那时也习惯将许知远塑造成创业之路上充满焦躁与矛盾的知识分子典型。

单向空间爱琴海店。图/豆瓣·单向空间小站
许知远并不否认自己创业之初的无力感。2015年3月,在单向空间与喜马拉雅FM合作推出的音频节目《单读》中,他提到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他说自己和“不得不”生活在美国的米沃什一样,正在“假扮成一个我不是的人”——逼迫自己学习商业,却距离“作家”越来越远。
然而,走过三年,经历无数轮自我纠结后,许知远开始厌倦外界赋予他的“经商的知识分子”这一充满矛盾感的标签。也许是缓慢进行的《梁启超传》让他获得了解脱。在单向空间新驻地——花家地的一幢四层小楼里,许知远在查阅晚清资料时发现,原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流亡通信中充斥着“投资” “回报” “股息” “募款”这些字眼;康梁组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时,同样也会为营收而烦恼。
“从来没有所谓纯粹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复杂让许知远释然。对如今的他而言,经营与写作更像互相逃避的方式。“写作不顺就回来管理公司,搞各种‘变法’,但往往搞得一团糟。”
“有我没用,缺我不行”成了许知远的自我定位,这个当初在投资人面前谈理想、聊情怀、分享缅甸旅行见闻的创始人,会在公司产品讨论会上忽然念一段奇克果(Kierkegaard)的文字:“审美的人追求快乐,然而他是以讲究趣味和优雅的方式来追求的。”他年轻的同事们往往一边听他讲话,一边刷着微信朋友圈。
在鼓励下属时,许知远会引用希腊人的说法——“若不发挥个人能量,是对人尊严的侮辱”;员工们则在谈及“哪个部门工作不饱和”时,投给老板许知远的票数仅次于店里流浪猫。

单向空间花家地店门外的黑板上,写着“新书推荐”。图/界面
许知远同样渴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他只是无法完全相信商业逻辑。
当许知远习惯分裂乃人生常态,以经营与写作互为解脱后,偶尔也会遭遇二者压力的集中爆发。那时他会在朋友圈自嘲,比如发上一张有酒有书的照片并配文:“一旦在夜半的办公室,一股失败的创业者加失败的作家的混合情绪就混在一起涌来,只好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酒鬼。”
然而,自嘲只能短暂缓解焦虑,喜欢接触陌生经验,唯恐自己陷入僵化与重复的他渴望的还有逃离。曾在中国与世界“游荡”多年的许知远说,这两年,他感觉自己被困在了花家地,“简直要发霉生锈”。
这时,一档名为《十三邀》的节目,成了许知远逃离的出口。
2006年年初,许知远和刚刚加入腾讯网担任副总编辑的李伦相识,后者是在央视工作了22年的资深制片人。此后的一天,李伦向许知远提出一个“意外邀请”——由腾讯新闻和单向空间联合推出一档网络人物访谈节目,许知远首次走到屏幕前担任主持。

《十三邀》片花。
作为一档访谈类节目,受访者的选择至关重要。《十三邀》制片人朱凌卿记得,许知远最初开列了一张天马行空的访谈名单,包括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知名导演伍迪·艾伦、相声演员郭德纲,“他还想和村上春树一起跑步,和性感女星莫妮卡·贝鲁奇在意大利小镇散步,到英国威尔士拜访自己崇拜的旅行作家简·莫里斯”。李伦看到这份许氏采访计划后直言:“这不十三不靠么?”
最终与许知远在节目中对谈的是罗振宇、姚晨、二次元团体、冯小刚、叶准、李安、张楚、蔡澜、俞飞鸿、陈嘉映、贾樟柯、金承志、白先勇。有些嘉宾的选择有贴近热点的考量,有些则完全是许知远的随性之举。
比如,在单向空间举行的一次“跟叶准学咏春”活动上,许知远看到耄耋之年的叶问长子,忽然想到年少时读过的武侠,“他脸上写满故事”,许知远忍不住偷拍了一张叶准照片,发给李伦:“我们就做这个。”
不同于其他正襟危坐的访谈节目,《十三邀》明显沿袭了许知远随性的个人气质:这位主持人总是顶着一头乱发,穿人字拖,或是跟冯小刚吞云吐雾,或是和白先勇、蔡澜、陈嘉映把酒言欢。采访李安时,许知远终于换上皮鞋,当被工作人员调侃为何换鞋,他答得坦白:“冷啊!”面对姚晨时,他说的第一句是:“你比我想象的矮啊!”
在茶馆等待俞飞鸿时,他说感觉就像大学时在女生宿舍门口等着约会,终于见到女神,他在酝酿良久后冒出一句:“你真的很好看!”到香港拜访蔡澜时,他们一起吃着火锅,聊人生、女人、文坛风流往事,许知远也三次毫无“眼色”地追问蔡澜:“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采访哲学家陈嘉映时,许知远如同一个一脸求知欲的学生;采访二次元达人时,他则显得茫然无措甚至有些疲倦。

许知远与俞飞鸿对谈。
许知远享受借由节目,和原本并无交集的嘉宾们的“偶遇”,“意外的邂逅会产生奇妙效应,可能连对方都忘掉的记忆,会随着谈话深入慢慢浮现”。他念念不忘拜访白先勇时,对方说宋美龄不仅抱过自己还给过巧克力吃这个小细节;当听到姚晨提到当年混迹于福州小城歌舞团,对生活充满期待却毫无出路,在肯德基打工,喜欢上一个叫托尼的经理,许知远脑中忽然浮现郁达夫笔下那些天生丽质难自弃的福州女子;当听到罗振宇说自己当年分配到北师大,因为傻大黑粗,第一个工作是每天背骨折的于丹上班,许知远忍不住笑了。相对于思想、知识,许知远说自己更着迷于每个生命个体,这些或温暖或浪漫、或离奇或荒诞的人生片段。
罗振宇是《十三邀》的第一个受访嘉宾。录制节目时,许知远正处在创业焦躁期,每天困惑于如何将读者、听众、用户,转化成真正的购买者,而《罗辑思维》在这方面显然特别成功。“我几乎是带着见心灵导师的心情去见罗振宇。”然而,当两人畅谈3个小时后许知远发现,“导师”的很多话,他都不同意。

《十三邀》片花。
罗振宇曾经这样解读过《罗辑思维》:“它不可能帮你求知,但是它缓解了你求知的焦虑感;另外,它给了你谈资,很多老头听了我们节目马上冲到公园跟他一起锻炼的老伙伴抬杠,因为我们给了他全部的歪理邪说和背后的道理。”
许知远不赞同罗振宇把知识过分实用化与工具化:“他让一切变得可用、可理解,而我却相信,世上大多事情不可用、不可理解;他觉得人应当一心往前冲,不应回头,我却觉得留恋过去是人特别幸福的一部分;他说时代不会留给唱挽歌的人,我恰恰是喜欢唱挽歌的人。”
虽然观点各异,许知远仍旧喜欢和罗振宇的这次见面:“他像一个焦虑时代的心理按摩师,做一种精神按摩,我不相信那些东西,但是我理解。”许知远有时也怀疑,罗振宇是否因为参与到这场巨大的商业游戏中,才故意说出一些狠话,强迫自己做出某些实用主义考虑。只是在许知远看来,“我们每个人,不管如何声称自己是时代的冲浪者,其实都是被时代所改变、所塑造”。


许知远与罗振宇的对谈。
单向空间是一家缓慢发展的公司,许知远相信有价值观的生意有其内在生命力。
除了满足许知远个人兴趣,《十三邀》同时也是单向空间媒体业务的另一个尝试。许知远并不否认,由于处在寻找项目的创业盲目期,他希望《十三邀》未来可以给公司带来比较大的广告收益。
在单向空间众多产品中,让他最为纠结的是2014年上线的新媒体平台“微在”。“微在”原型是美国最具娱乐精神的互联网新闻网站 BuzzFeed,通过类似“31 只喵星人看到了你不会相信的事情”“你不应成为的13种Facebook情侣”这样的文章标题,可以看出 BuzzFeed的内容偏好。
2014年以前,许知远从没想过BuzzFeed会和自己搭上关系,它的内容与审美不仅不是他喜欢的,甚至是反驳的对象。于是,当合伙人提出借鉴BuzzFeed时,他不置可否。“他们相信这会是对既有的单向空间的一个有力补充,它会抓住更年轻一代。我不太信任自己的判断力,觉得自己正在被时代抛弃,周围年轻人的谈话、喜怒,我越来越难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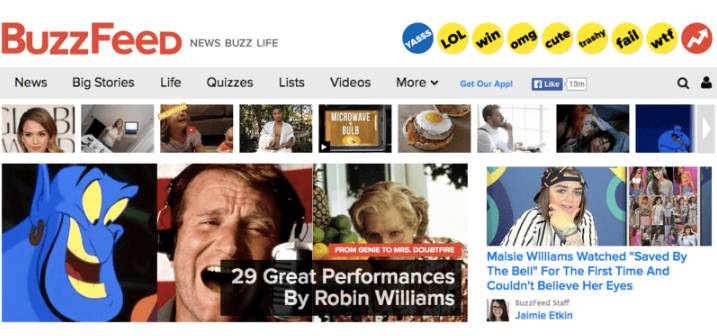
BuzzFeed网站首页。图/36氪
许知远索性“逃”到美国,再回来时,他依旧躲着年轻的“微在”团队:“我很少与他们交流,很是担心,因为一句蠢话,他们就在心里嘲笑我是个陈年旧物。”然而,许知远也感到了自己的变化。
在写于2014年11月的一篇《非典型创业日志》中,他提到,最初他觉得“微在”的内容浅薄、琐碎,但他慢慢发现,也许对年轻一代而言,“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一个萌猫的表情与乌克兰局势、星巴克的新款咖啡、Line上的新表情符号同样重要,他们天然地怀疑权威、强调自主性”。许知远很难说清,这是否是一种自我说服,毕竟那个他熟悉的大写的历史与世界,早已转化成一个更私人化、亲密化、简单化的“小时代”。
音频节目《单读》,一度成为许知远逃离“小时代”的避风港。录节目时,他会踩着人字拖、夹着要读的书、拿着咖啡或酒走进《单读》录音间——公司二楼库房。
《单读》每一期话题几乎都是许知远日常生活的映射:和罗振宇对谈后,他在《单读》中继续创业这个“无聊但重要的话题”;去美国前,他讲硅谷百年;“偷懒”时,他会安静地为听众读上十分钟《总统先生,一路走好!》。偶尔,他会在《单读》里插播一条“非常重要的一点都不无聊的广告”,推荐自家手账或日历。许知远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人生活在真空里”。

陈列在单向空间里的《单读》。图/豆瓣·单向空间小站
从《单读》的更新频率可以看出,年过四十的许知远依旧有着“过于任性”的一面,“下午想起来,就录一下,可能三四天都没兴趣,就不录了”。当听到罗振宇坚持每天早上6点推送语音,像时钟一样精准,许知远感慨:“那真是一种巨大的折磨,我有时不免同情他。”
在多数人眼里,许知远一直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他也曾频繁地见VC参加饭局,直到自己失去耐心;他也曾以创始人身份参加商业论坛,只是当别人谈产品用户时,他大谈陈独秀与梁启超;当别人感慨创业的血雨腥风时,他表示自己明年要正儿八经地学学日语。
“你看,那束光打在竹叶上多漂亮。”许知远忽然指着远处对记者说。单向空间花家地店,总让许知远想到当年圆明园的单向街图书馆,它们有同样布满爬山虎的灰墙、狭窄的玻璃窗以及草地院落。

单向空间花家地店。图/豆瓣·单行空间小站
如今,许知远仍会坐在店里看人来人往,畅想在中国的每个小县城都有一两家特别美好的小书店,“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在里面听着巴赫、莫扎特,随手翻翻海明威、王小波”。
有一天,许知远在店里遇到了一对夫妻,10年前他们在单向街相识,如今已结婚生子。这个爱情故事让许知远觉得特别美好。“我们没有那么大野心,只想成为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空间,至少可以给一小群人某种慰藉。”在单向空间内部有个口号:寿命超过BAT。许知远相信始终有一群人愿意跟随有价值观的生意,他喜欢特拉克尔的那句话:“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方向更重要。”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95期
直接戳图片即可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