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互联网上《方方日记》的爆红,一个古老而陌生的词汇——“极左”,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每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对方方批评抨击时,方方及其拥趸便会怒斥道,“极左!”。而对这突如其来的“帽子”感到一头雾水的年轻人,则会惯性地反击,“你才是极左!”,当然,还有躺着也中枪的左圈人士,他们无法否认自身的政治立场,于是只能不无戏谑地称:“我喜欢方方,因为她随时保证了我的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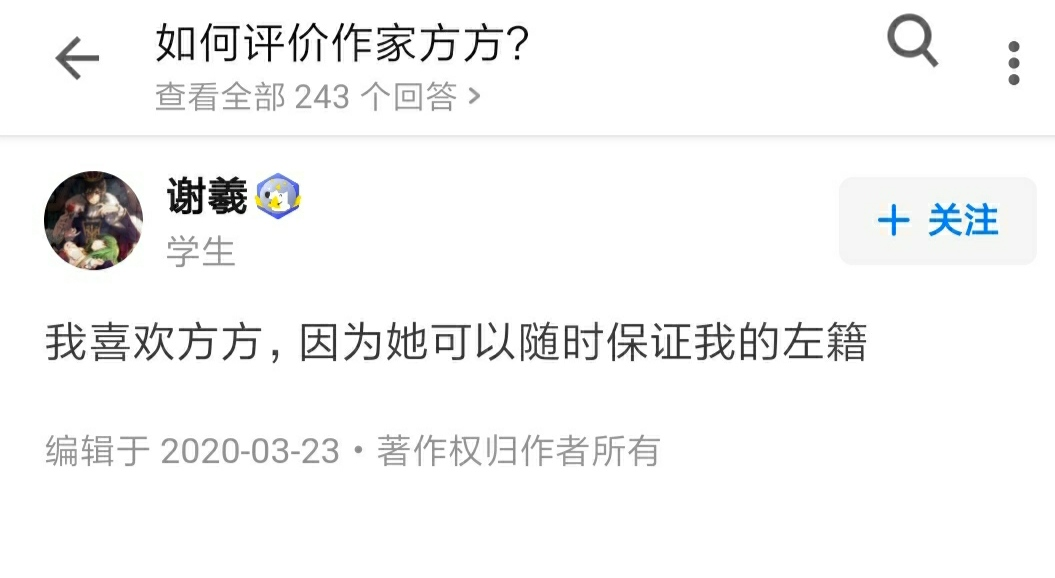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说“极左”时,我们在说什么?
对方方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关于凶神恶煞的想象,是那些对她疯狂进攻、罗织罪名,撰写大字报的人。不错,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假如事实能够证明,他们的指控都毫无根据,并对方方老师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失,那么这种批判的确有存在的道理。
可问题在于,如果要批判的只是一种极端思想和行为——扣帽子、扒黑历史、上纲上线、人身攻击……为什么偏偏要扯上“左”呢?是因为那些人善于使用左派语言,让她想起了当年的红卫兵?可是在骂她的人中也有很多人并不知“左”为何物,他们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在政治光谱中说得上右了,为什么也被归为“极左”?而且这种极端思想和行为在方方的维护者中也并不少见,那么他们是“极右”吗?说起来,短片《前进,达瓦里希》比《方方日记》所受到的攻击还要恶毒百倍,为什么从来只有“极左”和“红卫兵”成为愚昧与邪恶的代名词,而鲜有人批评这些“极右”和“白卫兵”?
如果说,将一切凶神恶煞命名为“极左”只是一种历史创伤所造就的无意识,那么,当方方和她的朋友们开始揪住“极左”不放,并大谈社会主义历史的黑白对错,将一种决绝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时,我们将终于明白——
虽然他们批的是“极左”,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批“左”。
毕竟有位朋友声称,不要以为你没干坏事儿就不是“极左”,只要你胆敢对新中国改开前的思考和看法与他们不同,只要你爱国爱到“友邦惊诧”,甚至破坏“中美亲善”的话,你就很有可能成为极左。
这样一来,一个有关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问题就被悄然置换成了道德问题。它基本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你批评方方日记,你就是无视武汉人的悲惨遭遇,就是没良心;因为他们口中的"红卫兵“是最没有良心的,而你还恰好分享着左派观点,所以钦定了,你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极左”。
尽管这个逻辑的每个环节都不乏漏洞,但它成功地将“极”加诸于所有理性批评者之上,又用“极左”给社会各界左派中派扣上了帽子,于是也成功让方方最终惹怒了所有(对日记持保留意见的)人,许多批评者觉得自己既不“极”也不“左”,而“左派”也并不认为自己十恶不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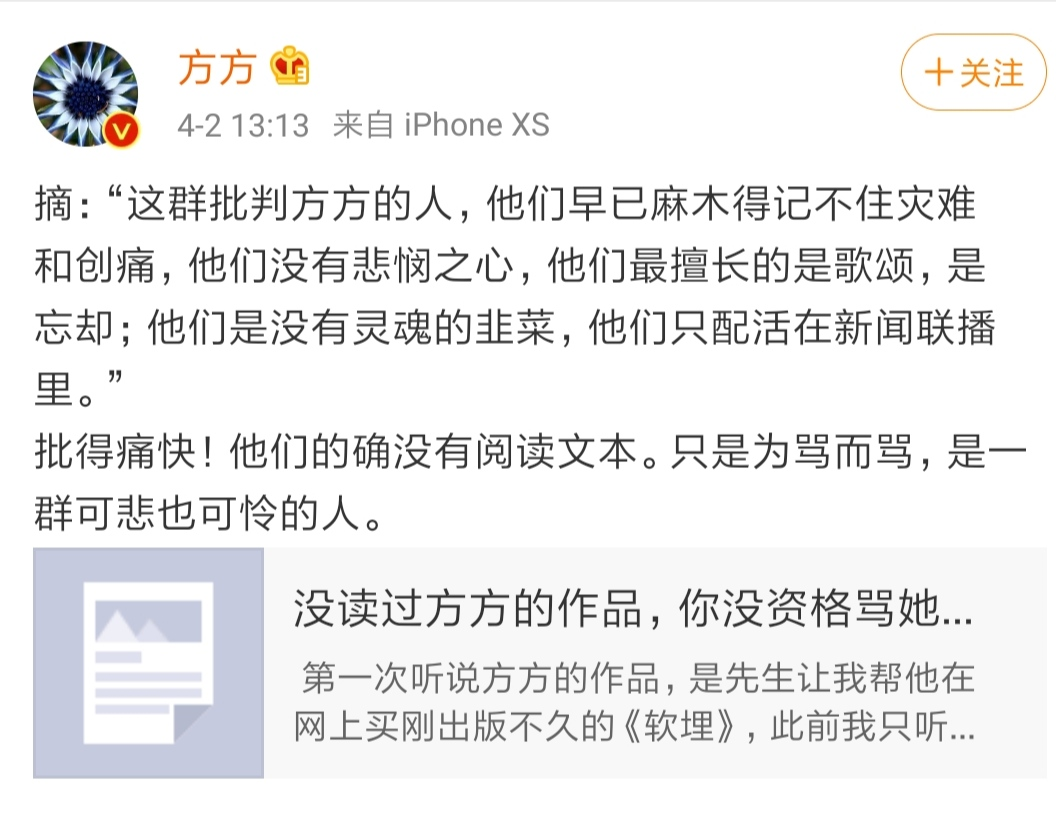
那么到这里,我们问题的答案,也就逐渐明晰起来——
当我们说“极左”时,我们在说我们身处的后冷战时代,在说一种站在冷战胜利者的角度来审判失败者的逻辑。
胜利者将洗刷自己的罪恶,而加倍审判失败者的罪恶。于是在他们(资本主义/右翼/新自由主义)的描述中,切·格瓦拉与毛泽东会成为“杀人狂魔”和“权欲熏心的专制主义者”,牺牲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英雄都是苏联高官拿枪毙威胁才去的,文革是比屠杀印第安人更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饥荒说你死了几千万就死了几千万,而一切悲剧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你有原罪——你们信仰的主义根本上是反人性的——你们必然走向恶魔一般的“极左”。
方方们向年轻人声称这样一种逻辑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但其实是以一种道德绑架的方式阻止了任何其他的思考路径。换言之,除了无条件地认同他们之外,你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能够证明自己“有良心”。
那么想要“有良心”该怎么做?他们倒是慷慨地明示了——把你脑子里那些“左的”毒素清理出去,再装进一点新东西。那装进去的新东西是什么?“启蒙”与“良知”、自由市场,人文主义,西式人权与民主等等普世价值……非常巧,符合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流价值,也与颜色革命的宣传策略颇为相似。
而这种道德绑架往往是建立在人民的名义之上。当代互联网舆论场上的许多骂战,诸如五毛VS美分、自干五VS公知、小粉红VS恨国党……尽管其中不无夹杂着有关民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的叙述,尽管有关“革命”的话语已被悄然置换为“民族复兴”,但总体来说其根本分歧都与90年代学术界“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歧类似,那就是“谁能代表民间”,也即争夺人民的代言权的问题。在如今已日趋简化的讨论中,一方常常讲述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道路改善了多少人的生活,而另一方则更倾向于关注有多少个体被侮辱和损害着。前者讲数据,后者讲故事。
显然,数据是冰冷的,而故事鲜活。因而人们在小说、在电影、在人物报道、在《方方日记》中共情于那些小人物的离合悲欢,在为之感动落泪的同时,一种“悲情叙事”也成功以渲染苦难的方式确认了敌手的邪恶,尽管这故事不一定真实(并非全部不真实)、推论不一定合理(并非绝对不合理),尽管这个敌手可以被替换、被改写为任何个人与组织。而这,就是所谓的直觉与常识。
我们以为直觉都发乎内心,常识都从来如此,但其实,直觉可以被操纵,常识也可以被塑造。这就是意识形态,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并不会轻易自我暴露,它让你感到天然合理,无需怀疑。而真相有时却恰恰是反常识的,比如小六子真的只吃了一碗粉,比如那个被称作张麻子的人,其实叫张牧之,他的脸上也并没有麻子。

当然,尽管自由派总是擅长为人民代言,所谓“不为权贵唱赞歌(未必不为西方权贵唱),只为苍生说人话(未必也为西方百姓说)”,但他们其实并不爱谈“人民”二字,因为“人民”往往只出现于共产国家的国名之上,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革命意味的语词。他们比较爱谈“底层”、谈“弱势群体”,并且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要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不要爱什么空洞无物的“人民”。作为对前三十年工农兵形象“高大全”的一种反弹,他们托举出“个人”,爱讲人性,但往往却只是人性的弱点与暗面。
八十年代以后,“伟大的人民”在很多文艺家们的笔下忽而跌落为“弱小的人民”。文艺家们在无数作品里讲述人的脆弱、无助、欲望与挣扎,即使反抗,也是相当凄惨而注定失败的反抗。他们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处于弱势,因而他们指望不了自己,而只能指望被发现、被发声、被拯救。人们喜爱这种呈现,不仅是出于他们善良的本性、对他人苦难的共情,同时也因为这种俯瞰视角将他们固定在一个观看者、拯救者的位置上。
那么在八九十年代被精英知识分子抛弃的“人民叙事”,就真的仅仅是以歌功颂德来掩盖现实黑暗、淹没小民尊严,是一种洗脑、一种谎言吗?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人民”不仅指称着被剥夺的个体、现实中的多数,而同时意味着已然觉醒的、具有阶级意识的思想者、行动者,他们不仅不需要被拯救,而且当他们联合起来,历史会因之而改变。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劳动者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并不是一种刻意拔高,而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揭示,虽然它听起来那么的“反常识”,虽然在公知痛批的文革年代里,它却是人所尽知的常识。
幸而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再次确证了,这绝不是一句空谈,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再现。我们有无数勤劳、善良、勇敢的人民,最可爱的劳动者,他们是“不计生死、无论报酬”、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是千里迢迢捐送蔬菜的农民、是十天创造出“火神山奇迹”的建筑工人、是在基层日夜奔波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1
面对他们,知识分子凭什么说自己代表了人类的良心?
“人民叙事”的衰落也提醒着人们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失败。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权延续和经济体制变化所带来的合法性缺失,也有来自胜利者一方对历史的涂抹、对是非的混淆,还有那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蛀虫和屡屡给敌人递刀子的极端主义者。因而戴锦华教授有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失败。
当你不能有效传播自己的理论思想,同时也无法用隐蔽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时,你就会失去人民的代言权,因为相信你并不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人们更情愿相信那些为他们写故事的人、为他们流泪的人,尽管那些人的理想王国远在大洋彼岸,尽管他们所许诺的“现代文明”同时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掠夺。
而一旦获得人民的代言权,自由派公知们就成功加冕为良知的化身,并且垄断“民主”与“自由”的解释权。可是当他们又不断露出自己的“屁股”,为他们理想国度的“民主”——资产阶级代议制和“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摇旗呐喊时,人们也将渐次醒悟过来——他们所代表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他们并不能代表人民,而只是伪装成人民的代言人。
但这种伪装,仅仅只能从道德品质的角度来评判吗?自由派、乃至“河殇派”的思想曾经在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中流行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并且至今仍充斥于我们的学术界、文艺界、各类媒体、网络空间。他们都是敌人吗?难道知识分子就注定“反动”?
如果我们坚持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那么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有过许多人民的知识分子,或者用葛兰西的说法——“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将知识奉献于人民的事业;但也有落后于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缺少广博的学识、美好的品质,可他们常常将自我超脱于人民之上,一不小心就成了反动阶级的帮闲。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矛盾,是因为知识分子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对自我实现有着极高要求,他们大多非常理想主义,也具有社会责任感,但另一方面,由于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际,他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要么根本不承认有阶级这回事,要么实际与剥削阶级站在一起,却声称自己代表人民,而只有那些经过深刻自我改造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
这对我们普通来说人也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启示:正是自我认同的需求促使我们追求正义、追求美善,成为有尊严的理想自我,但有个重要的前提是——求真。只有确认了你的追求是真正的而非虚假的正义,它有益于历史进步,有益于多数人也就是无产者的利益,这份认同才算发挥了它的作用。
而真理往往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如果仅仅停留于自我认同而固步自封,忽略实际条件的变化,无视具体的历史进程,那么就容易走向正义的反面,自我认同沦为一种抱残守缺的自恋。
这也是为什么,在沉思录18年的一次读者调查中,大量留言里的自述会让我们看到,不少年轻人都由最初懵懂无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变为追求个性与反叛的自由主义者,又在接触更大的世界后转向爱国主义,而最终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正生动展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与其说不同政治派别的年轻人们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如说大家只是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而处于不同的认知阶段。用方方老师的话来说,这叫“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如果信奉某种观念、追求某种理想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那么当你的追求不再合乎时代需要、甚至阻碍历史进程时,为了维护那种完美的自恋想象,人就可能开始说谎、扣帽子、非黑即白、人身攻击,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但如果你爱真理胜过那一点自尊心,也并不指望一劳永逸地获得真理,而是不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前进,那么不用担心,大家早晚会在终点相遇。
当然,也许并没有什么终点可言。正如一位最坚定的革命者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所说——
“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的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将来的一代应该比现在的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接续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成果。地球上的人类的条件,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连列宁也一定显得不高明了。”2
如何偿还历史的债务,如何继承历史的遗产,如何将火种从历史的束缚中救出,如何拿回“民主”与“自由”的旗帜,如何让新的火焰再次燎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一起上下求索。
1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Farooque Chowdhury《在毛泽东诞辰重申毛泽东》通吃岛岛主译
注:本文主要观点均启发自戴锦华老师的讲座《历史与人民的记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上b站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