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
变化
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李蓉蓉 李晓丹 段萌琦
作者简介:
[1]
李蓉蓉,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李晓丹,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3]段萌琦,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讲师。
文章来源:
《公共管理评论》2023年第2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
2023/4/24
版块分类:
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1497)
PDF全文:
点击链接<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可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摘要: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民众的政治态度极易发生变化。本文借助扎根理论的分析发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了积极与消极两种方向的变化,朝向积极方向的政治态度变化更多体现于政治认知中的肯定性信息增加,朝向消极方向的政治态度变化则更多聚集在政治情感上;促使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因素有利益关切、政府防控行为、媒体推动、参照效应、制度因素和政治价值观,这些因素构成了“多因素互嵌说”;由于六种因素在政治态度变化中的相互作用与催化形式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态度变化路径;其中参照效应在两种政治态度的分化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联结起所有元素,形成了所谓的“参照逻辑”。
关键词: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参照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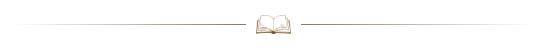
一、 引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危机的同时,也对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一系列冲击事关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休戚相关;与此相伴的是,在重大灾难面前,民众的政治心理极其脆弱与敏感,政治认知极易发生混乱,政治情绪极易波动,政治行为也可能失控。这两方面的问题均可直接投射在民众的政治态度上,因为政治态度是政治现象的“晴雨表”。因此,关注并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变化、发生哪些变化以及哪些因素引发了这些变化这三个紧密关联的问题,对于学界揭示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可为相关政府部门调节政治态度提供视角与路径。
中外学者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多是基于常态下的分析,对于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研究相对薄弱,可是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等非常态事件时有发生,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Beck, 1998)所说:“现代化所持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此,关切并研究非常态下的政治心理现象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其中,政治态度由于易受到特定事件与情境的影响(Shi, 2015),又是民众最为日常的政治表达,在诸多政治心理现象中格外突出。由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时间持久,极易将处于全球化中的一国乃至世界其他各国的政府行为、民众反响、舆论媒体等放置在“放大镜”之下,彼此比较,相互振荡,强烈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加速改造人们的政治态度。此时,对于政治态度的凝视,更能挖掘出常态下少有的特点,也更能快速捕捉到常态下鲜为人知的影响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实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深化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文章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将分五个部分剖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变化的状况:一是就政治态度的内涵、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界定,同时与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信任和政治支持等相近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明晰概念边界,建立论证根基;二是对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以便发现理论上的不足与探讨空间;三是通过介绍本文研究策略,包括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说明本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四是借助研究策略,推出研究发现,试图回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变化路径这三个问题;五是将研究发现与已有理论进行对比,凸显研究贡献并延伸理论运用。

二、 政治态度及其变化
所谓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s)是指一国民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政治系统所形成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且复杂交错的一系列倾向性评价。这一界定并不是学界对于政治态度相对宽泛的定义,而是聚焦于民众对于一国政治系统的倾向性评价。进一步说,倾向性就是主体对于客体所形成的内在的准备姿态,这种准备性姿态既包含心理上的准备,也包含行为上的准备(Allport, 1935),由此推演出所谓的政治态度的三成分说,即政治态度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构成,体现了心理准备与行为准备的双重意涵。同时,这一界定也表明了政治态度的时间性、内隐性、相对稳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从时间角度而言,尽管政治态度的生成源于儿童时期的学习,但这并不代表其是一成不变的。在政治世界中,由于政治环境变化较大,重大公共事件频发,因此政治态度的时空效应强于一般的态度,也就是说政治态度更易受到一定时期一国的政治系统、社会环境变迁乃至重大公共事件的影响。正因如此,从长时段来看,政治态度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其稳定性会产生波动,政治态度的稳定性一旦产生波动,其变化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同时,政治态度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心理现象(李蓉蓉和段萌琦,2019),内隐性是其基本属性,即政治态度往往是个体政治表态与政治行为的准备状态,尽管与外在政治行为关系密切,但是其毕竟是行为发生前的政治心理活动。除此之外,由于政治系统的复杂性,政治价值、不同层级的政治机构、政治人物、政治制度与政策乃至政治事件均是态度对象,由此可形成不同客体的态度系统。再加之,政治态度构成成分具有多元特征,即政治态度由政治认知(political cognition)、政治情感(political affection)与政治行为倾向(political behavior tendency)构成(Allport, 1935;Edwards, 1957;Rokeach, 1968),愈加凸显了政治态度的复杂性。
政治态度不等同于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信任乃至政治支持或者任何一种类型学层面的政治态度[1],但是它与这些政治心理与行为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具体来说,政治价值观(political value)是公民对政治系统或政治客体进行评价的标准和依据,而非单纯的评价,因此,它与政治态度内含的评价是不同的。但是,政治价值观是“政治领域中特定态度、偏好与评价的基础”,是个体形成政治态度的基础性观念(郑建君和赵东东,2021)。同样地,意识形态(ideology)也不能等同于政治态度,且不说意识形态究竟是统治阶级的专属还是一般民众拥有的一种信念体系本身就存在分歧(俞吾金,1993;马得勇和王丽娜,2015),即使意识形态可被看作民众的信念体系,也只能说明意识形态是民众持有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而政治态度只是民众对于政治系统形成的具有倾向性的评价体系,它或许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基础性阶段,但远没有达到信念和政治立场的程度。尽管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作为政治系统的反馈存在(孟天广,2022),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态度,却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政治态度。具体到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其更多地是指一种行为而非潜在的准备状态,因此也很难将其看作一种具有内隐性的政治态度。
一般而言,已习得的政治态度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重大事件的刺激和巨大的环境变化,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稳定周期相对较长。但是,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刺激下,外部环境短期内急剧变化,深受环境影响的政治态度极有可能与环境发生共振,产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政治态度内部成分的松动上,进而在强度上发生变化,最后决定了政治态度的变化方向,呈现出两种类型方向上的变化。一种类型的变化方向是积极性政治态度变化(change in positive political attitudes),这里的积极多与常态下比较,愈加肯定现有政治系统,并且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三方面均呈现出一定强度的上扬;另一种类型的变化方向是消极性政治态度变化(change in negative political attitudes),即个体对政治系统表现出比常态下更为低迷的判断,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不同取向上的变化可能具有“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积极性政治态度极大提升了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肯定、自豪与支持倾向,并由此解决了其长期困惑与不解的政治疑虑,增加了其政治肯定;消极性政治态度变化则更为低迷,情感更为委顿甚至疏离,支持倾向极为犹豫与不情愿,似乎加深了消极取向。这就表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所导致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效应可能并不是短暂的,有可能改变了个体原有政治态度,成为其未来政治态度的基调。

三、 非常态下政治态度
的
理论探索与争议
综观中西方关于非常态[2]下政治态度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两个方面的议题。一是非常态下的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非常态下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
第一,关于非常态下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的研究,大部分西方学者聚焦于自然灾害(洪水、地震、海啸等)对于政治态度或者政治参与的影响,认为自然灾害会引发民众的政治态度趋向激进,即民众在自然灾害的刺激下会增加对政治系统的关注(Nel, 2008; Ramsay, 2011; Fair et al., 2017),肯定性评价增多,产生所谓的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灾害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指出,受灾民众对于政府的态度更加激进,会了解更多的政治信息,参与选举的行为也急剧增加(Fair et al., 2017)。但也有研究虽然承认非常态下政治态度可能发生激进性变化,却指出非常态事件导致政治态度发生激进性变化的时间较为短暂,随着事件的推进,可能产生支持与反对两种态度变化(Jaeger et al., 2012)。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支持(陆剑云等,2015;尉建文和谢镇荣,2015)。由此可见,上述研究均表明在非常态下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究竟发生了积极抑或消极的变化存在争议。同时,这些研究对于衡量政治态度变化的标准相对外在,缺乏从政治态度内部构成成分、强度等方面更为精细的剖析。
第二,关于非常态下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本聚焦于两类单一因素的分析。一类认为,由于灾害或重大公共事件极有可能引发经济波动,进而引起政治态度或者政治行为的变化(Healy and Malhotra, 2010; Bergholt and Lujala, 2012),因此经济是否波动,成为联结自然灾害与民众政治态度变化的中介变量;也有学者发现政府对危机处理不善,增加了受害者对政府的不满,同时加剧了其对民主的不满(Katz and Levin, 2016)。另一类则关注被访者主观心理上的其他因素对于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这些心理因素包括灾难后的心理创伤或情绪的变化(Greenberg et al., 1997; Fair et al., 2017),如有学者通过研究美国“9·11”事件引发的政治态度变化,提出焦虑与愤怒情绪的相互作用是政治态度产生变化的中介变量(Lambert et al., 2011)。由此可见,情绪对于政治态度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对于公共安全事件下政治态度变化的解释路径均呈现出相互对立且单独作用的特征,可统称为“单一因素影响说”。然而,在现实中,一种政治心理现象的出现与变化,往往既无法摆脱情境的影响,也不能脱离自身心理因素的左右,甚至是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并发酵的结果。因此,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极有可能是链条式的多种主客观因素混合作用的情形,即所谓的“多因素互嵌说”。

四、 研究策略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回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变化路径如何这三个紧密关联的问题,本文相应地采取了三种研究策略。第一种研究策略,是设计访谈提纲、选择样本与访谈过程的设定,由此确定在某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第二种策略,是对已获得的资料就政治态度变化的内容、强度与方向等方面进行测算,以回应某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种策略,通过扎根理论发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促进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与变化路径。
(一) 访谈提纲的设计、样本选择与访谈
通常对于政治态度的了解较多采用李克特问卷,但是由于本文的第一目的就是考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后民众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只要能够获知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就达到了本次研究的目的之一,因此本文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抽样与问卷调查形式,而是采取了小样本深度访谈的形式,这样既可以较好地了解被访者政治态度变化的状态及其路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研究成本。
根据政治态度的内涵与构成,访谈提纲紧紧围绕某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前后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进行设计,借助对比的提问方式凸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动态变化规律。比如,(1)总体的政治态度:指民众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整个过程的感受以及对相关政治客体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总体评价,我们将问题设计为:“总体来看,您对某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扩散以及基本控制三个阶段的感受是什么?您如何评价政治体制、政府、官员以及相关政策?这些评价相较之前有没有变化?”(2)政治认知:由于政治态度的倾向性本质,政治认知更多地指人们对于一国政治系统中政治知识的关注与了解程度。所以,我们设计了如下问题以了解被访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前后的政治认知变化:“日常生活中您是否通过手机、电视等媒介关注政治类的新闻或知识?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您关注的频率和内容以及了解程度有没有变化?”(3)政治情感:指对于相关政治客体产生的情绪体验与准备,本次访谈主要指对各级政府与官员以及相关政治制度的亲近感与自豪感。因此,我们将此转变为以下问题:“平时您对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的亲近度如何?您对我国相关政治制度的自豪感如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这些情感有无变化?”(4)政治行为倾向:更多是指面对政治客体所产生的支持与配合的心理意愿,而非真正的行为。因此,将问题设计为:“平时您对各级政府、官员与相关的制度与决策的支持意愿如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相关行为意愿有无变化?”
在概念操作化、访谈提纲设计与访谈方式确定的基础上,为克服调研不便,对被访者进行了便利抽样。首先按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严重程度与累计确诊人数将不同省份划分为事态严重地区(确诊人数≥1000人)、事态较严重地区(1000人>确诊人数≥500人)以及事态不严重地区(确诊人数<500人)[3];随后,运用便利抽样的办法选取事态严重地区的W省、Z省,事态较严重地区的B市、J省以及事态不严重地区的S省、H省进行抽样,在抽样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保证职业分层、年龄段、性别的均衡与覆盖性,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最终,在考虑资料与理论饱和的基础上,共取得了24份样本,其中有效样本达到22份,无效样本2份。抽样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情况

续表

研究中我们采用了电话访谈方式,利用电话访谈可以更好地规避面对面访谈时的外界干扰,更为集中地获得相关信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被访者政治态度变化的状况,我们与每位被访者的访谈时间至少为一个小时,对个别被访者还进行了多次访谈。
(二) 对政治态度变化的测度
政治态度的变化可以体现在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政治态度的成分变化中,即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只有这三个成分发生了变化,政治态度在强度和方向上才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更为清晰地表达政治态度三个成分变化的状况,本文通过相对客观的赋值方法进行判断。赋值是量化思维在质性研究中的体现,类似的思维在QCA技术两分设计与应用中也有体现。具体赋值标准见表2。在统一设置的标准下,为最大程度保证结论的客观性,赋值与计算过程由单个研究人员完成,并由其他研究人员检验计算。经过计算,其结果全部符合研究者从原始资料中对被访者政治态度变化的总体感知。在22份有效样本中,政治态度积极性变化样本共计14份,消极变化样本共计7份,无变化样本1份。具体见表3。
(三) 扎根理论及其运用
扎根理论(grouned theory)是一种通过科学流程从繁杂经验材料中不断抽象概念并建立恰适理论模型的研究方法,最早于1967年由美国的两位学者格拉斯(Glaser)和施特劳斯(Strauss)首次提出,随后经历了多次修正与调适,存在经典扎根理论(Glaser and Strauss, 1967)、程序化扎根理论(Strauss and Corbin, 1994)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harmaz, 2006)三种主要类型。其核心以编码(coding)为依托,通常包括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和核心式登录(陈向明,1999),经过逐步归纳与提炼,实现了从概念到范畴,再到范畴间关系的演化。其目的就是通过对被访者访谈所获信息的多次提炼抽象发现事物间关系,常被用于复杂逻辑关系的因果机制建构。
表2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
变化的判断公式与赋值标准

注:赋值是以质性资料中被访者政治态度变化的节点为依据进行的,是政治态度变化的相对值。
表3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民众政治态度变化赋值结果

注:PC代表政治态度中的政治认知(political cognition), PA代表政治态度中的政治情感(political affection), PB代表政治态度中的政治行为倾向(political behavior tendency), R表示加权结果。横轴L1~D10表示样本的序列编号,为便于区分,L/X/D分别代表三位访员的访谈样本,1~10为样本编号。L1、L3、L5、X1、X4、X5、D1、D4、D5、D6、D7、D8、D9、D10为政治态度的积极性变化,L2、L4、X3、X6、X7、X8、D2为政治态度的消极性变化,D3为无变化。X2、D11为无效样本。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建模属于探索性研究范畴,与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其既能通过现实情境的剖析,从微观层面窥探民众政治态度的变化情况,又能从宏观层面依据相关理论,探索并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因此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确保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同时,随着访谈对象的不断增加,本文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验,当进行到第19位被访者时依然没有发现新的范畴,说明理论已基本达到了饱和[4],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最后,基于抽样,本文共收集整理形成了48621字的原始资料,并通过三级编码完成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形塑政治态度变化的路径建模。

五、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政治态度变化的图景全描
根据表2与表3,我们将加权为正的结果与加权为负的结果分别利用数轴坐标系建模(加权结果为0的剔除),从而得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积极性转变的数轴模型图(见图1)和政治态度消极性转变的数轴模型图(见图2)。其中Y轴表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间节点和政治态度成分的不同变化强度,以便区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前后的政治态度变化状态;从X轴的负坐标向正坐标的变化趋势分别表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等政治态度内部结构的变化方向,而X轴正坐标所定位的不同纵坐标则反映了政治态度内部成分变化的相对强度。

图1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积极性转变模型

图2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消极性转变模型
注:L1~D10表示样本的序列编号,为便于区分,L/X/D分别代表三位访员的访谈样本,1~10为样本编号。
由图1、图2可知,在有效样本22名被访者中,有21人的政治态度均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取向等成分的变化上,也体现在强度与方向的变化上,可以说明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政治态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再一次证实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民众政治态度的刺激是迅速且强效的,使得每一个置于这一情境中的个体一方面难以从熟悉且已有的记忆经验库中提取相似信息(Zaller and Feldman, 1992),另一方面在快速、瞬息万变的信息轰炸中极易动摇已建构的政治态度壁垒,不得不陷入重新学习(relearning)之中。由此看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是必然的。然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政治态度变化并非全然如已有研究所说的那样呈现出单一的激进态势,而是出现了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治态度内部成分的整体上扬态势(见图1)。在政治认知层面,较之常态下对政治的关注更多且对各级政府、官员与相关政治制度的认知水平有所提升;在政治情感层面,对各级政府、官员与相关政治制度的自豪感更为强烈;在政治行为倾向上更加支持与配合政府的防控要求。即使存在诸如X5(政治情感降低)、L5(政治认知降低)等个例,但多数情况下从模型图中可以看出被访者的政治态度较之常态下整体有所提升。且从强度来看,政治认知的变化幅度集中于“强度2~3”之间,政治情感的变化幅度以“强度2”为主,政治行为倾向的变化幅度则集中于“强度0”的水平。这就说明,民众的政治认知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变化强度略大于政治情感,政治行为倾向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不大,可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政治态度的内部成分变化并不一致,其中政治认知显然是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刺激最为敏感的因素。总体来看,政治态度积极变化的强度是一种中等水平的提升。
另一种类型是政治态度内部成分的消极性转变(见图2),除L2(政治行为倾向提升)外,几乎所有的数轴样态都呈全方位下降趋势。与积极性变化的政治态度成分相比,政治认知的变化幅度较集中在“强度0”的水平,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倾向的变化幅度相较集中于“强度-1”的水平,但并不稳定。这就表明,民众的政治认知变化不明显,而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则呈现下降趋势。相较于积极性政治态度变化的首要成分政治认知,消极性政治态度的变化在成分上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情感较为敏感,尽管变化强度与政治行为倾向无异,但政治情感数轴右半部分的变化幅度最大(X7、X8)。总体来看,政治态度消极性变化的幅度较小,其强度变化呈现轻微水平的降低,且不稳定性强。尽管消极性政治态度变化强度不大且以政治情感为主,但这种态度变化产生的影响并不小,这是因为政治情感是构成政治态度的核心因素。
由上所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发生了一定强度的变化,并且变化方向也不是单一方向,不同于已有研究描述的单纯激进性或消极性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是呈现出积极性政治态度变化与消极性政治态度变化两种类型。不仅如此,积极性政治态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认知强于政治情感、政治行为倾向变化不大的特点;消极性政治态度的变化则表现为政治情感的负向体现和政治行为倾向强于政治认知的特点。由此可推知,政治态度的内部成分中,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的重要性大于政治行为倾向,且不同的政治态度变化取向中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的作用强度也不相同。

六、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
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生成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政治态度发生积极性或者消极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路径是怎样生成的?文章采取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通过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核心式登录展现非常态下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逻辑。
(一) 编码过程
开放式登录主要是对原始访谈材料进行逐字逐句编码,为尽可能减少研究者的个人偏见,原则上使用被访者的原始表达提炼初始概念(王建明和王俊豪,2011)。本文经过编码与频次统计等过程初步提取出594条原始语句和对应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庞杂且存在一定交叉,经过对交叉概念和频次低于2的概念进行删减,同时为保证开放式登录的信度,对共同编码中出现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多次讨论决定,最终共计得出241条原始语句及对应概念。经过进一步分类整合,选取频次超过3的初始概念,共得出43个初始概念和15个初始范畴,为节省篇幅,本文仅呈现初始概念的出现频次与对应范畴。具体见表4。
表4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关联式登录则是通过对初始概念与范畴进一步分析,尝试寻找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归纳出主范畴,并进一步归纳为相应的类别。本文经过多次比较和讨论,对开放式登录的15个范畴进行归类,得到了中央政府防控行为、地方政府防控行为、宏观优势、微观矛盾、媒体推动、参照正效应、参照负效应、利益关切、个体政治价值观9个主范畴,并进一步归纳为政府防控行为、制度特点、媒体效应、参照效应、个体因素5个类别,具体见表5。
表5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核心式登录指对主范畴之间的联系做进一步分析并提取出核心范畴,尝试架构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经过对9个主范畴和5个类别进行深入分析,并不断对比原始材料,本文发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利益关切可作为核心范畴的发端,较好地开启政治态度变化的故事线,即个体基于利益关切,关注政府防控行为,并与媒体推动一起共振,使被访者的政治认知产生一定的变化(扩容或者固化)。而参照效应作为一个拐点,使个体对我国宏观政治制度、微观政治结构产生了不同倾向的政治情感强化,进而发生了政治态度积极或消极的变化,其中个体政治价值观作为政治态度变化的背景性因素,左右着政治态度变化的方向。具体关系见表6。
表6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注:L1~D10表示样本的序列编号,为便于区分,L/X/D分别代表三位访员的访谈样本,1~10为样本编号。
(二)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影响政治态度变化的共同因素与不同路径
通过上述三级编码可以提炼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促使政治态度发生积极或者消极变化的共同因素与不同路径。其共同因素均涉及利益关切、政府防控行为、媒体推动、参照效应、制度优劣和个体政治价值观六个方面。具体见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