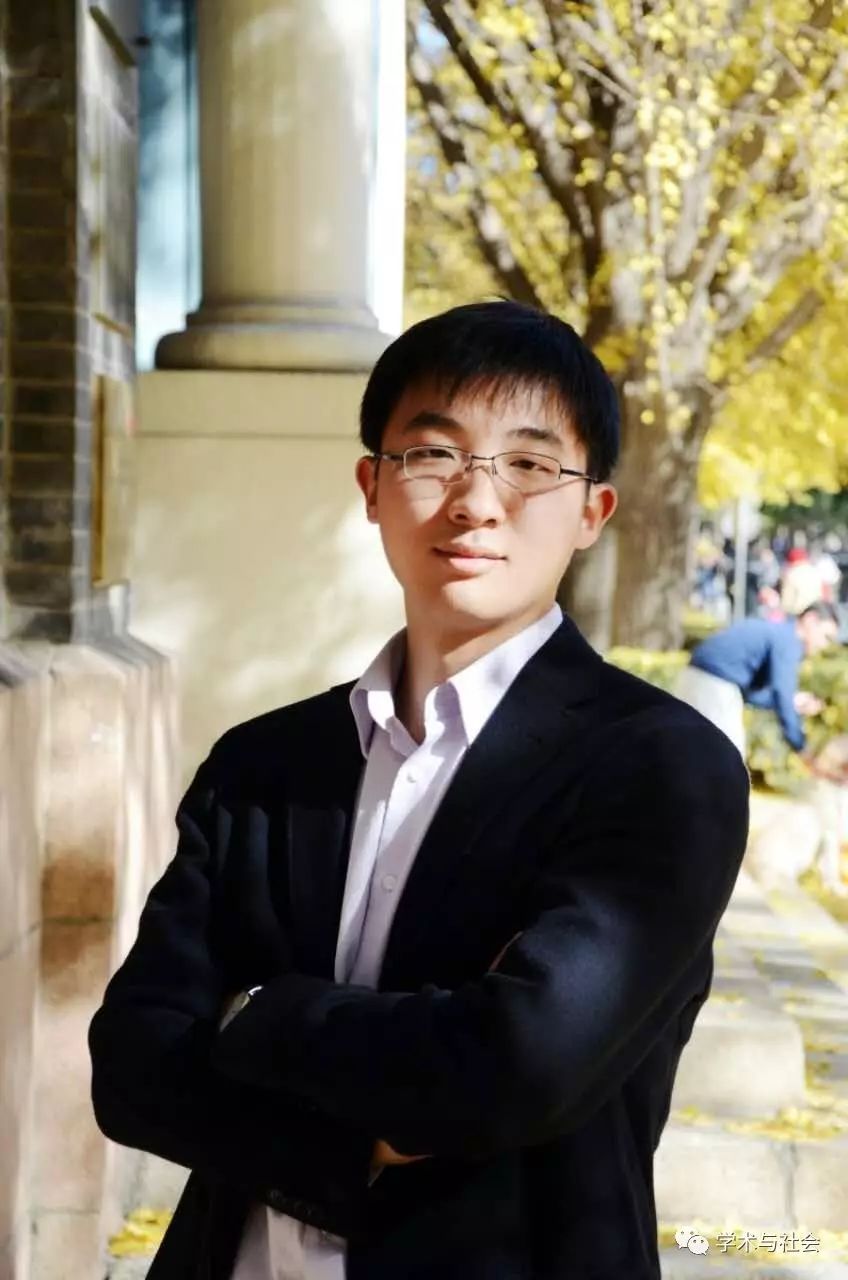
【石头引】
做博士论文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认为做理论研究不需要经验支撑。记得当年我刚毕业时,领导关起门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轻人,没有社会经验、生活阅历,不要随便套用书本上的理论,胡乱地揣测领导的想法”。这话今天想来,真是格外有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学社会学的,最怕读不懂社会。
“理论”研究最怕做成对经典理论的七拼八凑,或者是对
思维片段的牵强附会。
事实上
,即使做规范研究,最好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经验感。
另外一个误区是认为做经验研究不需要理论支撑,甚至认为今天再读涂尔干、马克思已经过时了。这种误区的后果就是
,即使面
对真实、生动和丰富的社会事实,研究者也会熟视无睹、视而不见。
因为缺少理论的素养,你就会觉得好多问题似乎是那么回事,但是又说不出来(更加写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举个例子,
《人民的名义》中
反贪局长陈海出车祸躺床上了,为什么祁同伟给陈家刨地,备受鄙夷,而侯亮平当着领导的面“赤裸裸”送去了一沓钞票,陈家老两口却很自然地就收下了?
理论素养与实证技艺是学术研究的两条腿,二者不可偏废其一,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好的研究,既是理论的,也是经验的。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经验的。
【作者简介】
唐啸,2015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治理和五年规划。论文载《中国软科学》,Sustainability等中英文刊物,内参发表于《国家高端智库报告》等,多次获国家领导人批示。中文专著《正式与非正式激励:中国环境政策执行机制研究》获全国博士后优秀学术成果奖,英文合著《The Modernisation of China's State Governance》将由Springer出版社出版。
【写在前面】
这应该是我人生拖稿时间最长的一篇文章了,到不完全是因为这段期间的工作压力,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则深感自己的博士论文学术含金量与此前诸期的老师和前辈们相比,差距未免有些太大,难免有些“丑媳妇不敢见公婆”之念;二来虽然《学术与社会》的是我长期关注和最喜爱的公号之一,对社会学也是“心向往之”但我自己却完全没有受过系统的社会学训练,发表的文章和博士论文中采用的定量方法也更多一些,很担心研究调研中的这点认识写出来过于肤浅,以致贻笑大方。
不过在石头老师的一再鼓励下,我还是大着胆子接受了邀请,最终硬着头皮攒下这篇小文,也算是对自己博士论文中心路历程的一点记录,更多的也是想以这篇小文表达对研究过程中师友支持的感谢。
2010年我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之后,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胡鞍钢教授。在读博开始之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从规范研究为主的法学领域转型到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公共管理专业的跨度并不亚于从文科向理工科的转向。而当时的清华公管并没有区分普博和直博,于是我这个在法解释学里折腾了四年,连定性和定量研究都分不清楚的本科生直接就一头就闷进了公管博士生的课程。在转型之初,面对公共管理专业课程训练中实证主义范式下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我犹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眼花缭乱而又茫然不知所措。至于与经管博士生同上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等课程,对我这个大一就已经结束了数学课程的法学生而言,无疑是天书了。
时至今天,我经常时不时的怀疑自己当初是如何通过的那些严苛的考试。不过现在想来,可能也正是我这样对实证社会科学一张白纸的认识,以及刚入“大观园”时东摸摸西看看的经历,促使我在博士论文的研究过程中,对方法乃至对诸多研究视角秉持了一种相对开放的“拿来主义”态度,虽然各项方法都学艺不精,但在一个困难重重的研究场域中,总算是东冲西撞,逢山开路,遇河搭桥,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一、问题提出:理论与现实的往返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方向,在导师胡鞍钢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定在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对这一选题的确定,不得不感谢导师的敏锐和善导。在研究选题之初,我对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兴趣并不是太大,总觉得过于技术化。作为一名受过法学训练的学生,我似乎天生的对国家制度、体制变革等宏大议题更感兴趣。但导师没有直接否定我的兴趣,而是以一种温和睿智的态度启发我:看似技术化的问题背后其实与宏大叙事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搭建这样的桥梁。现在想来,这大约是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对我的第一次启蒙。
选题方向确定之后,我很快就面临了聚焦核心研究问题的挑战。当真的扎入浩瀚文献之后,我很快便得了一种博士生常见病“为什么好问题都被研究完了?”这里“好”既指研究价值的好,在我内心私语中也颇有点“容易”的意味。不过,学术研究大约是很少有“容易”的机会。既有文献中自成体系的理论逻辑,和对现有事实的有力解释,都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难以找到研究空间。
不过,正如我本科时很喜欢的那句铭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事实本身”,当我努力跳出文献,将目光往返于理论与现实之间时,我开始发现那些存在于优美自洽的理论逻辑背后的冲突与矛盾。
作为一个生在这个快速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的青年研究者,我想是我们是幸运的,中国治理实践的不断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我检验既有理论带来了机遇。在我博士论文选题的同时,中国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制度设立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五年时期,对这一制度的讨论和效果的检验成为了可能。然后正是在对这一事实的分析过程之中,既往看似统一的理论出现了裂隙。一部分学者认为约束性指标提高了与环境绩效有关的官员奖惩效力,因此有力的改变了以往由“财政联邦主义”和“官员晋升锦标赛”所导致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较差的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宏观层面的数据支持。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由于中国科层制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如“减压阀”和“共谋行为”等,约束性指标并没有能够加大中国地方官员的环境政策执行力度。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定性案例的支持。
这两类观点在逻辑上和证据上都有一定的支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涉及到对中国科层体制下官员激励和政策执行问题的基础认识,可以说对这些问题学界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讨论,但是在更新的现实材料面前,此前看似牢固的理论大厦上显现了不可回避的裂痕。而对这种分歧背后的真相追求则是我当时的学术野望和自认为的可能贡献。这也促使我最终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中国约束性指标制度设立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最初设想的研究重点则聚焦于约束性指标中的十一项奖惩措施对地方官员动机与行为的影响。
二、初入黑箱: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限于中国政治的高度敏感性和官员群体的相对封闭性,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官员激励,特别是政策执行中的官员动机仍然是一个充满“迷雾”的黑箱。
因此当我最终确定将研究问题锁定于官员行为动机之时,相当忐忑,也曾经想过避难就易,做一些相对宏观的数学模型设立,在原有基础之上引入一些参数设定,从而推演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结果,形成一篇论文。但是,导师胡鞍钢教授在这一过程中向我强调,真世界,真方法,真问题的三真理念。在导师理念的鼓励下,我最终走出书斋,开始进行自己初步的田野调查和实证材料的收集。
带着书斋里的生涩和少许研究者的自傲,我开始寻找受访对象,试图让他们回答我所总结的学术界的理论冲突问题。然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尽管我曾经设想过被访者很多种回答,无论他们更支持哪一种观点,但我确实没有想到第一位被访者的回答就击碎了我之前的一切设想。
我找到的第一位被访者是我的一位师兄,在基层政府服务多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地方政府行政主官。作为一名同时拥有实践经验和良好的公共管理学训练的被访对象,应当说是相当完美的受访者。然而,当他听完我最初的研究问题之后,仍然充满了迷惑,这种迷惑并不是来源于他对学术界争论理解的困难,而是他对学术界为什么会执着于这些在他们眼中“细枝末节”讨论的疑问。
尽管我一再努力试图向他说明约束性指标制度文件中所罗列的这十一项奖惩措施可能对官员产生的影响和其理论上结果的重要性,他最终用一句话回答了我。"小唐,你说的这些,都不可能实质影响一位地方主官的政治行为"。
然而,当我以为天平似乎开始偏向否定约束性指标影响的方向时,他的回答却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期初的设想是多么的不完善。我继续向他求证约束性指标设立之后是否改善了地方环境治理时,他思考之后的回答却是“确实有改善,改善不小”。后续的追问囿于我初次访谈技巧的不足和师兄的顾虑,并没有能够继续深入下去。
第一位受访者看似矛盾的回答之后的几天时间里继续困扰着我,在某一个晚上入睡之前,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假设这位师兄的回答更加接近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在书斋里看似完美的理论推演上一定存在着逻辑问题和盲点。
在我继续不断努力的通过“滚雪球”方式扩大我的各类访谈对象——各类官员时,在夹杂着各类口音的访谈录音和各种自相矛盾的回答与数据调查中,在一个个午夜整理访谈稿的过程之中,这一个逻辑盲点终于逐步浮现了出来。
“约束性指标奖惩措施的有效性并不等于约束性指标的有效性。”当我第一次在电脑上敲下这行字时,我开始初步体会到那种学术发现的快乐。
坦诚说,和官员群体进行交流和访谈,并不总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过程,或者说大部分时候都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尽管母校,学院特别是导师动用了很多关系,为我创造了对多数研究者难以想象的研究机会和研究条件,但是官员群体职业所带来的高度谨慎性和话题的敏感性,都往往使得我的访谈和调研陷入到各类的真真假假的矛盾之中。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田野调查和材料收集的过程之中,我开始慢慢融入乃至逐渐理解了我的研究对象所面临的真实世界,也正是这一层的情感浸入,为我研究此后的推进奠定了基础。
当我真实坐进一位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在和他近乎同吃同住两周之后,我意识到此前一遍遍向一些地方核心领导人询问他们对约束性指标所规定的那些奖惩措施的观感和有效性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在中国五层体现的科层制下,一位县级地方核心领导人每天所要处理的日常行政事务的繁杂,所面临的突发事件和应急事件的困难性和紧急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因此,尽管制度文件的制定者和学界的研究者绞尽脑汁设计和推行各种各样精细的奖惩措施,这些奖惩措施其实很难如设想中那样真正达到行政血管终端。这并不取决于制度设计的精细,而是因为一个更为基础的逻辑。中国这样的人口巨国和行政巨国现实情况的复杂,并不是纯粹理性科层制的制度设计所能承载。
所以不只一位的地方核心领导人在面对我的问题提纲时,所显露出的茫然便显得是那么理所应当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一位管理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地区的主政官员,在正常的行政过程之中,去了解某一部门的一两项数字指标背后的具体奖惩措施是什么,更不用奢望他们会对这些奖惩措施产生最终的反应。当然,你也很难指望在这个已经形成自我运行逻辑的科层组织中,上级某一部门在常态下真的根据一两个数字指标对下级的核心领导人进行实质性惩戒。
三、黑箱内外:价值中立的价值
持续的田野观察为我进一步扩展视野和反思学界既有定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进入“黑箱”帮助我的博士论文有机会进入到了“不破不立”的阶段,但总结提炼事实,实现将“故事向知识转化”的学术生产,则成为我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来源于两个层面:
一是在材料挖掘层面,随着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进一步深入,早期研究时期“遍地新故事”的新鲜感已经过去,研究过程中的知识边际增量也在逐渐降低。这也促使我开始进入材料的深度挖掘期,试图理解和挖掘现象背后的核心逻辑。在研究进入到这一阶段,我开始意识到,已经不能够再仅仅简单依靠我的研究对象的讲述进行素描,事实上随着访谈的的深入,我开始明显的感觉到,
在被访者的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背后,有时并不是故意的隐瞒,而确实是被访者自己也并没有能够准确的认识到其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制度机制逻辑。这恰恰印证了那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二是理论建构层面,同样的“庐山”也矗立在重返理论的道路上。在对理论的回溯和反思中,我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思考此前研究中的逻辑盲点:为什么我们会将“约束性指标奖惩措施有效性等同于约束性指标的有效性”,进一步所衍生的问题就在于如果正式制度中的奖惩措施是没有效果的,那么究竟又是什么要素使得约束性指标产生了效果?
事实上,材料提炼难点和理论逻辑盲点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而解决这一问题,则不仅依靠的是在材料和理论的往返,更关键的启发则是需要跳出现实中隐形的“黑箱”和理论里难现的“庐山”。
在材料的整理和文献的回溯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在评判约束性指标制度的执行中,都近乎先验的将约束性指标正式制度的严格执行认为是推动环境政策执行正确乃至唯一的途径。所不同点在于,被访者更多强调的是正式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困难和被迫变通后的无奈,而学术界则直接批判了对正式制度的种种违反行为。进一步的分析,则不难发现无论是执行中的“变通者”还是研究里的“批判者”,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关于“正式制度”被严格执行的法治理想国。尽管不止一位的受访者谈到,如果严格按照约束性指标制度执行会产生的种种荒谬,但聊到如何加强环境治理,几乎所有人又都回到“严格按制度来,制度落实了,环境就上去了”的老路上。
所以当我跳出这样的研究情境,再一次的推理和审视。我意识到我犯了同样的错误,
先验的价值判断和对“法治”的向往,让我们忽视或者说并不相信非正式制度同样有可能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影响。
而产生此前逻辑盲点的可能原因就在于,我们相信且只相信约束性指标正式制度(奖惩措施)有效,环境政策执行力度就会提高。换句话说说,我们只相信约束性指标的正向影响只有一条路径。
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之后,我的研究思路开阔了许多,研究重点也开始转向约束性指标的非正式制度激励。新的视角,让我在审视同样的材料有了诸多的新的发现。例如,此前一位地方环保局长谈到约束性指标时曾经说过“这个事(约束性指标)能做成什么样,……,得看领导怎么说,……,单独说、会上说,拍着桌子和你说(效果不一样)”,如果依然带着先验的视角去观察,会将这个材料归入到地方政府核心领导人对正式制度的干涉导致执行失败命题之中,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依据核心领导人意志进行执行推进,那么视角就会转化为约束性指标对核心领导人产生何种影响的命题。
总之,如果不再带着“合理”和“荒谬”这样的价值判断,那么事实的挖掘和理论的建构会展现出一个新的“庐山”,尽管这座庐山依然有些云山雾罩,不一定是全部的真面目,但确乎是与此前眼中的“庐山”有所不同。
四、材料的使用:伦理与科学的兼顾
在我进入到研究中期之后,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处理定性研究材料也曾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由于我的研究对象的敏感性,以及在进入场景时的承诺,我最终没有选择初期曾经考虑过的定性案例研究方法,而是选择了CQR共识性编码对材料进行处理。这一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确实更加符合我博士论文前半部分研究里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感受,而采用这一方法也为我提炼概念和知识提供了工具的有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研究科学性。
但是最核心的考虑依然是研究中的伦理因素,当我反复多次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场景之中时,我不得不说,我产生了一种“理解之同情”。
坦陈说,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谨慎和顾虑,为研究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甚至是不可弥补的遗憾。但如果我能够力图切换到他们的角度,初步体味到他们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甚至是重新反思他们对自身工作价值的疑虑时,我不得不说,他们的谨慎和顾虑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这种顾虑存在本身就是中国官僚制度运行逻辑的反映,也是理解他们行为逻辑的重要切入点。
另一方面,这种理解也让我对那些相信我,并尽可能为我提供研究条件,乃至在各种场合为我提供研究便利的受访者,有了更深的感激,也最终促使我选择了一个也许会损失一定信息量,但可以更好的隐藏受访者身份信息的研究工具。
事实上,近乎所有的深度访谈受访者在后期都会谈到自己对这份工作和这份职业的理解,还有对我完成这份研究的期待。这种期待更多的来源于他们自身对更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环境的期待,来源于这些上至红墙内外,下至基层乡镇的受访者对理想,对事业,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期待。
所以在基于论文所形成的学术专著的致谢里,我为他们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扎根古老中国土壤里所特有的狡黠与野蛮生长的力量,他们可以有着无数的方法,让最现代化的公共管理工具陷入于水土不服;在他们身上,我同样也看到了可以上述至两千年前孔孟的士大夫责任和从最红热的革命年代留下激情与梦想,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以自己的智慧和责任从那些模棱两可乃至相互冲突的政策方案中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不再是文献与新闻里面目模糊乃至刻板的符号,不再是博弈论中假设的理性人,也不再是模型中那些机械的变量,而是一个个有着自己血肉与智慧的人。他们是服从的,他们也是反抗的,他们是固执的,也是变通的,他们是智慧的,也是盲目的。毋庸讳言,正是在他们彼此的冲突、矛盾、妥协与合作中,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而在这场正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发生的环境治理革命中,他们也是最重要的一员。然而,归根到底,他们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有着一样的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有着一样的爱恨情仇与利益取舍,这是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每一个职业都有着自己平凡和伟大。”
五、余论
行文至此,其实我博士论文的这一点粗浅心得早已可以结束。但最终还是想用这样一段话作为本文和我的博士论文结束,也作为我刚刚正式开始研究生涯的启示。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里,曾经极为早熟的创造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国家治理的机制。尽管这一机制在两千年的时间里被无数次修改,增补,完善乃至改头换面,但其内里的逻辑则顺着这个文明的血脉,若明若暗的延续至今。这一机制,创造了古典世界里人类治理规模的奇迹,也或多或少推动了新生中国的现代化奇迹,可毋庸讳言,无数次的治理失败甚至国家溃败也同样源于此。
今天,我们无时无刻生活在这一治理机制提供的国家公共物品之下,也近乎每天耳闻目睹的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的怪胎与荒谬。可我们对这一机制的了解,从现代社会科学学术的角度而言,却依然是不足的,甚至有时是片面的,狭隘的。这些不足有些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的客观限制,但可能还有很多是因为先验的价值观念所导致的主观误判。
因此,我在这一段研究历程之中,乃至未来的研究生涯里,将这样一句话作为我的铭言:“研究的意义不仅是发现和批评“荒谬”,而且是发掘和理解“荒谬”背后的逻辑,并为之提供改善的方案。”
毕竟,将更多的“荒谬”变为“合理”,是时代进步的最好标志。
-------------END-------------
点击左下角“
阅读原文
”,关注《学术与社会》并回复关键词“石头”,即可查看所有图文。
投石问路 | 如果匿名评审说不,该如何应对?
《博士论文》第51期 肖文明:没有理想主义的学术生活不值一过
《博士论文》第50期 杨春宇:博士出门,修行开始
《博士论文》第49期 陈拯:我用八年,写了两篇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