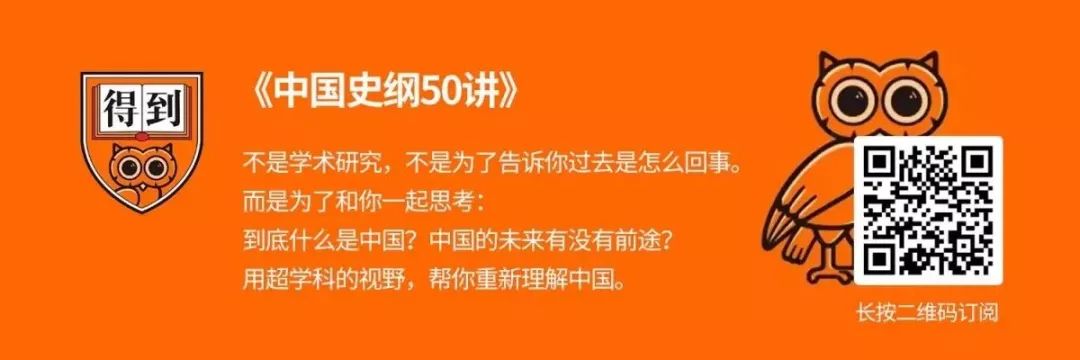导言:
冷战结束后,长期被意识形态对抗所掩盖的文明冲突逐渐显化,伊斯兰世界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产生新的冲击,对普世主义的权利观念也带来一系列必须加以回应的理论挑战。欧洲与美国的权利观有着一种微妙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差异,很可能它们因此而有着不同的历史责任。
节选自《枢纽》第七章“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失衡”第三节“全球治理秩序之变迁”。

反西方的力量需要获得自己的精神凝聚力与道德正当性辩护,曾被意识形态所压制的传统宗教及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衰退的情况下,重新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世界因此开始陷入一种“文明的冲突”的状态。

▲ “文明的冲突”就如同冰与火
多神世界开始在奥古斯丁秩序下面隐隐浮现,西方对此并未真正地有所准备,又一次精神悖反的过程于此展开。西方普世人权观的价值体系在冷战之后由于暂时丧失了真正的敌人,于是也就丧失了对于真正深刻严肃的政治问题的思考,逐渐走上对政治的技术化讨论,日常政治的琐碎与轻巧遮蔽了非常政治的深刻与担当,理想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被建制化,形成过度的“政治正确”,从而走向异化。
“文明的冲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严肃的政治问题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当中。如果说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主要是在物质层面;伊斯兰教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则主要是在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它使得西方秩序的道德正当性本身遭遇到挑战,并逼使世界直面“何谓政治”这个问题。
非常政治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重新激活,它需要特殊的精神强度与思想强度才能被真正地面对。精神强度与思想强度并不是一回事,对于问题的深刻反思需要思想的强度,面对决断时刻拥有行动的勇气则需要精神的强度。

在权利政治的时代重思“何谓政治”,需要先对权利观念进行辨析。对于权利的来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认识。
基于经年累月的社会互动形成了人们普遍默认的惯例,这些惯例对于人们的具体行为有实在的约束力,当它被法律化表达时,就成了“权利”。
启蒙时代以来,理性要求将一切都置于自己的审视之下,各种现成事实并不因其作为事实便自动获得正当性,除非它们经过了理性辩诘而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资格,思想家们基于理性的建构确认了一些权利,它们会被具体化为一系列法律,作为评判现成事实的标准。
信徒们坚信自己与神之间的神圣契约,它规定了作为个体的人在世间的义务,也承诺了个体在世间的尊严,人世的法律不过是用来保障神所赐予的个体权利。
这些不同的权利来源,呈现出的法律外观可能很相似,但是其底层的动力机制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些差别并不能通过对法条的分析而识别出来,它更多是基于对政治哲学,以及对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即使得法律能够活动起来的社会心理要素的分析而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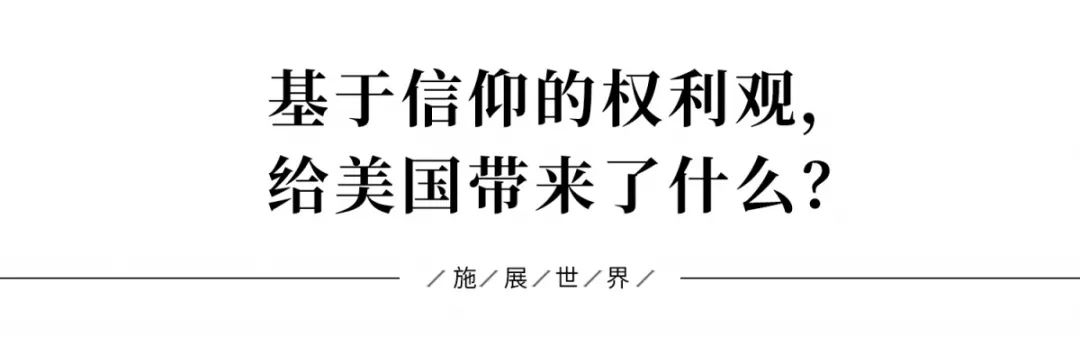
美国的权利观是基于信仰的。
无论是《独立宣言》的开篇所言,造物主赐予个体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还是美国总统手扶《圣经》宣誓的传统;抑或美元上印的“我们信仰上帝”;等等,都在提醒我们,清教精神贯穿于美国的政治哲学与民情,它以某种方式规定着美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它激励着美国人的开拓精神,也带来了美国人的傲慢自负。

▲ 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在美国所能发现的令人兴奋的东西与令人厌恶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伴生于清教精神的,无法单独剥离开来看。以信仰为基础,美国人形成了一种有时显得不合时宜地固执的权利观,它对应着一种责任观,权利与责任都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更具体地说,这样一种以清教精神为基础的权利观,在美国的东西海岸等高度国际化的地方,相对来说已大为柔化,这些地方的民情有些近于下文要谈的欧陆的权利观了;美国其他顽固坚持地方自治、重视宗教价值的区域才是清教权利观存留更加稳固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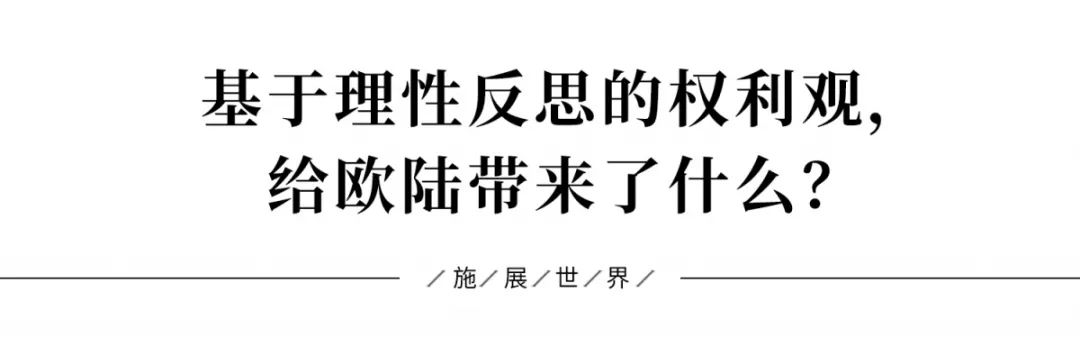
在欧洲方面,英国的权利观差不多是基于传统的,而欧陆国家的权利观则基于理性的反思。
欧陆式的理性反思有一种自反性的效果,任何绝对的东西在反思面前都无法彻底站住脚,它会突破任何禁忌,因为禁忌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

▲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主义
于是理性的反思,有可能令权利的扩展突破各种不容置疑的疆界,这种无止境的自由,使得人的创造力获得了巨大的释放,是人文精神与艺术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土壤;但同时它也带来一种相对主义的效果,权利似乎不是那么强固,它本身要经受不断的反思,在相对主义的情境之下,就可能导致政治意志的丧失与行动力量的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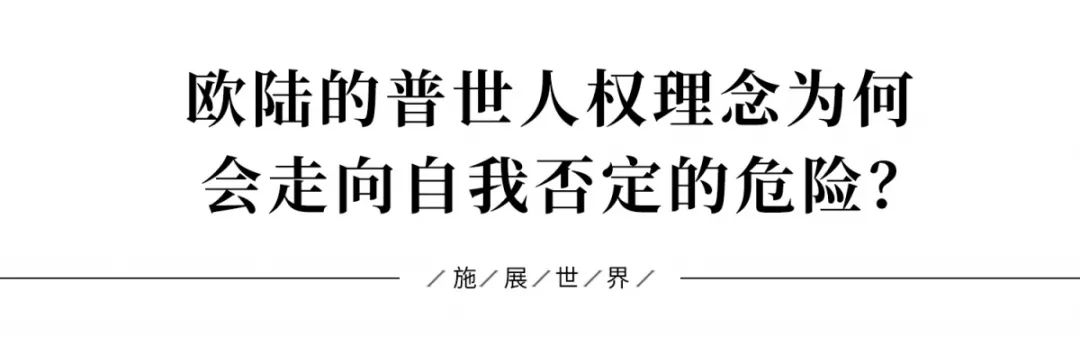
欧陆式(不等于欧陆)的理性权利观,拥有思想的强度;美国式(不等于美国)的清教权利观,则拥有精神的强度。但是一种奇妙的辩证在这里又浮现出来。

▲ 欧洲城市中席地而睡的难民
欧洲的相对主义虽无力,却因其突破了各种不容置疑的理念疆界,而走向了实实在在的普世人权实践。它在近年来对于穆斯林难民的接纳,甚至在一系列恐袭案之后也并未决意停步,正是一个极佳例证,因为欧洲在理念上无法将穆斯林排除在普世人权的承诺与保护之外。欧洲的这种决策有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气质,表达了一种极有价值的道德勇气。
但是这种道德勇气的悖反是,欧洲有可能一方面因此背上负担不起的成本,一方面将恐怖主义问题内在化于欧洲自身,使得相对主义的权利观有走向自我否定的危险,成了一种事实上无法普世的普世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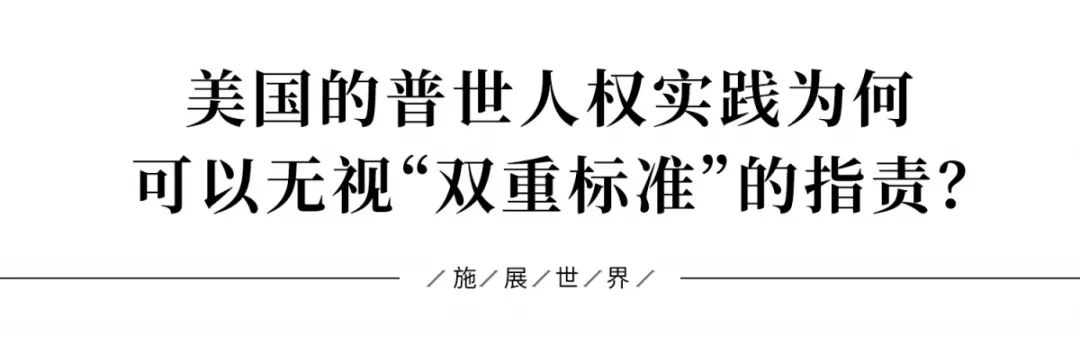
美国的力量支撑着普遍主义帝国,面对难民的时候却呈现出一种防火墙式的格局,墙的这一边是普遍主义法权得以适用的地区,另一边则是不能适用的地区。
普遍主义面对这种并不普遍的二元格局,可依凭对清教精神影响甚大的奥古斯丁神学来自我辩护。对美国来说,墙的两边只不过是善的存在与善的缺失的关系,缺失善的那一边尚不能适用普遍主义法权,并不是它在本质上不能适用,而是需要等待其完成对善的孕育,在此之前它是需要被隔离与规训的。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拒绝普世的普世主张,却使得美国的政治决断所需支付的成本,能够比较容易地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现代世界秩序需要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要求对各种禁忌的突破;但同时世界秩序也需要有力量维护自身,这又需要一种固执的不妥协。
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历史已经做出裁定,就西方文明对世界秩序的意义而言,欧洲负责勾勒未来美景,美国负责提供当下保护。美国的普世主义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虚假性,需要欧洲为普世主义正名;欧洲的普世主义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虚幻性,需要美国为其撑腰。旧大陆与新大陆,对于世界历史有了不一样的责任。

▲ 美国最高法院
单薄的日常政治视野,会让政治迷失在对细小问题的争论中,无法再直面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需要思想强度来回答,自由与正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人类需要精神强度来回应,在自由与正义遭受威胁之际,它如何保卫自身? 这种威胁可能来自外部,但它同样可能来自内部,来自理想的异化,来自建制本身的蜕变。
倘若丧失直面这些根本问题的勇气,将会让自由变得脆弱不堪,让人类的前景变得晦暗。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明的冲突”让人类的精神重新焕发活力,重新获得勇气,被建制化所异化的理想,也能够脱开建制的束缚,进行更为严肃的追求。
———— END ————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