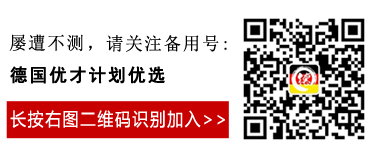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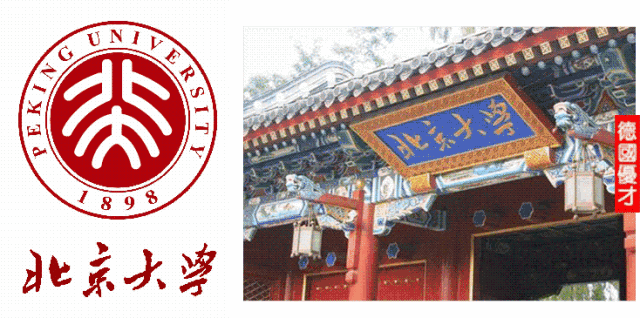
立国之本,尽在教育,
教育之本,重在大学,
今天,2018年5月4日,
五四青年节,
也是北京大学成立120周年校庆日,
北大首开中国近代教育先河,
而提起北大,提及近代教育,
就不能不提他,
他是今日北大的奠基者,
更是今天中国的引路人!
中华教育史上,
他的名字如雷贯耳,
可你却不一定知道他真正的传奇。
他,就是
蔡元培。

1868年1月11日,他出生于浙江绍兴,
自幼天资聪颖,为学勤奋专注,
无论冬夏,
每日必早起晨读,晚上看书至深夜,
冬天冷,他倒不在乎,
可夏天蚊子多,尤爱进攻双脚,
为了坚持学习,他把脚伸进坛子,
蚊子再多也不怕它咬脚了。
寒窗苦读十年,才华横溢的他,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7岁中秀才,
23岁中举人,第二年又中进士,
27岁时就成了翰林院编修。
1898年,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开始,
整个中国都在激情中欢呼,
只有他冷静分析:
康、梁二公做法太过草率,
寄希望在皇帝的几道圣旨上,
想要改变中国是不可能的。
果真如他所料,
维新不过百日就被惨烈镇压,
他更清楚意识到:中国积弊这样深,
必须从根本上培养人才,
才能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
他毅然抛弃大好仕途,
走上
“教育救国”
之路,
跑回老家绍兴办起第一所新式学堂,
开设化学、物理等科,
增加日语、法语教程,
聘请精通西学的教师,
而就在他锐意改革之时,
守旧派却纷纷跳出来阻挠说:“你这是造反!”,
他们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
徐树兰让他抄录皇帝“遵守旧礼教”的上谕,
并挂于办公室,
他愤而辞职:“我来这里办教育,
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
就这样,他第一次的教育改革被扼杀了,
之后的十多年,他一面关注国内革命形势,
一面疾呼“救中国必以学”,
乱世之中,
他的“教育救国”之路注定坎坷无比,
但无论遭到多大打击,遇多少失败,
他从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成立,
他即刻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
而他面对的,
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教育部连他就三个人,
没人不说还没钱,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
而他二话不说,拿了
印
就走马上任,
没房,就自己租;
没钱,就四处借;
没人,就自己去请,
如此教育总长,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个。
而他的工作效率更是震惊众人,
短短两个月,
“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
于此时大略完成。”
而在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开展之际,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之位,
他十分不满袁的专制独裁,
宁愿离开也不为袁效力,
袁再三挽留:
“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他脱口而出一句:
“元培亦代四万万人而辞职!”
在大权在握的袁世凯面前,
如此胆大包天,
普天之下,
舍蔡元培其谁?

随后他游学欧洲,
为中华学术崛起积蓄更多能量,
直到四年后袁世凯命丧黄泉,
他收到段祺瑞政府的急电:
“教育宜急,请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可许多朋友却劝他不要就任:
因为“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
进去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
可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那堂堂北大,当时究竟有多腐败,
才会被称之为“地狱”呢?
当时的北大,受袁世凯复辟的歪风影响,
完全不像学校,倒像个衙门,
监督及教员有的是大摆架子的官僚,
有的是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
所谓讲课,
就是把讲义给学生读一遍了事。
真正研习学术之人是少之又少。
而学生们大多都是官僚后代,富家子弟,
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他们来这里并非为学习,
而只是为混一张
“最高学府”的文凭。
更为混乱的是学校的风气,
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
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
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
(‘两院’指参、众两院,
‘一堂’指北大,京师大学堂)
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
这些钱,
不是用来
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
就是用来
“结十兄弟”,
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学生结拜,
毕业后谁官做得大,
其他九人
就到他手下当科长、
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
美其名曰“有福同享”,
而这个官,
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
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顾喆刚曾悲叹:
“如此贪淫成风、乌烟瘴气的北大,
哪里还能培养出人才,
只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
而这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
严复、章士钊、何燮侯......
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却要么被风潮所逼离开,
要么奈何不了学校的“官老爷”,
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毅然接过了这块“烫手山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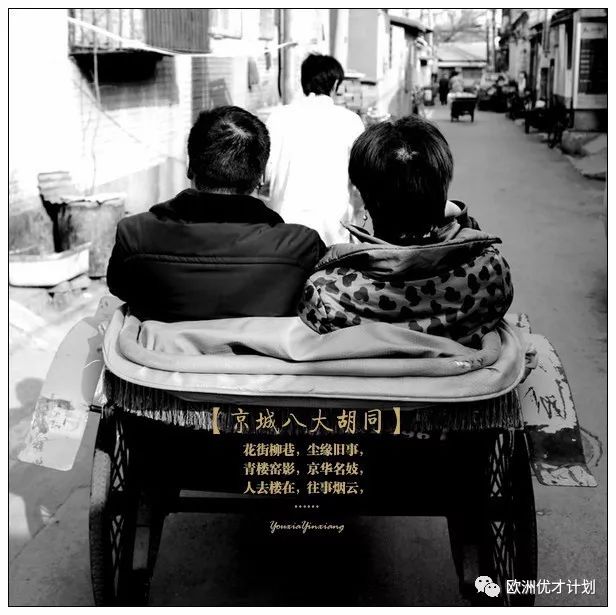
1917年1月4日,
他迈进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
就震惊了北大所有师生,
他脱下礼帽,
谦逊的向两边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以往的校长可都不可一世啊,
哪里有校长向校工鞠躬的?
这可是北大开天辟地头一遭,
他们哪里会知道,
这一躬不但是彻底改变北大的开始,
更是就此拉开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在开学典礼上他发表就职演说,
一开口就语惊四座: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给大学性质下了精准的定位: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
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
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他将教育定为国本,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他对学生们提出: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他还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全国文化之中心,
立千百年之大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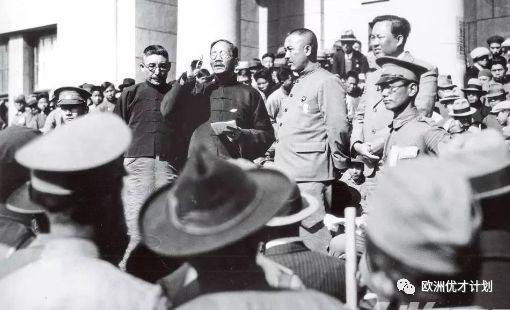
这篇演讲,志存高远,抱负宏大,
听呆了师生,震惊了中华,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那深邃、无畏,
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
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
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
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随后,他大刀阔斧的改革,
势如乘风破浪席卷整个北大,
他聘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将“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
“北”是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
“大”构成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这一设计理念在于要“以人为本”,
象征北大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

而他则亲自设计了北大校旗,
右边横列红、蓝、黄三色,喻意“科学”;
左边以白色为底,喻意“哲学”;
中间缀黑色北大校徽,喻意“玄学”,
“网罗天下,包容一切学问”,
他的宏大抱负,尽在这面校旗之中。

接着,他开始整顿教师队伍,
坚决剔除尸位素餐之人,
有几位英国籍教师,不但屡屡缺课,
还时常流连于烟花之地,
他知道后马上炒了这些人,
这些人不服气,请英国公使亲自登门谈判,
先是劝诱,然后威胁,
而他却始终不为所动:“留用绝无可能!”
最后闹到对薄公堂,以“胜诉”结束此事。
如此不惧强权,铮铮风骨,
普天之下,
舍蔡元培其谁?
他在中国四处寻求真才实学之士,
1917年夏,一大早,
他就跑到了北京西河沿胡同中西旅馆,
等64号房客起床,
这名房客既非大官,也不是名儒,
只是个穷酸秀才而已,名叫
陈独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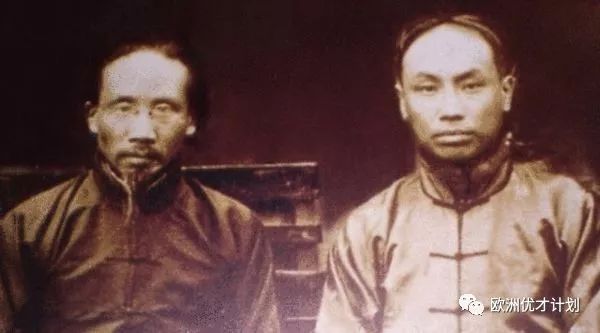
(蔡元培和陈独秀)
陈独秀起来后两人交谈起来,
陈说:“我没有学位,怎么能当文科学长?”
他笑笑:“好说好说,我给你发张证书就行”。
陈又说:“我是《新青年》主编,
可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
他又笑笑:“好说好说,
我将《新青年》搬来北大即可。”
就这样,陈独秀硬是被他请来了北大,
而且陈独秀的“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证书,
还是他给帮忙伪造的!
如此礼贤下士,“造假”魄力,
普天之下,
舍蔡元培其谁?
1917年9月,
年仅24岁的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
却遗憾落榜,
梁漱溟将自己写的《究元决疑论》寄给他,
希望能得他的赏识,从而进北大读书,
没想到,他看完后当即说
道:
“根基深厚,佛学见解独到,
他当北大学生没资格,
那就到北大当教授吧!”
于是,
梁漱溟就这样意外的竟成为了,
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
如此慧眼识人,不拘一格,
普天之下,
舍蔡元培其谁?

(
梁漱溟)
求贤若渴的他,
费尽心机几乎请来了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
胡适、鲁迅、
马寅初、熊十力
等学界名流,
周作人、刘半农、
李大钊
等革命先驱,
刘师培、钱玄同、
黄侃、
辜鸿铭
等国学大佬,
从此,
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
接着,他又举起一杆大旗:
“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
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
他以身作则,一手塑造出: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
1917年底,他出版《石头记索隐》,
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
胡适觉得他是瞎胡搞,牵强附会,
想找一本《四松堂集》,推翻他的观点,
结果到处都找不到这本书,
可某天有人敲门,胡适一看,
竟是蔡元培带着《四松堂集》来了,
如此容人雅量,
普天之下,
舍蔡元培其谁?
在绝无门户之见的他的带领下,
北大校园出现这样一幅幅画面:
辜鸿铭提倡文言文,
胡适提倡白话文,
他让二人隔空相争;
坚持旧文学的黄侃,
与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针锋相对,
他让二人同堂辩论;
西装革履的留学博士讲授孔子、老庄,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
操一口流利英语讲西方知识......
北大一时流派纷呈,盛况空前,
可以说:当时有多少学派,
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
中国有多少党派,
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中华历史五千年,春秋战国之后,
也只有他引领的北大,
第二次实现了“百家争鸣”的辉煌,
北大,
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和学术中心。

随后,他又提出
“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
他说:“要使学校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牵涉,
需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治校体制,
这样,即使没有校长,学校也不会乱。”
他设立“评议会”,
“评议会为北大最高权力机构,
从教授中选取评议员,
凡校重大事务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他将校中大小事务,俱任教授处理,
如此不贪权不慕名,
普天之下,
舍蔡元培其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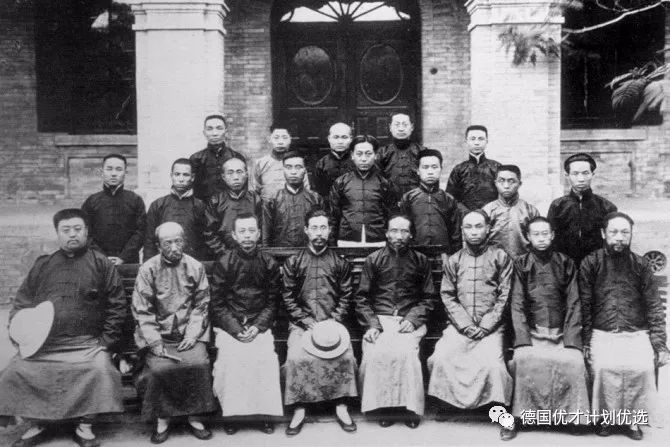
而评议会所作决定,
凡是“难事”“恶事”,都由他出面摆平,
有段时间,教育部拖欠北大教师薪资,
为维持教师生活,
评议会决定征收少许讲义费,
部分学生不肯交纳,为此聚众抗议,
他挺身而出:“你们闹什么?”
为首学生说:
“沈士远征收讲义费,我们找他理论!”
他说:
“这是评议会决定的,我是校长,我负责!”
学生大喊:“你倚老卖老!”
50岁的他毫无惧色,挥拳道:
“校规已立,谁不服,我跟你决斗!”
学生们被他气势所慑,全部散去。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从此北大面貌焕然一新,
不但成为中国最自由大学,
也成为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
“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
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之时,
才得以真正的诞生。”

为更好育人,他兴办各种科学研究所,
首开中国近代大学研究所之先河;
增设兴趣社团,
体育会、雄辩会、技击会等,
后来,新闻研究会中走出了一位伟人,
他叫
毛泽东。
为更好修德,他创办“进德会”,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
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
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他率先选择乙种会员,
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
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
成为了公认的模范会员。
之后他更是一举打破封建桎梏,
要求北大招收女生,
开启了中国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例,
他还提出领先时代的“五育并举”:
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
美育教育,
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之先河。

他来北大不过两年,
北大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人间地狱”涅槃重生为“学术天堂”。
“各流派之间,新旧文化你争我辩,
产生激烈的碰撞。”
“学生沉浸于好学与乐学之中,
争相进取,不甘落于人后。”
而这样的好学之风,不仅席卷北大,
更是席卷了整个北京,甚至影响到全中国,
他仅凭一己之力,
就扭转了整个中华历史!
顾颉刚曾评价说:
“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
摇身一变,
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
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梁漱溟说: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
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
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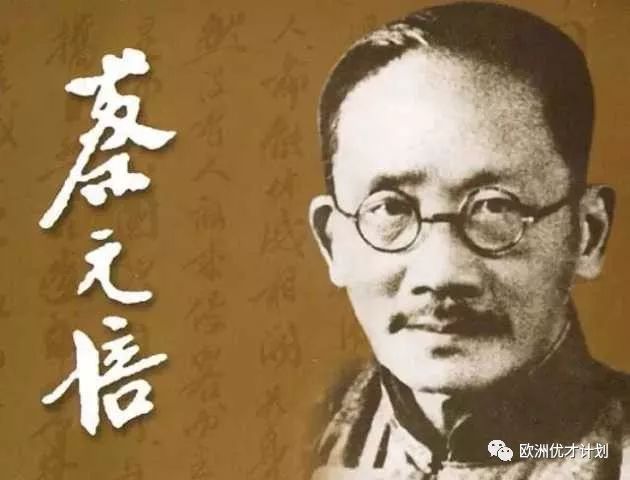
之后近十年间,
他不但使北大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学府,
更是源源不断的为中国输送栋梁之才:
朱自清、冯友兰、蒋梦麟、
杨振声、罗章龙、顾颉刚
等等。
北大校长无数人,可一提起,
我们只会想到他的名字,正如杜威所说:
“以校长身份,
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
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拥有蔡元培的北大,自此成为绝响!
而他成就了北大,
北大也回赠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吴梅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做了一首校歌,
送给北大,也送给校长蔡元培:
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培栽。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
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这是北大第一首校歌,
也是中国迄今为止,
唯一一首写入校长名字的校歌,
中华校长无数人,
唯有蔡元培,担得起这份尊荣。

1927年,居功至伟的他,
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
同时卸任北大校长,
离开北大,他又展开更大的宏图,
他要为中国建立一个最高学术研究的机关,
这也是中国几代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
在他努力奔走下,
1928年1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
孙中山、严复、
梁启超未完成的事业由他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