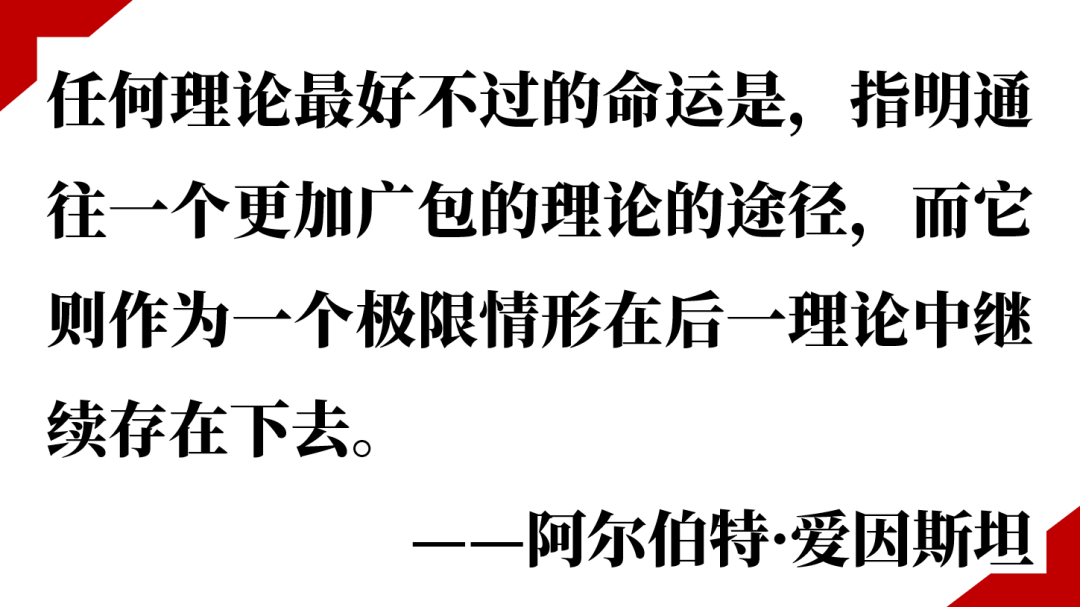
在以往历次的微信文章中,笔者或多或少都会对结论导出的认知途径有所涉猎。人们思考问题总得依靠一个相似性、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但现实是并非所有的参照系都是正确的,如果初始锚下得就有问题,那么后面的解决方案更难言正确,尤其是那些被大家广为传播的、权威的、公认的参照系,如果不敢或不能质疑、反驳,进步就无从谈起。
知识的来源
发端于文艺复兴,又历经改革、宗教战争和革命战争的变迁并导致近代科学技术诞生的这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始终受到一种空前的认识论乐观主义的激励。这种乐观主义对人察明真理和获得知识的能力持一种十分乐观的态度,其本质在于主张真理是显现的。
有乐观主义,也必有悲观主义。当认识论乐观主义遭遇现实打击的时候,认识论悲观主义力量就会抬头,此时人们做事就会倾向于传统的权威。这一观点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如果对于一件事情的解决,当我们有N种方法时,我们不太介意用另外一种更合理的方法来替代这种不完美方法,但如果对于一件事情的解决,我们只有一种方法,那么即使我们明确知道这种方法有明显的瑕疵,我们也倾向于继续沿用这一方法,我们更难接受的是完全的浑沌所带来的失控感。
这里主要还是谈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信念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真理必胜论。只要赋予真理相当的机遇,真理、善良就必定胜利,如果显现的真理没有获胜,那么它一定是被人蓄意地压制了。因此,每当事与愿违,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也应运而生。
简单的真理是:真理往往很难达一致,并且一旦发现,也很容易得而复失。错误信念可能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它无视经验,也无需任何阴谋的帮助而能延续千万年。
显现真理说是笛卡儿和培根两人的学说的核心。笛卡儿把他的乐观主义认识论建基于神赐真理性的重要理论之上,即上帝的诚实必定使真理显现出来。培根则基于大自然真理性,心灵纯洁的读者不可能误读它。只有当他的心灵为偏见所毒害时,他才可能陷入错误。
笛卡尔神赐真理性学说认为,我们的理智是知识的源泉,因为上帝是知识的源泉,为了区分真理和谬误,必须只依赖理智。神赐真理性学说有着更久远的源泉——柏拉图的回忆说,只要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居留和加入观念、本质或本性的神圣世界,它就处于神性的全知状态。人的出生是他的堕落;是他从自然的或神的知识状态堕落,作为回忆的结果,真理恢复到未被忘却也未被隐藏的状态:它就是显现的真理。
源泉说是个遗传的问题。它本着这样的信仰:知识可以其谱系证明为合理的。背后有着这样的形而上学观念:纯种知识、未玷污的知识和导源于最高权威、导源于上帝的知识的高贵性。
从逻辑上说,认为一个陈述的真可通过探索其源泉来判定的奇怪观点与语言中概念、定义同我们的陈述或命题的真理性之间的深刻相似性有关,但
相似并不等于相同
。源泉说的逻辑是:如果起源能决定一个词语的真正意义,那么,它们也就能决定一个重要观念的真正定义,至少能决定一部分基本原理。但是,现实世界中,定义从不给出任何关于事物本性的事实知识,我们试图在起源问题和事实真理问题之间建立的逻辑联系破裂了。
同样,培根的观察源泉说也是错误的。观察每前进一步,就需要前进更多步,每个人在叙述时总是充分运用他有关人物、地点、事情、语言惯用法、社会习俗等等的知识,而且观察中也总会遇上那些不可直接观察的因素,追溯一切知识的源泉是通过观察在逻辑上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叙述谬误将导致无限倒退。
什么是我们知识的源泉呢?
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有权威性。
关于探讨知识的终极源泉的根本错误是,它没有十分明确地区分起源问题和正确性问题。当我们考察历史时,把历史源泉的内容加入进来考察是必要的,但若要
断定任何一个陈述为真,考察或检验则必须直接对断定本身进行,或者对其推论进行,它是否同事实一致。
经验主义者的问题“你如何知道?你的断定的源泉是什么?”提法上就是错误的,这是企求独裁主义回答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已经知道,我们的知识是猜测、意见,而不是真知、认识。所以应该代之以“怎样才能有希望发现和消除错误?”这样的问题,而正确回答是:
通过批判其他人或自己的理论或猜测。
由于没有一种源泉具有权威性,所以,人都不具有用律令确立真理的那种权威,传统知识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和传统主义决裂,为什么?因为除了少量的先天知识(如数学等含有必然性的知识),我们知识的源泉大都是传统,但如果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知识,它们是批判、反驳的原材料。虽然我们有时可能通过一次偶然的观察而进步,但一般都取决于它修改我们以往传统知识的力量。
在一个反驳、拒斥各种猜测的体系中,只要我们去寻找,就往往能找到一个值得保留的真实观念。虽然观察和理性都不是权威,但是观察、推理甚至直觉和想象的功能也非常重要,它们能帮助我们批判考察那些大胆的猜想,而我们凭借这些猜想探索未知。
科学的分界
关于科学的分界,一个曾经很流行的理论是维特根斯坦的分界标准,它继承了培根的观察源泉说,该理论主张:一切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命题实际上都是非命题或假命题;它们是没有意义的。一切真正的命题都是描述“原子事实”,即在原则上可以用观察肯定的事实。这些“观察命题”都是描述可能事态的简单陈述并能加以引申,而且在原则上能通过观察加以肯定或者否定。所以,全部的观察为真的命题就是整个的自然科学。
维特根斯坦的分界标准就是可证实性。但是这个标准太窄了:它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排除掉了;同时,这个标准又太宽了,它却没有排除掉占星术——一种基于大量观察与陈述的伪科学。
更为公认的回答是:科学不同于伪科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地方,是它的经验方法;这主要就是归纳方法,是从观察或实验出发的。维特根斯坦的可证实性标准也是采用归纳方法。有些理论有着明显的解释力,是因为我们看到确证事例无所不在。不竭的证据就是这些理论典型的特征,然而细究起来,不过是顺序在先的归纳法在起作用。
每个观察都用以前的经验加以解释,同时本身又成了补充的确证。它确证了什么呢?无非是可以用这理论解释一个案例而已,但除此以外就再无其他信息含量。但是它们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构成了支持它们的最有力的论据。事实上,这个表面上的长处正是它们的短处。有必要重新定义一下确证,只有当未经待反驳理论的启示就已经预期一个和这个理论不相容的事件,这才算得上确证。
从理论角度看,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因为陈述或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能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得到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对一种理论的任何真正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
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人们常说,科学解释是把未知还原为已知,实则是科学解释是把已知还原为未知。应用科学把纯科学当做已知的,而在纯科学中,解释总是把假说逻辑地还原为其他普遍程度更高的假说,把已知的事实和理论还原为我们尚知之甚少、还需加以检验的假说。
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
“任何理论最好不过的命运是,指明通往一个更加广包的理论的途径,而它则作为一个极限情形在后一理论中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还是需要当心某些理论逃避反驳的行为。有些理论被发现为假时却仍旧大行其道,这因为有人为营救该理论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这种行为被称为“约定主义曲解”,语言就是人为约定的产物,人们总是可以通过人为约定来免于理论被驳倒,如果初始阶段,定义的陈述就已经是谬误,我们很难一时证伪,这样营救理论就可能暂时得逞,但这是以破坏或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为代价的。
归纳与演绎
因为理论的归纳一定是从观察中得来,所以对“科学是从观察到理论”的否定常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这种单独从纯观察出发而不带有一点点理论性的东西的信念反而是荒唐的。观察很少是随便的观察,通常按一定目的进行,旨在尽可能获得明确的反驳根据以检验理论。
观察作为一个及物动词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它还需要以相似和分类为前提,分类又以兴趣、观点和问题为前提。
因此,人们以猜想和预期作为一种背景参照系来接受的那些理论。实际上,一直是我们主动地企图把规则性强加给世界,这种对规则性的期望无论在心理上还是逻辑上都是先于观察的,尽管这种期望可能失败。我们企图在世界中发现相似性,又把相似认作相同,并用我们发明的规律来解释世界。我们不等待前提就跳到结论,这个结论如果被观察证明是错的,以后就得放弃,这就是试错——猜想和反驳。
假设还是观察哪个在先?回答是:一种较早的假设。我们选择的任何特殊假设在它前面都将有过一些观察,但是这些观察反转来又预先假定已经采纳了一种参考框架,一种期望的框架,一种理论的框架。正是这些观察不能在旧的理论框架、旧的期望水平上加以说明,所以人们需要发明假设。
休谟早就指出归纳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归纳法只是把事实问题与论证合理问题等同起来。因为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过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
数学的均衡前提为归纳法提供了用武之地,传统科学也为归纳的应用制定出一种法规即专业规则,人们又把企图把这种成功推广到日常生活,也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不区分现实世界的广阔领域与理性的狭窄领域两种情境的行为,造成归纳法在现实中应用屡屡失效,因为现实中却并没有归纳有效的确定标准。
归纳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借助于概率。这个提法也是错误的。同复杂的理论相比,简单的理论总是有较高的可检验性。一个理论的简单性同它的逻辑不可几性相关联,而不是同它的可几性相关联。现实中采用归纳法的人逻辑可能是这样的:通过观察发现一些或然性,通过更多观察提升为概然性,然后用概然性去替代必然性。但是我们寻求的是高确认度的理论,并不寻求高概然度的理论,因为我们始终需要寻求有力的解释。
清晰、明确、连贯都不是确立真理的标准,相反隐晦、含混、不一致性却可能象征错误。演绎逻辑推理的作用对于批判方法非常重要,演绎是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的推理。只有通过演绎推理才能发现理论的涵义,从而有效地批判它们。批判就是力图找出理论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一般是在这一理论推出的比较间接的逻辑推论中找出来。
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演绎工具可以作为排除虚假理论的方法——否定式假言三段论。它具有大小两个前提与结论,其中大前提与结论是正确的假言判断,假言判断指形式为:“如果......那么…...”,“如果”后面的判断叫“前件”,“那么”后面的判断叫“后件”,否定后件,也必否定前件。否定式假言三段论的逻辑结构表现为:
借此我们可以判断许多命题的真假。举例来看以下两个陈述:
陈述一:如果想要做到准确判断,那么就需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现在我们为判断某问题采用一些主观的指标,我们就必不能在该问题上做到准确判断。
陈述二:如果归纳只是使理论成为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那么理论无助于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在某项研究中解决了问题,我们就一定不是依靠归纳理论的可能性来达成的,而是依靠某种必然的因素达成的。
如果第一段假言判断为真,而
我们又接受单称陈述的真实性的话,这使我们可以断定全称陈述的虚假性。
在我们通过观察陈述排除虚假命题的同时,我们也很容易走向未被证伪的领域,它比被排除的虚假理论更重要,是因为那里可能还蕴藏着真理。
演绎之所以正确,不是因为它是人为树立的权威致使这些规则将被接受,而是因为它采取了和包括了真理据以从逻辑上较强的前提传递到逻辑上较弱的结论、谬误据以从结论逆传到前提的那些规则。
我们借助演绎工具进行猜测和反驳,而猜测与反驳就是大胆地提出理论,竭尽所能表明它们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那就试探地加以接受。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仍如此。在一个理论被驳倒之前,怎么也无法知道必须以哪种方式修正它。批判态度可以说成是有意试图让我们的理论、猜想代替我们自己去经受适者生存的进化竞争,然后使我们得以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