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海峰、李兵
来源=《中国科举史》
改革举措的酝酿
尽管如此,历代统治者通过八股取士选拔少量的治国精英,却造就了许多除了举业之外一无所长的儒生。八股文类似于一种汉语文字游戏,有的人多做之后容易痴迷其中,染上“八股癖”。当士子将才思过度集中于做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文字游戏时候,自然无心也无暇顾及其他学问和营生。因此,改革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鸦片战争敲开了清政府闭关的国门,中国被迫从传统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而八股文体日趋衰薄,以八股取士,不仅无法起到“正人心、正学术、正道德”的作用,反而具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消极作用,加之八股文的命题来自《四书》《五经》,根本不能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相适应,“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矛盾日渐凸显。批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成为包括洋务派、维新派等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共识。
随着八股取士弊端的日渐暴露,批评的声音亦愈加猛烈。魏源认为必须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他说:“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训诂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魏源:《魏源集》之《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他主张以实用知识试士,他说:“故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法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例案。”他还建议在闽粤两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选拔海军人才。录取之后,“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魏源的这些建议都是十分切合当时强军的实际需求的。
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日益加深,清朝统治岌岌可危,改革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王茂荫、黎庶昌、桂文灿曾先后上疏指陈时弊。如王茂荫要求“于各途考试之外,更切旁招,使有才者不终淹,而无才者无所幸。”他建议罢去时文、小楷,殿试改用誊录,以矫正士习,振兴实用人才。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探花冯桂芬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而设立的,因此必须改革科举,他说:“至近二三十年来遂如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因此他主张必须改革科举。他建议加大考试内容的难度,他说:“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具体而言,他建议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宜先试汉代经学,然后试宋代经学,原因是后者比前者容易;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以古学为第三场,试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并主张将三场各设一名主考官而分校之,可以克服以一场考试的优劣确定考生录取与否的弊端。会试和殿试亦然。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在教育方面,冯桂芬主张在广东、上海建立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住院肄业学习,聘西人教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教经史等知识,兼习算学,“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赏给举人。”冯桂芬还建议在通商口岸拨款设船炮局,聘请洋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教授众匠工。对于达到或超过洋人水平者分别赏给举人或进士,允许参加会试或殿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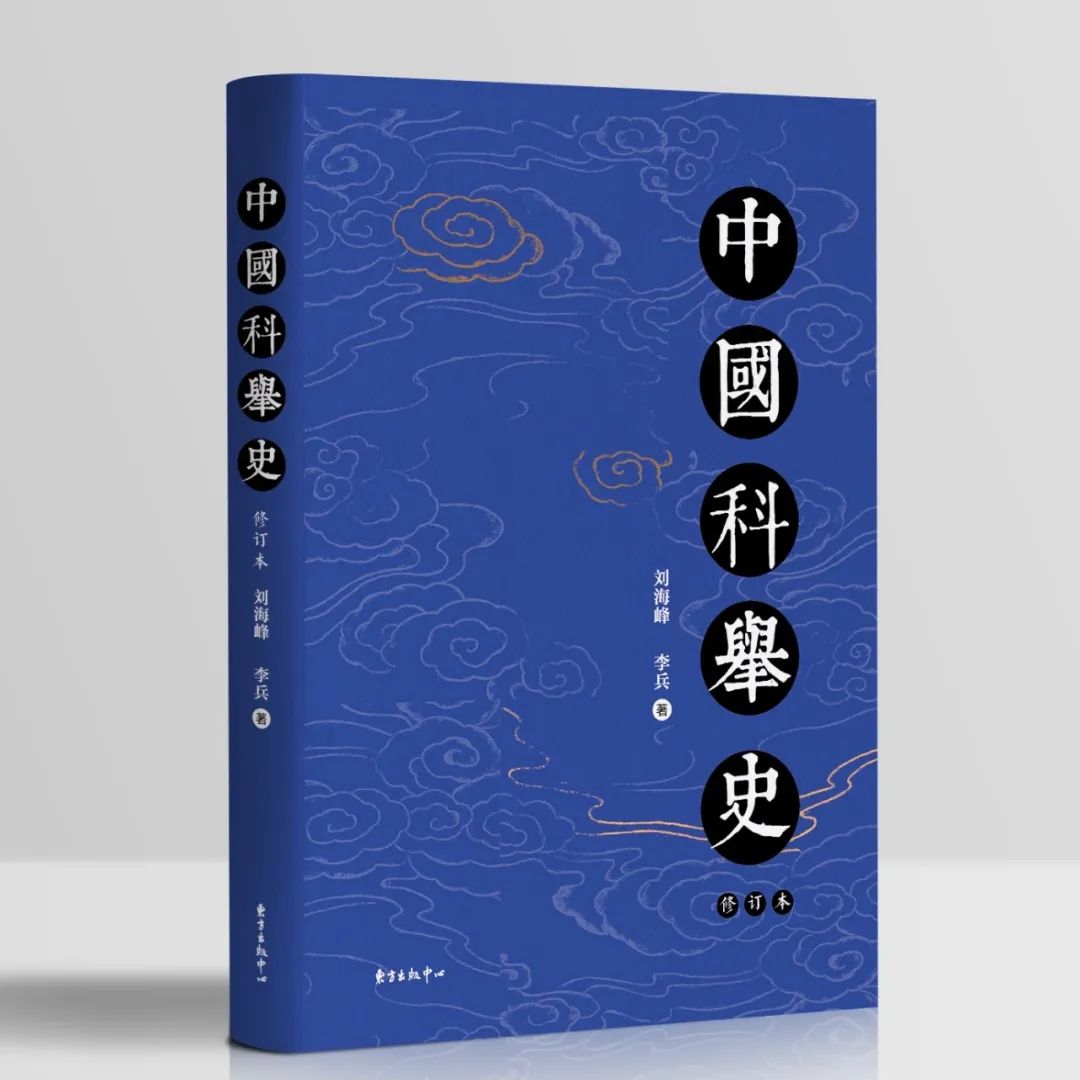
《中国科举史》
以学习英文、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自居的郑观应比较中西方的取士之法,认为西方取士制度的考试内容是实用技术,而中国的科举的考试内容是空疏无用的八股文,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显然明显落后于西方。他说:“泰西取士之法”,“无论一才一艺,总期实事求是”。而中国的八股取士则不同,他说:“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夫以八股为正途,视别学为异端,其不重可知矣。人材焉能日出哉!如是,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他主张科举考试分两科进行,首科考经史、时事策、判例案;次科考西学,“一试格致、算、化、光、电、矿、重诸学。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以期借此选拔精通有用之学和富强之事的人才。但在郑氏的改革方案中,认为考西学与科举制度可以并行,科举制度可以保留。他说:“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国家成法也。”
与此同时,郑氏也看到,即使考西学,“恐未必能与正科并重”,必须模仿西方近代教育体制设立各级学校,在州县设小学,各府设中学,省会、京师设大学,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西学为主。并将学校考试和科举制度联系起来,各级学校的学生仍称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同时实行三年一试,由朝廷命该省督、抚、水陆提督会同学校的掌教评阅,“其历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试,考取后名曰艺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这种以学校考试选材的办法,是科举取士仍占主导地位情势下的变通,也反映出他的对科举制度容忍的态度。
以谋求自强、富强相标榜的洋务派认为八股取士与洋务运动无丝毫关系。为选拔培养洋务人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增开洋务科,并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等科目,如洋学局学生学有所成,则将其科举出身同等对待。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十七日,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折》,他提出要仿照翻译科设立艺科,凡是“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都能报考,将算学列入艺学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之一,并制定了章程十二条。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
光绪二十一年(1895),荣禄、陶模等人上书变通武举,建议以武学堂取代武举的培养和人才选拔。荣禄在奏疏中说:“若每省延聘精通洋操之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岁之后,可成精兵。定以学习三年,作为武生……三年由督抚考试,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陶模也建议:“兵士宜自幼入学校,分别水陆,各习专门,学成后,作为水军、陆军秀才,咨部考试作为举人,而罢去旧例武科。”
不仅中国的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来华西方人以异质文化者的身份也关注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其利弊得失往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可能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对科举改革提出不同的解决之途。
1882年7月20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中国专尚举业论》一文,批评分析了科举取士的弊端,指出:“天下智能才艺之士一一来(应为‘束’——引者注)缚于举业、制义、试律之中,而不知变计之为,可惜也。”他认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空疏无用,“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专尚举业有害而无利,并说:“窃谓今日之中国,纵不能举举业之制义、试律而废之,亦当如有唐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多其科目,而又参以宋司马温公所云……十科取士之制而斟酌行之。其会垣郡邑之书院不必专课制义。”他还建议设立机构,仿照西方之法学习科学技术。他自称:“余西士也,本不欲妄参末议,为越俎之谋。特居中国久,不无杞人之忧。因西学为当务之急。”
传教士花之安也认识到了八股取士的弊端:“八股虽美,非有实际,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天下至理无穷,事物何限,岂八股所能尽耶?”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批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做法,认为这只能是束缚士人思想,他说:“是为搭题文法所限也,既不足益士子之大智,更不能阐圣道之渊源。”同时,他还认为科举考试仅以一篇文章定考生的去取,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他说:“况人固有千日之短,一日之长者,场中灵机偶动,必有佳作,亦必录取之矣。”“要宜知人之能文,乃学问之偏端,非学问之全体。夫能文者,不必尽为博学,即博学者,亦不必尽能文也”,不能断舞弊、启人干禄心、不暇及他学等弊端,并得出“考试之典,利少而弊多”,应该变革的结论。
西方人大多不主张废科举,但在改革科举的方向上,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深入认识的西方传教士主张复古,采用唐代科举多设科目的办法,或参照古代乡举里选的办法;而更多的人则是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废除八股文的同时,在考试内容中引入西方科学知识。例如从1865年起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起任总教习(校长)前后达31年之久的丁韪良,曾翻译引进了许多西方著作,他主持的同文馆成为清末算学科举的评卷处和及第者的归宿,他是设立算学科的提议者。他还再三向清朝内阁各大臣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力陈科举采用科学的必要。丁韪良在《西学考略·自序》中也说:“中国倘能稍用西术于科场,增格致一门,于省会设格致书院,俾学者得门而入,则文质彬彬,益见隆盛矣。”1895年,李提摩太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应新增科目,他说:“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废也。惟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考西国读书,于可以为官外兼为益于各业而设。每十人中能作字者,率有七八人。中国仅一、二人。学者既少,人才益稀。盖由三年一科,取士太寡,专讲一门,其道太隘。若不立新法以广荣途,终瞠乎在人之后。应请明发谕旨,增设中西一科。每年每府取进中西学秀才约百人。每年每省中式中西学举人约百人。每年中式中西学进士约百人。每年殿试钦点中西学翰林十人。学费有限,济济多才,方驾大地矣。”
与此同时,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传授西学,对中国传统科举教育也形成了冲击和挑战,从而加速科举制的解体。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的建议和构想,就曾明显受到过西方传教士改革科举言论的影响。
变通科举的尝试
面对如此强烈变革科举的呼声,清廷也不得不开始变通科举制度。算学科的设立是晚清变革科举的首次重大举措。早在同治年间就有大臣提出设立算学科取士。同治九年(1870)五月,英桂上奏:“水师之强弱,以船炮为宗。船炮之巧拙,以算学为本……拟请特开算学一科,使家有其书,人自为学。”但是他的主张并未受到重视。光绪元年(1875)正月,礼部在《奏请考试算学折》中只是请求允许精通算学者参加考试,一体考试取中,“现在山林隐逸,以及末秩下僚中,如果有专精算学者,应请饬下京外三品以上大员,恪遵前旨,核实保荐,听候简用。其本系正途出身兼通是学者,即如该督等所请,别加优异,以示殊荣。若有资质明敏、愿学算法者,统归国子监算学照章学习。无论举贡生监及大员子弟,均准录取。其各省学政考试,仍一体录送科场,不阻其上进之路。总期由成法而得变化,即末艺而溯其本原,仰副朝廷造就人才之意。”但礼部又反对开设算学一科,“如此多设其途,较之特开一科尤觉鼓励奋兴,不至以实求而以名应,庶算学不难日益精密矣”。
至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江南道监督御史陈琇莹奏请将学习算学者归入科举正途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给予相应的科甲出身。陈琇莹在奏折中,首先陈述了设立算学科的必要性,他说:“西法虽名目繁多,皆权舆于算学。洋务从算学入,于泰西诸学,虽不必有兼数器之能,而测算既明,不难按图以索……可否仰肯饬下各该学政,于岁科试报习算学之卷,宽予录取。原卷咨总理衙门复勘,作为算学生员。届乡试时,除头场、二场仍试《四书》《五经》文,其三场照翻译乡试例,策问五题,专试算学,再照官卷例,另编字号,于定数外酌中数名,会试亦如之。”其次,陈琇莹建议给与算学科及第者出身。再次,陈琇莹提出将算学科及第者送往国外大学学习,学成之后回国任职,他说:“中式后,请予京职,遇有游历员缺,即令出洋赴泰西各书院学习。学成差旋,专充洋务及出使等项差使。”
军机大臣奉慈禧太后的懿旨,会同吏部、礼部以及醇亲王奕讨论,讨论结果是基本采纳陈琇莹的建议。之后,清廷批准了他们的讨论结果:“俟乡试之年,按册咨取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不分满、合、贝、皿等字号,如人数在二十名以上,统于卷面加印‘算学’字样,与通场士子一同试以诗、文、策问,无庸另出算学题目。其试卷由外帘另为一束,封送内帘,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于二十名额外取中一名,但文理清通,即为合式。如并无清通之卷,任缺无滥。卷数虽多,亦不得过三名,以示限制。”而会试则是仍然按另编字号的惯例,“至会试,向年另编字号之例,凡由算学中式之举人,应仍归大号,与各省士子合试,凭文取中”。这种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科举考试内容只考人文学科的局面,代表西学主要组成部分的算学终于成为科举考试的部分内容,这是科举制度在危亡时局下的一种突破性变革。
尽管如此,清廷并未将西学列入考试内容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只是试图通过将算学列入科举来应付日益强烈的改革呼声。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乡试,总理衙门将各省举送的监生及同文馆学生共计32名试以算学,仅录取一名举人,这既是中国近代第一名西学举人,也是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的唯一实际成果。次年恩科乡试,参加算学科考试者只有15人,没有人被取中。这些考生只能参加顺天乡试。此后,历次乡试时,皆因算学科应考者少而改应顺天乡试,算学科名存实亡了。
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清廷的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需通过改革科举,发展教育,破格选拔人才来缓解这场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翁同龢说:“当此时变,不能不破格求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贵州学政严修奏仿照康熙、乾隆年间开设的博学宏词科的方式设立新科目,主要选拔“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学律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并提出“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
严修的奏折受到清廷的重视。次年正月初六,总理衙门对此进行讨论,向清廷建议,经济特科的考试内容包括六个方面:“一曰内政,凡考求方舆险要、邦国利病、民情风俗者隶之。二曰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隶之。三曰理财,凡考求税则、矿产、农功、商务者隶之。四曰经武,凡考求行军布阵、管驾测量者隶之。五曰格物,凡考求中西算学、声、光、化、电者隶之。六曰考工,凡考求名物、象数、制造工程者隶之。”参加经济特科的考生由京官和督抚、学政保举,在保和殿进行考试,十年或二十年开一科。在特科之外,总理衙门还建议设立经济正科。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基本同意了总理衙门的议奏,只是要求“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以资观感”。
同年(1898)五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着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于三个月内,迅速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一俟咨送人数足敷考选,即可随时奏请定期举行,不必俟各省汇齐再行请旨,用副朝廷侧席求贤至意。将此通谕知之。”但同年八月,经济特科尚未实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在废止新法的过程中,以经济特科“易兹流弊”为由将其停罢。
戊戌变法时,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严厉抨击八股取士弊端,他说:用八股取士,即便能金榜题名,“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道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因此,他请求光绪帝立废八股文,然后再废科举,他说:“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故臣生平论政,尤痛恨之。即日面奏,荷蒙圣训,以八股为学非所用。仰见圣明,洞见积弊。夫皇上既深知其无用矣,何不立行废弃之乎?……特发明诏,立废八股。其今乡会童试,请改试策论,以其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事有用之问学。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
梁启超认为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迫在眉睫,他说:“中国所谓洋务学生者,竭其精力,废其生业,离井去邑,逾幼涉壮,以从事于西学,幸薄有成就,谓可致身通显,光宠游族,及贸贸然归,乃置散投闲,瓠落不用,往往栖迟十载,未获一官,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千金屠龙,成亦无益。”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梁启超请求清廷废八股文、试帖诗,他说:“特下明诏,宣布天下:令自丁酉、戊戌乡会试之后,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严复也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
根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奏请,五月初五日,清廷发布上谕:“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这是继康熙帝之后,清廷第二次下诏废八股文,并且规定科举考试改用策论。
同年(1898)五月十六日,张之洞、陈宝箴等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具体建议,不仅规定了三场的考试内容,而且还规定了每场录取名额。六月初一,依照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之奏,清廷发布上谕:“着照所议,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礼部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与此同时,光绪帝诏令改革武科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清廷下诏各省武乡试从庚子科(1900)始,武会试从辛丑科(1901)始,童试自下届科试起,均改试枪炮,废去默写武经一场。
八股文被废除之后,士人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新学,学风也随之发生改变,梁启超描述说:“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社会大众对于废八股文也是普遍认同的,《申报》记:“ 今岁五月初五日恭奉明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曰:八股无用,八股无用。”
当然,废止八股文也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废八股文诏令发布以后,守旧者大惊失色,甚至私下讨论,准备阻止此项改革,甚而有大臣联名请求恢复八股文。有的地方大臣根本不理会清廷的诏令,依然在主持考试的时候以八股文命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廷发布上谕斥责两广总督谭钟麟,“年逾七十,两目昏盲,不能辨字,拜跪皆须人扶持。粤东环海千里,武备尤重,该督到任后,首以裁水师学堂、撤鱼雷学堂为事,裁撤轮舟二十八艘,弃置不用。近日叠降诏书,举行新政及停废八股,该督考书院,故出八股题。学堂至今未立。其他商人禀请开矿筑路等事,则必阻之,全省有谈时务者,不委差使,吏士以此相戒”。不少长期习举业的士人也强烈反对,他们痛恨康有为,甚至有人想聚集起来去示威,甚至殴打他。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以后,立即中止了维新变法的几乎所有改革。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懿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九月十八日清廷再发懿旨,武举恢复原有考试内容,即考试刀、弓、石为主。维新变法以废八股文为核心的改革科举制度的各项措施尚未真正实施就宣告失败,科举又回到原有的轨道上,八股文起死回生。只是此时的八股文已病入膏肓,复活仅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正如欧榘甲所说:“及政变而八股文复矣,然不独聪明英锐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以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之为愈矣。”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科举
清末虽然在考试内容和考试文体等方面都作出了一些的调整,但都未能改变科举制度不能适应近代化需要,以及科举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弊端,科举的大变革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庚子事变之后的1900年11月,被《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称为西方人中“寓华最久知华最深”的“美国通儒”丁韪良曾说:“今为十九周之末年,明岁即二十周之元年。天意欲辟东方大新之局面。”身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些通古今之变的人士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大之一莫过于科举制度的停罢。
科举“新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清廷意识到改革科举、发展新式教育的紧迫性。不少大臣呼吁将西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两广总督陶模等人上奏,请求本年的乡试、次年的会试均按照光绪二十四年改革科举的方案实行,“倘以学校经营未易,收效需数年,国家求才正急,不得已而思其次,则请将本年乡试明年会试,暂遵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谕旨,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及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以《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同年三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则提出增加实学一科,将原有录取名额的二成用于实科,他说:“暂宜量为变通,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他建议采用渐进的方式减少科举的录取名额,他说:“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而实科亦必另作一途,仍归各省一律举行。”
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刘坤一上奏,请求在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勤游学四个方面进行改革,以育才兴学。其中在“酌改文科”方面,作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时期改革科举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他提出“拟即照光绪二十四年臣之洞所奏变通科举奉旨允准之案酌办”。在主张改革科举的同时,张之洞等人认为要逐渐减少科举录取名额,“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面对覆亡的危机和大臣们的极力呼吁,清廷于七月十六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布改革科举,内容几乎完全采纳陶模、张之洞等人的建议,直接将戊戌维新时期改革科举的举措照搬过来,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也要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至此,八股文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随着科举制本身在1905年被彻底废止,沿用500余年的八股文也就万劫不复,真正作古了。被清末人士深恶痛绝的八股文迅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且是一个十分丑陋的名词,后来“八股”几乎成为“迂腐俗套”“陈词滥调”的代名词。
这些改革主张随后得到实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补行庚子(1900)、辛丑(1901)恩正并科乡试,有12个省份开科,考试的内容是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策问,三场经义。试题内容明显向新学靠拢。
在改革文举的同时,也宣布废止武举制度。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十六日清廷亦发布上谕: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着即一律永远停止,实行了几百年的武举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
清末新政过程中,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恢复了戊戌变法时期的做法,废止了八股文,考试内容也增加了新学知识,有利于选拔实用人才,对促进新式学堂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上而言,科举制度还是很难适应清末社会大变革情势下兴学育才的迫切要求,要求停废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
除了改革科举,慈禧太后还宣布恢复经济特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阽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允宜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天下之广,何患无才,其有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着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出具考语,即行保荐。并着政务处大臣拟定考试章程,先期请旨办理。”
然而,上谕发布之后,地方官保荐并不积极,至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仅有广西巡抚黄槐森保荐了一人,前安徽巡抚王之春保荐了四人。为了使经济特科得到落实,清廷政务处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奏拟经济特科考试章程,要求有关大臣需要保荐素行廉正、不干清议者;京官五品以下,除京官翰林读讲科道外,外官四品以下,除现在实缺道府外,其余各员已任、未任及举贡生监、布衣,均准其获得保荐;并且规定,保荐者于本年十二月以前解送到京城。章程正式确定,经济特科分两场,第一场试历代史事论二篇,第二场试内政外交策二道。
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十日,内外大臣保荐者达370余人。闰五月十六日,考试在保和殿进行,参加考试的有186人,考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清廷派张之洞、裕德、徐会沣、张英麟、戴鸿慈、李昭炜、张仁黼、熙英8人为阅卷大臣。二十一日拟定梁士诒等48人为一等,桂坫等79人为二等,准予覆试。二十七日在保和殿覆试,第一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第二题是《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清廷派荣庆、张之洞、葛宝华、张英麟、陈邦瑞、戴鸿慈、李昭炜、郭曾炘等8人阅卷。录取袁嘉穀等9人为一等,冯善征等18人二等。正场录取者被淘汰了100人,其中正场一等的前5名仅录取了张一麟,梁士诒、杨度、李熙、宋育仁都落榜了。
尽管经济特科在考试内容方面作出一定的改革,不但考试内容更贴近现实,而且经济特科章程规定,字画无庸刻意求工,准许添注涂改,阅卷时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求形式。但当有传闻正场中取中的士子与革命党有牵连时,清廷大为惊慌,不但改换了阅卷大臣,大量削减取中人数,草草了事,仅仅录取了27人。这27人的授官情况也与康熙年间的博学宏词科有天壤之别,据《清史稿》载:“迨授官命下,京职、外任,仅就原阶略予升叙,举、贡用知县、州佐,以视康、乾时词科恩遇,寖不如矣。”录取的人数、录取过程中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介入以及及第以后的待遇等方面情况都显示出经济特科作为改革科举的重要举措是失败的,社会普遍认为:“现虽举行经济特科,不过招贤自隗始之意,止可为开辟风气之资,而未必遽有因应不穷之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