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卡文纳及其长诗《大饥荒》(节选)
桑克
我是实心实意觉得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文纳1942年写的长诗《大饥荒》能和艾略特1922年写的长诗《荒原》相媲美。这句话我几乎逢人就讲,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帕特里克·卡文纳是谁?著名歌手卢克·凯利唱过的《在拉格伦路上》就是他的诗:“在拉格伦路上在一个秋日里我和她第一次相逢,知道/她暗色的头发编织出一种诱惑,知道我将遗恨终生”。
你如果找不到卢克·凯利的版本,还可以到网上找其他人翻唱的版本,其中最著名的版本是女歌手欧拉·法隆唱的,非常好听。不多说了,你只要知道卡文纳是上接威廉·巴特勒·叶芝、下启谢默斯·希尼的爱尔兰诗人就行了。当然他写的诗也与那两位一样出色。
还有一个稍微详细的介绍,如果你觉得烦就跳过去。卡文纳1904年10月21日出生于爱尔兰莫纳亨郡的因尼斯基恩村。父亲是个小农场主和鞋匠。卡文纳13岁成为制鞋学徒,可惜只干了15个月。随后卡文纳种了20年的地。三十年代初,卡文纳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诗。1936年出版诗集《农夫和其他诗篇》,1938年出版自传《青皮傻瓜》。1939年卡文纳离开家乡来到都柏林——他自己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1942年出版《大饥荒》让卡文纳名声大噪。1947年出版诗集《待售的灵魂》,1948年出版小说《泰里·弗林》。五十年代,卡文纳和兄弟彼得出版《卡文纳周刊》,主要发表自己写的时政评论。1955年卡文纳切除了一个肺。1960年出版《来和基蒂·司托布林跳舞吧以及其他诗篇》。1967年和凯瑟琳·莫洛尼结婚,同年11月30日死于支气管炎,终年63岁。
为什么知道卡文纳的人不多呢?这个简单,因为他写的东西大多没有译成中文。这几年我一直忙这个,译了他的大部分短诗(即将与读者见面),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长诗《大饥荒》译成了中文。至于这块引玉之板砖成色如何还要请方家指教。
《大饥荒》是卡文纳代表作,素有定评。一般来说,它在世界文学尤其爱尔兰文学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都柏林大学戴斯蒙德·斯万说这首长诗是一首“独特的史诗”。伊万·博兰说它是卡文纳“最雄心勃勃的一首诗”,知道斯万和博兰的人不多,那就换一个人人皆知的谢默斯·希尼。希尼在一篇文章中称卡文纳“是一位具有纯粹精神力量的诗人”,“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人物”。他称《大饥荒》是“杰作”,它“把熟悉的死物踢进生活,把笨重的东西扔进旋转,诗中既有力量也有新鲜感,既有现实主义也有远见卓识。”厉害吧?还有一个社会文化指标:汤姆·麦金泰尔把《大饥荒》改编成舞台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点儿类似安德鲁·韦伯把艾略特的《老负鼠的实用猫经》改编成音乐剧《猫》的情形。顺便打个广告,我近来出版的《老负鼠的实用猫经》译本是中英文对照本,注释部分还是有点儿东西的。
《大饥荒》分为十四个部分。把“部分”译成“章”或者“节”都可以。不重要。这首长诗有多长呢?目测比《荒原》长太多了。《帕特里克·卡文纳诗汇集》的编者安托奈特·奎因说它759行,斯万说它765行。为什么相差6行?我笨寻思,可能是版本不一样的缘故。我手头有两个《大饥荒》版本,一个版本收录在《帕特里克·卡文纳诗汇集》里,另一个版本则是《大饥荒》的单行本。都是企鹅版。我认真数了数,都是759行。在斯万那里多出来6行的真正原因,他自己肯定清楚,只是我不知道罢了。这个问题我准备留置明年深究一番。
《大饥荒》写什么呢?写饥荒,而且是大的饥荒,没有粮食的生理饥饿,没有粮食的社会贫穷,错综复杂的政治,没有出路的欲望,贫瘠的土地与不公正……除此之外,奎因还说过:“《大饥荒》对读者来说是具有明显意图的说教诗。它有意识地颠覆了自从《抒情歌谣集》时代以来以乡村为基础的诗中普遍存在的原始崇拜,此外它还破坏了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勒拉设想的小农场乌托邦。”从来就没有如梦似幻的乡村乌托邦,有点儿狠是不是?奎因提到的《抒情歌谣集》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诗合集,它一向被认为是开了英诗一代风气的。说到底,奎因的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学者凯瑟琳·基尔科因在2012年《爱尔兰大学评论》中发表文章,并不赞成奎因的观点,认为他的“纪实”认识只是一种简化。卡文纳自己则说“《大饥荒》与穷人的痛苦有关”。实在倒是挺实在,不过仍是一家之言。标准答案从来就不是作者提供的。
《大饥荒》把读者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一个名字叫帕特里克·马奎尔的爱尔兰单身男人的身上。
单身男人——这才是重点。当然,此帕特里克并非彼帕特里克,不要联想。在爱尔兰叫帕特里克就如同在中国叫小强一样,很普遍。还有就是需要强调一下,诗中的我不可能总是现实中的我,尤其是作者本人。如果你把单身的马奎尔附会到单身的卡文纳身上就麻烦了。
与中国社会传统界定类似的是,这种没有结过婚的单身男人在爱尔兰社会传统中也是不能被称作“男人”的。应该称之为“男孩”。跟中国差不多。将这个置换到中国语境中还可以称之为“单身汉”或者“老光棍”,这也就是爱尔兰乡村常说的一个短语,the men’s the boys(男人中的男孩),不管男人岁数有多大,只要没结婚,在父母眼中就始终都是男孩。
《大饥荒》明显关注单身以及性欲方面的问题——在很多或显或隐的诗句里都能看到相关端倪——而且这些问题又与其他问题勾连在一起,比如土地问题与粮食问题,这就形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链。人类生殖与粮食生产在多种文化之中都具有同构关系。标题中的“大饥荒”明显与粮食问题相互牵扯,这让读者不得不联想起历史上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1845—1847),又称“土豆饥荒”或者“马铃薯饥荒”。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土豆染病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状况造成的,它直接导致100万人死亡,150万人逃荒与移民。卡文纳的这首长诗表面上与这场大饥荒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全诗看下来关联又是如此深刻。
不少学者将《大饥荒》纳入田园诗或者反田园诗的研究范畴。没错儿,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就是一个诗人写的一首长诗而已。诗人从他的经验与认识出发创造了一个含混而郁闷的马奎尔世界。卡文纳在接受一本杂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我是我们时代唯一从内部来写爱尔兰乡村的人。”这段译文来自学者刘庆松的专著《守护乡村的绿骑士:帕特里克·卡瓦纳田园诗研究》。他把“卡文纳”译成“卡瓦纳”是没有问题的。这本书值得读者关注。外交官丹尼尔·穆尔霍尔在一次演讲中,在引述完卡文纳的这段话之后,针对他的这一自我评价说“这是一个公正的评论”,然后丹尼尔又说,“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叶芝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是从外部窥探爱尔兰的乡村,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其理想化。”卡文纳说叶芝在爱尔兰的外面而且是理想化的,这个说法就有针锋相对的意思了。这也就是说,卡文纳认为自己不仅在爱尔兰的里面,而且是反理想化的或者是高度现实性的。果真如此吗?
诗人莫琳·加拉格尔在《帕特里克·卡文纳——是神秘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2013年3月《戈尔韦评论》)中指出:“在爱尔兰,有一种在凯尔特神秘主义神殿前烧香的趋势。帕特里克·卡文纳的诗长期以来就一直被用来为这些想法提供可信性。”这也就是说,莫琳并不赞成把卡文纳的诗全部归于神秘主义的说法。当然,我们早就知道影响力极大的叶芝和其他一些诗人一向服膺神秘主义或者玄学传统,势力甚大。
莫琳集中火力对准的是另一个学者乌娜·阿格纽的文章《帕特里克·卡文纳的神秘想象》。我能理解乌娜,更能理解莫琳。她们强调的点实在是不一样的。按照我对莫琳的理解,她认为卡文纳的诗主要还是源于缺乏保障的物质贫困和缺乏启蒙的精神贫困,正是由于这种双重贫困才剥夺了许多爱尔兰成年人的婚姻计划,而片面强调神秘主义则有可能淡化了真正的现实主义问题。这可能就是卡文纳与叶芝的根本区别,但是按照老说法说卡文纳只是现实主义的、叶芝只是神秘主义的,我也觉得并不十分妥当,因为卡文纳仍旧具有相当的神秘性。
诗人就没有不神秘的,但是我们此刻强调现实主义部分有其具体原因。对卡文纳来说,这与历史饥荒有关,也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爱尔兰现实有关。卡文纳笔下的《大饥荒》还可以译成《大饥饿》。饥荒强调广度,饥饿强调感受,侧重点不一样。只不过我此刻更倾向于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判断而已,而换一个时间我可能就会把译名改成《大饥饿》。从全诗观察,粗看满篇都是生理饥饿和精神饥饿,细看处处都是政治饥饿和道德饥饿的幽魂。
《大饥荒》的写法与艾略特《荒原》的写法同样复杂,它不仅包含各种经验(尤其乡村经验),也包含对爱尔兰文化各种层面的精心处理。厉害的是,它并不直接书写肚皮饿得咕噜响,而是着重书写粮食和人。这里的粮食就是当时爱尔兰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土豆。土豆/马铃薯是卡文纳的目标靶心之一:“用四齿叉搂起枯茎,注意不要让土豆/从后挡板掉到不平坦的通道上——”(第1节)“然后他在土豆堆上鹿一般蹦蹦跳跳,/把土豆捡到筐里。”(第12节)“帕特里克·马奎尔,这个老农民,既不该死,也不值得吹嘘:/他即将安息的墓地只会是一块深耕过的土豆地”。(第14节)
卡文纳没有像电影《都灵之马》那样细致地描绘农民每天吃土豆的情景,而是把土豆置于全诗各个角落。它既是氛围构成,又在时时暗示土豆与饥荒的表面勾连。因为真正的饥饿或者具有杀伤力的饥饿另有构成,比如土地的饥饿——土地的贫瘠造成了社会的贫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大饥荒》从十月起笔又终结于十月。左看右看十月都具有特殊性,无论文本还是内涵。即便对十月问题不加深究,只从起始周期来说,还是能够看出这是一个略带神秘的逻辑闭环,这与斯万指出的卡文纳在诗中始终遵循的“情感运动”模式极为相似。“情感运动”模式基本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从一个消极记录开始,关键词是“消极”;第二个步骤是将消极记录上升为对美好事物的期盼与希冀,关键词是“美好”;第三个步骤也就是最后,是重新回到消极甚至绝望的状态,关键词是“消极”。“消极”-“美好”-“消极”,这种“落-起-落”的逻辑闭环模式恰恰反映出老光棍马奎尔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挣扎与绝望。
而马奎尔消极的个人命运是从土地开始的——黏土是道,黏土是肉身,/土豆采集者好像机械化的稻草人/沿着山坡移动——马奎尔和他的人。(第1节)
这是《大饥荒》开头三句。在初译稿里,我将“道”译成“词”。“黏土是词,黏土是肉”。黏土与爱尔兰关系密切,可以说它是爱尔兰土地的核心特质。我个人认为这句诗指出了黏土的双重性质,一个是精神性的“词”/语言,另外一个是生物性的“肉”/肉体。词与肉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爱尔兰人和土地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早已渗透在爱尔兰文化传统和社会传统之中。如果我们想要比较透彻地理解爱尔兰人,首先就要理解“黏土”/土地这个关键词。面对叶芝或者卡文纳的诗,这一点非常必要。后来在和翻译家少况的交流中,我获得极大助益。他建议我将“词”译成“道”(随后相应地把“肉”调整为“肉身”)。这样或许更能体现卡文纳对性与灵性的双重关注。“马奎尔和他的人”,说明马奎尔是一个小农场主,有自己的人/雇工,所以他的性悲剧和土地悲剧比一般雇工更能说明问题。而且这种悲剧中还带有一种批判性的滑稽成分,卡文纳在《作者手记》里说:“《大饥荒》是悲剧,而悲剧是有待发展的喜剧,并不是天生的。”喜剧萌芽就在悲剧泥土里。
“世界看着,/谈着农民:/农民没什么可担心的;/在小小的抒情田地里,/他犁地,播种;/他吃新鲜的食物,/他爱新鲜的女人,/他是自己的主人;/在开始的时候,/农民生活是单纯的。”(第13节)马奎尔作为农民代表,他的生活就是农民生活的样本,虽然他的老光棍生涯并不具备完全的代表性。其实这也是奇怪而特别之处,一个为土地繁殖而工作的人,自己却没有繁殖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对比反差之强烈恰恰可以证明问题的严重与悖反,恰恰可以说明悲剧的程度之深。“没有农民之基,文明必死”,这是长诗的核心之一。它高度强调农民/农业对于文明的基础作用,甚至说“农民是没被损坏的先知的孩子”,这为读者理解马奎尔的形象起到了部分纠正与校勘之用。在这种基础上进行的批判会更深刻,读者的同情之心也会油然而生。
马奎尔对于女性的无用性是值得同情的。他被土地牢牢困住也值得同情。他面前摆放的这条“软弱而苍白、真实而不幸的道路”正是被卡文纳认定的《大饥荒》的精髓所在,而这条道路却是“一匹拱着周边草地的病马正找一个干净之地去死”。马奎尔虽是病马,但是他仍旧把自己的终局之地设定为“干净之地”。这是他关于最终获救的想象。
《大饥荒》塑造的马奎尔形象是卡文纳对世界文学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这一形象又清晰又复杂。清晰的是光棍汉形象,复杂的是它的构成。
对于这一类爱尔兰光棍汉,卡文纳的诗句向来锋利而深刻。比如“男人们大步跳过犁沟,/迷失在从来不需要一个妻子的激情中”。没有妻子的单身生活会形成一种“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自我暗示,而这种自我暗示又分明具有自我欺骗的成分。再比如“他现在不确定妈妈是对的,/当她赞美一个把田地当作新娘的男人的时候。”“把田地当作新娘”这句非常精彩,一方面表明马奎尔对土地的钟爱,另一方面则体现出马奎尔母亲对他单身的讥讽。马奎尔自己的“不确定”则意味着他对单身生活终于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的生理欲望并未死透。
马奎尔的性状态与性心理,诗中都有暗示与明示。比如“他大腿上待着一条无能的虫子”,暗示他的性无能。比如“但是他的激情变成了一场瘟疫,/因为他变虚弱了,他携带着模糊的/渴望接近的心目中的女人,/至少每一周肉欲都必须出现那么一次。”以一周为周期的肉欲如何解决读者只能猜测与想象。比如“马奎尔厌倦了/冲没有靶子的目标开枪,/回到胡萝卜和卷心菜的地头,/再次来到太监也能成为男人的田地里,/生活比野蛮更糟糕。”这类表现自慰和土地贫瘠的诗句曾经被迫删除。这与《尤利西斯》的出版命运极为相似。当时爱尔兰警方根据1939年《紧急权力法案》认为《大饥荒》的某些诗句“淫秽”。虽然出版《大饥荒》的库拉出版社逃过一劫,但是《大饥荒》仍旧难逃被删改的命运。
这种删改就是鲍德勒化。库拉出版社是叶芝的姐姐利莉·叶芝和罗莉·叶芝创办的。她们帮了卡文纳大忙。
“再次来到太监/也能成为男人的田地里”,土地贫瘠犹如没有生殖能力的男人。这是《大饥荒》的诗眼之一。“太监”这个词的出现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自慰至少还保有单身汉解决性欲的基本方式,而“太监”则将这种方式彻底否决与取消,等同于阉割。由此可以判断出马奎尔的生活底色,同时也可以判断出田地/土地的贫瘠如同太监一样没有任何创造力。没有粮食创造力的土地和没有生命创造力的人才是《大饥荒》的真正来源,而性饥饿又常常被粮食饥饿所遮蔽,所以莫琳·加拉格尔才会说:“忽略《大饥荒》实际上是指性饥饿这一事实——自始至终涉及化成死灰的孤独自慰——也是在加剧失明。”没有创造力的生命,只有精神失明的人才看不见这一残酷的事实。《荒原》描绘文化与社会绝境,《大饥荒》则显示类似绝境的历史特征和生理特征或者生理基础。
在与女性艾琳的关联描述中,马奎尔的道德自律看起来更像无能的借口。在第四节里,卡文纳还写到一个提筐的姑娘。这个姑娘是艾琳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马奎尔对这个姑娘的欲望非常真实,当然也可以说是“非常真诚”,但是结局仍以他的退缩和姑娘的消失而告终。因为马奎尔认为这里的“原罪比约翰·班扬梦见的还大”。他的犯罪感多奇怪。卡文纳在第七节里提到的艾格尼丝比“提筐的姑娘”更重要,不仅因为她有明确的名字,而且还有更具诱惑力的动作,“湿草地永远不能冷却从她/多余的子宫里辐射的火焰”。这意味着爱情或者肉欲的力量是惊人的。马奎尔不仅面对自己的肉欲,也面对具有攻击性的外在力量。试看普天之下谁能挡得住人性的偷袭?肉欲也是人性一部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马奎尔的欲望解决方式还有两种,一种是摸牛,“代替妻子的处理”具有暧昧的混乱意味;另外一种是环绕田地跑步,用这种方式降低欲望温度也是比较常见的。
马奎尔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黎明的鹬鸟掉下来好像一块呼呼响的石头”,这句比喻非常精妙,映衬出马奎尔的孤独和寂寞。马奎尔在大风中劳动,土地则如同“处女”反抗强暴那样在大风中挣扎着。此外,马奎尔也是有小快乐的。比如他“最快乐的梦”是在小溪边擦屁股,还有抽烟斗。在第八节里,马奎尔坐在木门上的场景好像电影画面。我们看见他表面的自由,唱歌、抽烟与喝酒。这些本已近于完美,但是“年轻的女人们一路狂奔,/梦见一个孩子”,女性的魅惑和生殖的愿望还是将马奎尔所谓完美的背后缺陷显示了出来。他过的就不是完整的人生。更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她们松开扣子的裙子,/故意松开的扣子。”深入的细节足以要了老光棍的小命。马奎尔主观地想要凭借“呼唤”“神”拯救自己,行吗?看起来理由充分,这“是必要的痛苦/而不是扼杀真爱的绳子”,他能真正地说服自己吗?
三十四岁或者三十五岁的时候,谎言可能是管用的,但是现在呢?当卡文纳的母亲死去之后而他六十七岁的时候呢?这谎言还能像木门一样支撑他的身体和灵魂吗?唱,笑,“开着白日梦的汽车”,“用膝盖卡住自己的身体”,管用吗?“欣喜若狂”是真的吗?自我陶醉还是自我麻痹?
马奎尔是一个矛盾体,他似乎洞悉真相,但又为这真相的原因进行着无力辩解。
第九节表现以前的生活。马奎尔仍旧没有办法解决难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新的一年里给自己一次机会。“一个新节奏就是一种新生活”,看起来不错,但在这种新节奏和新生活里,“婚姻高高挂起”。还是没有婚姻。新生活的本质还是旧生活,而且经济状况令人堪忧,“……婚姻高高挂起,还有钱”。那么四十七岁的状况又会怎样?第十一节第二段和第三段的劳动场景非常细腻,几乎像电影一样。马奎尔的面貌、体态和声音都在读者眼前呈现出来。他的佣工乔自言自语的样子既可爱又可怜。第四段表现马奎尔内心之中来自学生妹的性幻想以及自我惩罚。诗人将这种惩罚的法律或者宗教律条的相关言辞巧妙延伸到第五段的教堂事务,有点儿像蒙太奇或者词语接力。第八段是马奎尔看着雏菊回忆自己的童年,并且想象雏菊后面是否藏着一个仙女。经验与思考并峙。第九段是马奎尔的善行,帮穷女人和醉鬼,而聆听年轻人的声音又该怎么理解呢?第十段比较重要,表现马奎尔的善和愚,也表现他的逆来顺受,“感谢安排这些事情的上帝”。这段对理解马奎尔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几乎就是一把万能钥匙。第十一段的反问是卡文纳自己的判断。马奎尔本人也许不会这么想。
马奎尔的签名在“诗人和妓女之间”。这是有意味的。奎因认为“妓女”一词是印刷错误,我认为不是。诗人是捍卫灵魂的人,妓女是出卖肉体的人,词义对立反差非常之大。马奎尔居于中间,恰好表现他在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挣扎状态。马奎尔居于中间,但还是稍稍偏向于“妓女”一面,所以斯万才指出马奎尔的日常生活与“卖淫”之间具有某种联系。是出卖肉体吗?还是对不起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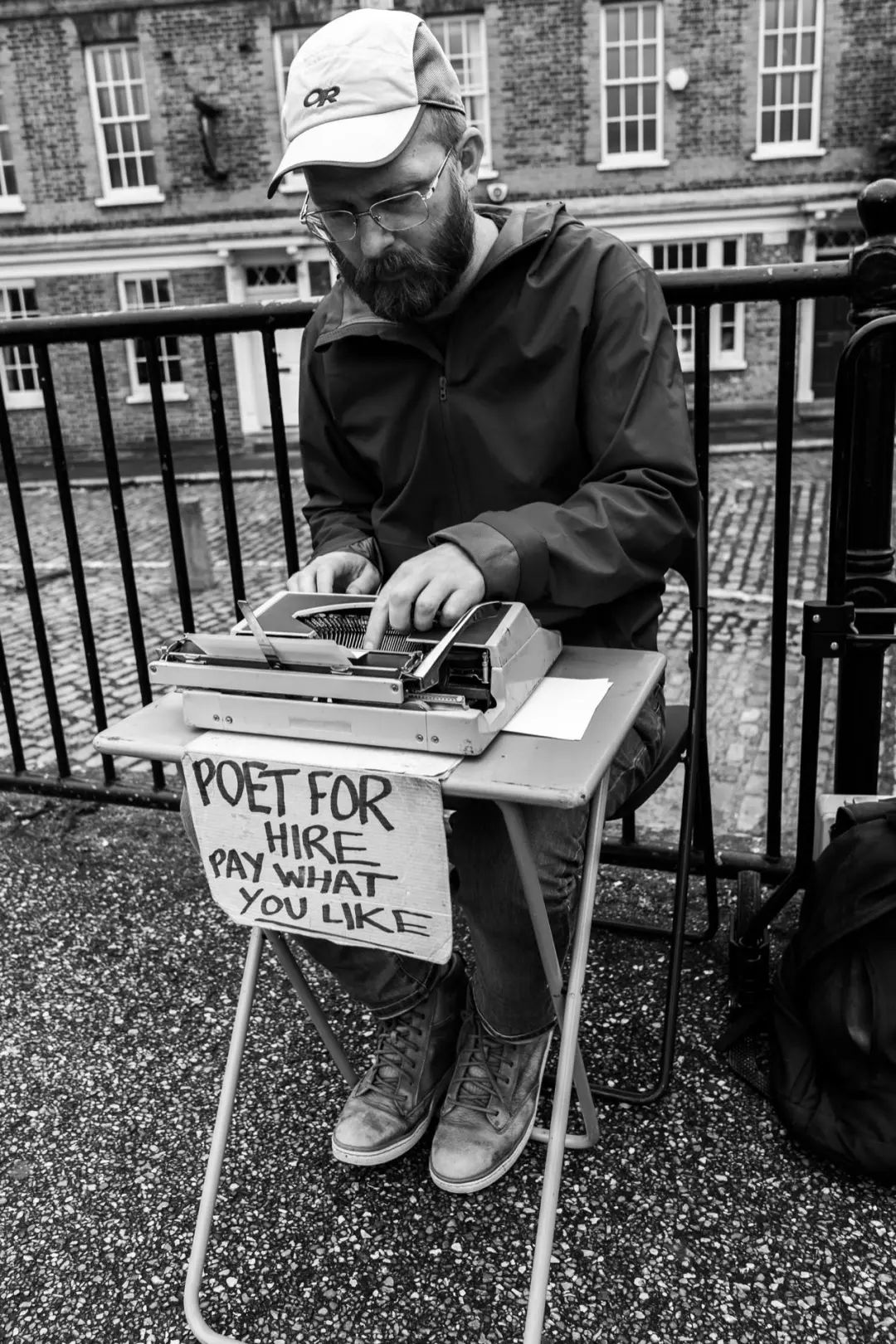
附:
[爱尔兰]帕特里克·卡文纳
1
粘土是道,粘土是肉身,
土豆采集者好像机械化的稻草人
沿着山坡移动——马奎尔和他的人。
如果我们盯住他们一个钟头,我们就能证实
如同《死亡之书》折断脊背一样的生命到底是
什么?幸运的是乌鸦在虫子和青蛙上面急促而含混地嘟囔着,
而海鸥则像旧报纸一样从树篱上被吹得干干净净。
潮湿的土块里有想象的光芒吗?
或者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发抖?
这些人中的谁
爱着光芒和过于贞洁的
女王?昨天还是夏天呢。谁对自己承诺结婚,
在万圣节的苹果挂在天花板上之前?
我们会等着看最后一幕悲剧,
直到最后的灵魂好像一袋潮湿的粘土被动地
滚下山坡,又被犁铧错过的或者铁锹站立的
角度改变了方向,把路变得窄窄的。
一条狗趴在翘起的马车下面的破夹克上,
一匹马沿着花束丛生的地头小心翼翼地走着,
拖着生锈的犁。三颗脑袋悬在相距甚远的
两腿之间。十月在松弛的铁丝围栏之上演奏着交响乐。
马奎尔看着田垄磨平了,
燧石在一处没有火焰的六月祭坛上为他点燃了
蜡烛。田垄滑过去了,日子滑过去了,
他抖开脑袋,从这世界的缰绳之中自由地跑了出来,
当他喝着一品脱波特酒,嘲笑着,
还有自己如何从播撒于经验缝隙的网中
自由挣脱出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比城镇的任何人
都聪明。他摇了摇聪明的脑袋,
他假装对自己的灵魂
在四月仓促之田里的孩子们感到厌烦,
男人们大步跳过犁沟,
迷失在从来不需要一个妻子的激情中——
刺痛的刺是耙子上尖锐的钉子。
孩子们大声尖叫,乌鸦带走了
一英亩的种子,还发出粗鲁的奚落声。
帕特里克·马奎尔,喊他的狗,往空中扔了一块石头,
赶走了多年以来一直驻扎在这里的鸟。
翻开杂草丛生的土块,梳理纠缠在一起的一束东西。
他在那儿找到了什么?
他以为它是一颗土豆,但是我们比探究
懵然不知的植物茸毛之泥手套里的手指头更明白这个。
“往前移筐,把它放在坑里
保持稳定。放下马车操作柄,乔,
骑到马上去,”马奎尔喊道。
“吹过布兰纳甘家的风,意味着现在就要
下雨了。
用四齿叉搂起枯茎,注意不要让土豆
从后挡板掉到不平坦的通道上——
那就是我们在十二月里必做的一份工作,
在沼泽地边缘铺碎石子,修马路牙子。用我的三叶草
遮一下卡西迪的屁股吗?这是神的诅咒——
狗在哪儿?
从来不在它需要之处。”马奎尔嘟囔着吐口水,
透过挂着粘土的胡子,从高处凝视着它。
他的梦想再次发生改变好像摇晃云朵的风
他现在不确定妈妈是对的,
当她赞美一个把田地当新娘的男人的时候。
看看他,看看他,山上男人的灵魂
就是一只拍打着时间膝盖的湿麻袋。
他活着就让他的小小田地保持着肥沃,当他的身体
铺展在两副以基督名义交叉的犁刀之下的沟底的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多疑,好像接近奇怪面包的耗子,
这时候姑娘们笑着,姑娘们尖叫着,他知道这些意味着
发情的小牝马的叫声。他不会走上
通往他命运的坦途。他梦见
嫩荆棘的天真成为上瘾的欺诈。
噢,掌握,噢,不规则田地的掌握!没有人能够逃脱。
不可能是因为群山之脊,爱是自由的
而沟渠直挺挺。
没有一个怪物的手举起了孩子放下了猴子
就像这里一样。
“噢,上帝,如果我变得更聪明一点儿”
他的叹息声好像蓟丛里褐色的微风,
他望向他的房子和院子,“噢,上帝,如果我变得更聪明一点儿”
而今一片皱缩的树叶从山楂树丛里
飞奔而出好像一只受到惊吓的知更鸟,篱笆
透过一扇小窗露出再生之草的绿色,
他知道自己的心正在呼喊着妈妈是一个撒谎的人,
上帝的真理就是生命——即便他最肮脏的火焰有着奇怪的形状。
马抬起头而鹤
穿过荆豆和石头
在满地乱爬的三叶草里亲吻着迟来的感情。
在堆着沉重的好像道德一般的巨石的灌木缝隙里,
生活的傻瓜如果爬过去就会流血。
风从布雷迪家倾泻而下,款冬叶的窟窿眼儿里全是铁锈,
雨水灌满了车辙和底盘形成的凹槽;
一轮黄太阳反射着多纳赫莫因
马蹄踩出的水坑里悲惨的光茫。
想象,跟我来吧,走进这座房子,
我们会在门口看见时光倒流,
我们也会知道一个农民的左手在纸上写着什么。
十月,放轻松。没有咯咯叫的母鸡,马嘶声,树的沙沙声,鸭子的嘎嘎声。
(桑克 译)

发表于《当代·诗歌》2024年第6期
2024年《当代》创刊45周年之际,推出诗歌版,即《当代•诗歌》,立足中国诗歌的当代书写,以对国内、国际诗坛的兼容并蓄,尽显当代诗歌的活力、重力、实力、魅力。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当代·诗歌》衷心期待得到文学界同仁与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关注与批评指正。
全年六期,每逢双月出刊
每期定价:25.00元
全年定价:150.00元
邮发代号:80-561
订购《当代·诗歌》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当代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