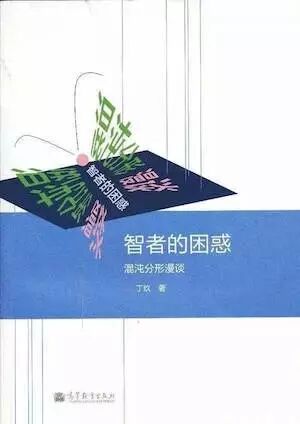
《智者的困惑:混沌分形漫谈》
本文节选自丁
玖
著《智者的困惑:混沌分形漫谈》第4章,该书已在赛先生书店上架,点击文章底部“
阅读原文
”购买此书。
天气预报是个古老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天都要看看天气预报以决定出门是否带伞。远古时代的天气预报大概主要是靠猜想或者根据经验,故传统的方式不太像科学,更像感官性的一门技术。现代天气预报基于求解描述大气运动的微分方程组。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能够预报中长期的天气走向。如果能知道明年的今天天气是怎么样,那该多好啊。但是中央电视台的天气报告员就要伤心难受,因为饭碗可能就要丢掉。长期天气预报这个科学幻想小说中可能描绘过的美好前景能够实现吗?
二十世纪在非数学的领域中对全人类可能贡献最大的纯粹数学家冯·诺依曼是天气预报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非常短暂的五十三年寿命最后的几年当中,拉普拉斯发扬光大的牛顿式决定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他智慧的大脑,认为描述天气的方程就像描述行星的方程一样,都由牛顿力学所确定:既然彗星能被精确预见多少年后会再次光临,天气为什么不能被精确地预报呢?不光如此,他满腔热情地展望,随着大规模科学计算的可能性跟随着计算机的不断发展接踵而至,人工控制天气的美好时代也将会随之到来。
天气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物理过程,但它被流体力学的基本定律支配着。天气预报依赖的是求解对应的偏微分方程组,它们的解是温度、气压、风速等这样的函数变量,而它们以时间及其地球表面上空一定高度内所有点的三个坐标数作为自变量。要确定从某个初始时刻起以后依赖于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天气变化的方程解,我们必须知道在那个初始时刻的温度、气压、风速等的空间分布,而这些初始数据可以通过密布全球的观测站收集。所谓的数值天气预报,就是数值求解偏微分方程组离散化后的代数方程组。可供观测的资料越多,这些方程组的尺寸就越大,天气预报的准确度也就越高。但这在现代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的几百年间是难以做到的。
从冯·诺依曼五十年代初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造出第一台现代计算机,他就立下矢志,让越来越强大的电子计算机成长为一位“人造的英雄”,为天气预报以及更进一步控制天气发挥重要作用。真可惜,他万万都没有想到,操纵天气变化的微分方程内在的特性即将扮演着一个反英雄的角色,让他所有的雄心壮志化为乌有。
发现这位反英雄的是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Norton Lorenz, 1917—2008)。
洛伦茨1917年出生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康涅狄格州西Hartford市,从孩童起就是一个气象迷,每天都在他家房子外面注视那个测量气温的温度计上的记录。他先后在达特茅斯学院和哈佛大学学数学,1938年获得前者的数学学士学位,两年之后拿到后者的数学硕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2年直至战后的1946年,他如愿以偿地成为美国空军的一名气象预报员。二战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学校读书,兴趣自然转向到气象学研究,故决定学气象,并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这个领域的两个学位,包括1948年的博士学位。他最终成了这所名校的气象学教授。
从战争的经历中,洛伦茨就清楚地知道天气预报对于空军作战胜利的至关重要性。1944年6月“D-Day”的欧洲战场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那几天关键的“恶劣天气间有十几小时的好天气”的精确天气预报是无名的英雄,当然它的盟军最高指挥官、美国未来的第三十四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
)是众所周知的有名的英雄。尽管短期天气预报已经基本上令人信服,然而,那个时代的中期天气预报准确性依然不尽如人意。现实背景让洛伦茨毫不奇怪地把“大气”纳入他的研究版图。在他漫长的科学生涯之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气象科学先驱之一、出生于瑞典并且最终也在祖国首都去世的卡尔-古斯塔夫·罗斯比(
Carl-Gustaf Rossby, 1898—1957)
对他的研究之路深有影响。在著名的挪威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维尔海姆·比叶克尼斯
(Vilhelm Bjerknes, 1862—1951)
用于气候模型的原始方程激励下,罗斯比和其他气象学家曾经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动态大气模型。
1960年,洛伦茨选择数值天气预报方程时,选取了十二个微分方程来决定十二个变量,用计算机来模拟天气,并已注意到这个微分方程组具有非周期解。但是一打方程,对于当时的计算机计算起来还是有点多。最后,他决定从美国耶鲁大学的青年地质及地球物理教授巴里·萨尔茨曼
(Barry Saltzman, 1931—2001)
最终于1962年发表的论文中所研究过的一组七个方程中挑选出三个。这些方程描绘流体的对流运动,即受热流体的上升运动,就像当我们夏天走在被太阳烤热的柏油马路上看到的冉冉升起的气流那样。这三个方程组成的系统尽管是非线性的,却是十分简单的非线性,只有变量的二次项出现,并能对他所制造的“玩具天气”令人信服地模拟。
1961年冬季的一天,美国东北部寒冷的天气似乎也在等待一个科学的春天到来。洛伦茨教授像往常一样地走进他任教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系的办公室,继续用他的那台Royal McBee公司制造的简陋计算机来计算与天气预报有关的那三个简单非线性微分方程的初值问题的数值解。
这一天,与往常一样算了一阵子之后,为了休息一下,洛伦茨暂停了计算,只是把计算机终端上的数据抄了下来,作为再次计算的初始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他穿过大厅下楼喝咖啡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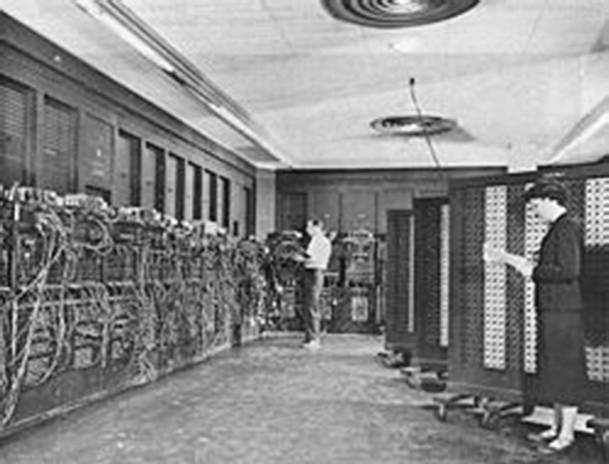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从左至右依次为:洛伦茨、罗斯比、比叶克尼斯、萨尔茨
一小时之后他回到办公室,十分吃惊地看到计算机并没有精确地重复老结果,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照理说,程序一样,初始值一样,输出结果也应该一样。难以理解的是,他发现新的计算结果同上一次的计算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偏离,面貌全非。不到几个“月”时间,“天气”完全不一样了。严谨而又细心的他将信将疑地重新算了几次,类似的现象在反复试验中总是出现。他的脑海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计算机坏了。
但是,计算机完好无缺。一刹那,洛伦茨明白了。这个伟大的理解,借用美国科学记者格莱克的语句,“播下了一门新科学的种子”。他这个无意之中的收获,表面上虽属偶然发现,好像一个人们常常经历的随机事件,本质上实属必然结果,纯粹是水到渠成。造福全人类的英国细菌学家、1945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得主之一亚历山大·弗莱明
(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
1928年秋培养细菌时偶然发现盘尼西林的历史一幕又在美国重演了。
原来,计算机内存中的数据保持六位小数,输出时为了节省空间,只打印了四舍五入后留下的三位小数,比如0.123456打成0.123,0.456789打成0.457。他喝咖啡前抄下的数据只有三位小数,与旧的计算结果仅仅相差不到千分之一,而将其打进计算机作为再次计算的初始值,新的计算结果和原先预期的计算结果就会大相径庭,这真是奇怪的现象,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悖。
通常的观念是:小的输入误差导致小的输出误差。这是一切物理、几何测量的依据。任何测量都有误差,但只要误差足够小,结果就应该足够精确。譬如要算出一个正方形的面积,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边长量得足够仔细,算出的面积就足够令人满意。
但是,小的输入误差也会导致大的输出误差。如果我们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月亮上的一个物体,望远镜仰角极小的增加就会把我们的视线落在月球表面另一个相距甚远的目标上。这是因为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作为角度测量误差导致弧长计算误差的“放大因子”,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放大因子不太大,持续不断的放大也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让我们做个简单的数学实验。随便取一个0和1之间的数,加倍一下。如果结果还在0和1之间,就得到下一个数,再做同样的事;如果结果比1大,就砍掉它的整数部分,得到下一个数,再做同样的事。如此周而复始,给出一个无穷迭代过程,所有的迭代点都落在0和1这两个数之间。
这个迭代产生的数列的每一个数都是前一个数乘以2,再去掉结果的整数部分。比方说,如果第一个数取为
 /8,后面依次
/8,后面依次
 /4,
/4,
 /2,
/2,
 -1,2(
-1,2(
 -1),4
-1),4
 -5,8
-5,8
 —11,等等。如果第一个数有了1%的小误差,那么第二个数的误差就加倍为2%,第三个数的误差大到4%,以后依次增加到8%,16%,32%,64%等等。我们看到,第七个数的误差是初始误差的
—11,等等。如果第一个数有了1%的小误差,那么第二个数的误差就加倍为2%,第三个数的误差大到4%,以后依次增加到8%,16%,32%,64%等等。我们看到,第七个数的误差是初始误差的
 倍。每次都放大一倍的数量递增会迅速地增加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就像乔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 1904—1968
)在1946年初版的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
One, Two, Three
...
Infinity: Facts and
Speculations of Science
)中一开头那个智者戏弄富豪的“大数故事”所讲的那样。写了许多优美科普书籍的杰出物理学家伽莫夫生于俄国,后来移民美国,常与好朋友乌拉姆讨论与无穷大有关的科学问题。
倍。每次都放大一倍的数量递增会迅速地增加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就像乔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 1904—1968
)在1946年初版的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
One, Two, Three
...
Infinity: Facts and
Speculations of Science
)中一开头那个智者戏弄富豪的“大数故事”所讲的那样。写了许多优美科普书籍的杰出物理学家伽莫夫生于俄国,后来移民美国,常与好朋友乌拉姆讨论与无穷大有关的科学问题。
洛伦茨在他的计算中看到了这种“对初始值的极端敏感性”。他终于领悟到这一异常现象根植于天气预报所依赖的微分方程组的这个内在特性,而不是什么计算过程中的舍入误差在作怪。后来,在其1995年出版的《混沌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Chaos
)这本有中文译本的书里,他再一次回忆到自己当时的想法:
“如果实际大气的形态像这一简单模式的话,那么长期天气预报将是不可能的。温度、风以及其他和天气有关的量,确实不能精确地测量到三位小数。即使能够这样,但在观测点之间进行内插也不能达到类似的精确度。我有些激动,并且很快将我的发现告诉了一些同事。最终,我确信小的差别的放大是缺乏周期性的原因。”
洛伦茨由此得出结论:
“一个确定性的系统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表现出非周期的性态。”
洛伦茨把他的发现和分析写成了论文“确定性非周期流”,发表在美国气象学会的《大气科学杂志》(
J
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1963年的第二十卷第二期上。他的如下断言无情地击碎了幻想长期天气预报一劳永逸的美梦:
“由于天气观测存在自不待言的非精确性和不完全性,长期、准确的天气预报将是不可能的。”
日后,洛伦茨把这一现象形象地比喻成“蝴蝶效应”,用在了他1979年12月29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题目:“可预见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
就凭洛伦茨创造出的蝴蝶效应这一混沌科学定义的形象提法,他就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当代科学普及大师的行列之中。有多少严谨的科学家能把深刻的科学发现像立体电影似的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芸芸众生的眼前,令他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洛伦茨就能!他的蝴蝶效应甚至在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里也引起一连串的派生效应。例如,在百度的百科网页上就能读到这样的说法:
“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伽莫夫
(左)
、《从一到无穷大》
(右)
中国这些年房地产业的狂猛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或许能给上述断言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喜欢一睹中国斯诺克台球名将丁俊晖(1987—)比赛风采的人也可以从圆球与桌面边界四周撞击的轨迹中领略蝴蝶翅膀的洛伦茨效应。只要丁俊晖击球杆的运动方向有一丝丝的小改变,几经反射后的球的最终目标就可能让他夺冠的希望扑空。“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应该是丁俊晖容易记住的一句成语了。由于台球的几何运动轨迹基于非线性函数的迭代理论,非线性分析中就多了一门数学分支:台球动力学(dynamical billiards)。在这个领域,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任教的俄罗斯数学家、在确定性动力系统和概率随机系统之间建造了一座桥梁的建筑大师雅科夫·西奈依(
Yakov G. Sinai, 1935—
)以他用来刻画气体热力学性质的“西奈依台球”模型著称。它的几何形状只是挖去了中央圆盘的一个正方形,但是其台球动力学则具有丰富的数学内容。有趣的是台球健将们一般不懂台球动力学理论,而这个理论的行家也大都不会打台球。
 蝴蝶效应(左)、《大气科学杂志》(右)
蝴蝶效应(左)、《大气科学杂志》(右)
天气预报的蝴蝶效应由于格莱克1987年的那本面向大众的国际畅销书《混沌:开创新科学》而成为路人皆知的一个形象说法、一个专用名词。现已在该校退休的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的坦普尔·费(Temple H. Fay, 1940—)教授找到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在平面极坐标系中画出的图像看上去是一只美丽绝伦的蝴蝶。他的漂亮作品发表在1989年5月期的《美国数学月刊》(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上(喜欢收集蝴蝶标本者以及美术爱好者可见维基百科网页)。
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saixiansheng
@zhishifenzi.com
您可回复"年份+月份"(如201701),获取指定年月文章,或返回主页点击子菜单获取或搜索往期文章。
赛先生为知识分子公司旗下机构。
国际著名科学家文小刚、刘克峰担任《赛先生》主编。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赛先生”。
微信号:
iscientists

▲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