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编身边好几个微信群都再次被「上四休三」的探讨刷屏。
先是日本东京都政府宣布,将于2025年4月启动「上四休三」试点,允许员工通过弹性工时实现更多休息时间,希望借此缓解低出生率的社会难题。这一政策迅速在日本国内引发热议,支持者与反对者争论不休。
再是上海市人社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生育友好岗」的试点通知,鼓励用人单位通过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灵活休假等方式,帮助职场父母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推动「工作友好型」文化的构建。
12月18日,携程集团也跳入了「上四休三」的浪潮中。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示,携程正在探索四天工作制,目标是让灵活工时既不影响效率,还能显著提高员工的幸福感。这一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有效——混合办公两年来,员工离职率下降了30%。

一时之间,「上四休三」再次被推向舆论的浪尖。而在这个热议话题里,传媒行业,似乎格外有发言权。毕竟,这个行业本就以「弹性」闻名——
不用打卡、随时随地办公、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这些特质似乎让传媒行业天生适合成为「上四休三」的试验田。
但这个标签,真的名副其实吗?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小编特意和几位已经实现「居家办公」或「自由职业」的朋友聊了聊。结果,听到的却并不是满怀欣喜的认可,而是批判与厌倦。「整天在家,工作变成了全天候,累得不行」,「节奏不规律,反而打乱了生活」……这样的抱怨屡见不鲜。
反倒是目前在大厂做产品的前同事,对「上四休三」表现出了更多的期待——少了通勤的麻烦,多了旅行和社交的可能,生活或许真的会更自由一些。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一个表面看上去与「弹性」高度契合的行业,为什么在面对「上四休三」时,展现出的却是这样的反差?
今天,小编想和你展开聊聊「上四休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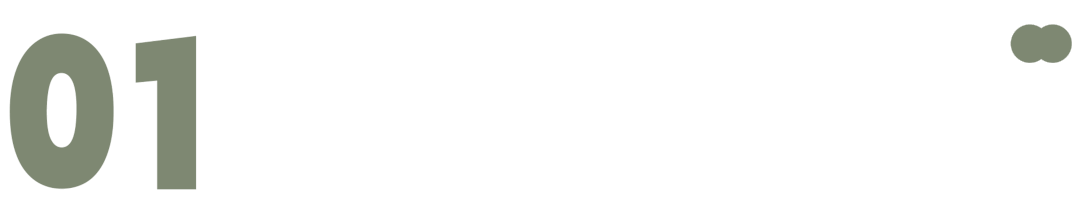
「上四休三」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上四休三」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后的劳工权益运动。19世纪,工厂里的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2到16小时,每周工作六天甚至七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工组织的壮大,「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一场争取时间与尊严的标志性运动。
到了20世纪,「五天工作制」逐渐成为全球劳动市场的主流。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发现,缩短工作时间不仅不会降低生产效率,反而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忠诚度。这种模式很快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标准。然而,进入21世纪后,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工作内容越来越灵活,但工作时间却未必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四休三」重新被提上日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上四休三」最成功的案例是冰岛。冰岛从2015年到2019年,针对2500名公共部门员工进行了「上四休三」的试点。结果表明,工作时间的减少并没有降低生产效率,反而大幅提高了员工的幸福感和健康状况。如今,冰岛的公共部门基本实现了四天工作制。此外,西班牙在2021年资助200家企业试行「上四休三」,数据显示员工满意度提升,生产力保持稳定。英国2022年的实验覆盖70多家企业,结果显示多数计划长期实施四天工作制。新西兰的Perpetual Guardian公司成功推行四天工作制,人们的效率和健康状况显著改善。日本将于2025年起推行该模式以应对低出生率问题,而阿联酋自2022年起已调整为4.5天工作制,进一步平衡工作与生活。
「上四休三」表面上看是关于时间的重新分配,但深层次的逻辑更为复杂——它折射的是个体幸福、社会公平与国家发展的多维博弈。
从个体的层面来看,这是一场关于时间主权的争夺。
工作时间缩短,表面上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自由的代价往往是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心理负担。那些被压缩的工时背后,是企业对劳动者「高产出、少工时」的隐形期待。如果结果导向的考核不被重新设计,「上四休三」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更加隐秘的内卷——一边工作强度更高,一边假期却并不是真正属于自己。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这是一场效率与公平的艰难平衡。
对高收入者而言,时间的自由意味着更高的生活质量,但对低收入者来说,工时减少可能直接转化为收入缩水。「上四休三」若设计不当,很可能加剧阶层差距。与此同时,对于国家经济而言,缩短工时并不是普适良方,高精尖行业可能受益,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却面临巨大的生产与成本压力。
归根结底,「上四休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模式改革,而是一场对时间、效率与公平的深刻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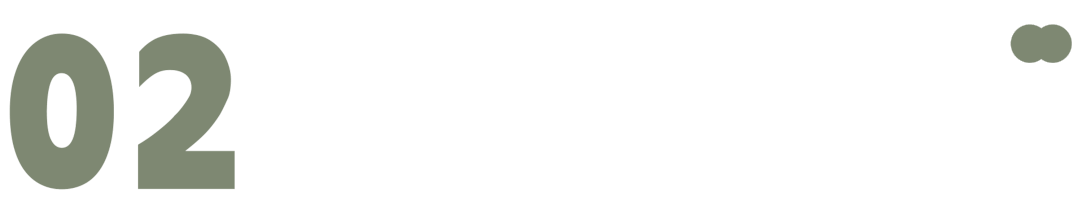
「可量化」与「创意性」:传媒工作内容的双重矛盾
那么,对于传媒行业来说,「上四休三」的博弈点在哪里呢?
从与几位传媒领域工作者的对谈中,小编看到了
两个鲜明痛点——「可量化」与「创意性」。
具体来说,传媒行业的工作内容具有两种典型特征:一是任务的可量化,比如新闻稿写作、短视频剪辑、内容排版等;二是创意驱动的非量化,比如选题策划、品牌内容制作、热点事件把控。这两种特性让「上四休三」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双重困境。
对量化任务来说,时间压缩难以减少任务压力。
传媒行业每天都有固定的内容生产量,新闻平台要更新文章,视频账号要发布内容,热点爆发需要及时响应。即便是四天工时,也无法减少这些任务需求,反而可能导致工作时间的进一步拉长,比如每天从8小时增加到10小时甚至更多。短期内的任务完成反而吞噬了长期的职业热情,「四天工作制」变成了「压榨制」。
对创意工作来说,灵感的「计件生产」是伪命题。
创意性任务更复杂,它并不是时间的简单投入就能换来产出。选题需要思考,策划需要积累,创意的迸发需要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如果在「上四休三」的高强度工作模式中,创作者的生活被压缩到只剩工作,那么他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休息时间」,更是创造力本身。
你看,矛盾就这样呼之欲出——「上四休三」在传媒行业不是解药,而是放大镜。
任务量不会减少,热点不会等人,所谓的四天工时只会让工作节奏更紧,压力更大。而对创意从业者来说,这甚至可能是灵感的「杀手」。灵感需要积累,创意需要时间,强行压缩工时,只会让创造力被榨干,变成流水线上的伪创新。问题的核心不是时间多一天少一天,而是如何优化效率,释放创意空间。如果这些底层逻辑不被改变,「上四休三」不过是给忙碌的传媒人,换了一种更隐形的枷锁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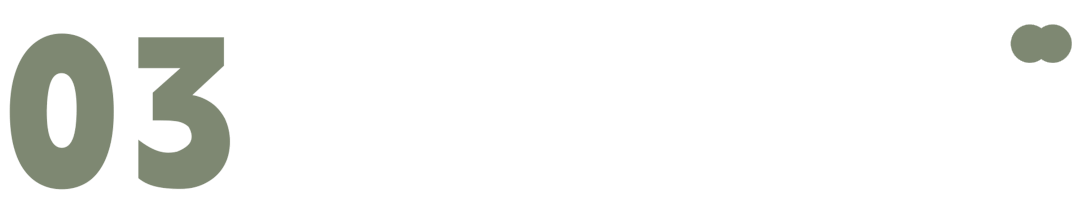
其实比「上几休几」争议,更可怕的是丧失主体性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表面工作时间」的缩短解决不了根本矛盾,传媒人该如何从这种看似无解的循环中突围?
一位同事的话给了小编灵感,他说:「我不害怕加班,相反,做一些有挑战、有意义的工作时,我是越做越爽,不计成本的。但如果是毫无意义的机械式重复,那我一分钟都不想浪费。」
这个时候,小编想引用宫崎骏的一句话:「生命之美在于奋斗和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本身。」你看,当我们在工时的苦海中深陷的时候,总有那么一批像宫崎骏一样的人,能够超越996和007的庸常挣扎,活在一个超然的自我时空里,创造出不可估量的伟大价值。为什么?因为他们始终掌握着对工作的主动权——一种绝对的主体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是他们选择在任何环境下都主动创造价值。
那么,这些人,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来构建信念感,获得真正的自由呢?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部分?
小编觉得,这其中的诀窍其实在于主体性,或者说,
是一种面对工作的正向底层逻辑:热爱工作,愿意与工作融为一体的人,根本不怕花功夫。
他们的付出不是机械的消耗,而是一次次为自己赋能的过程。他们知道,工作的价值不在于完成任务,而在于通过工作实现自我存在感的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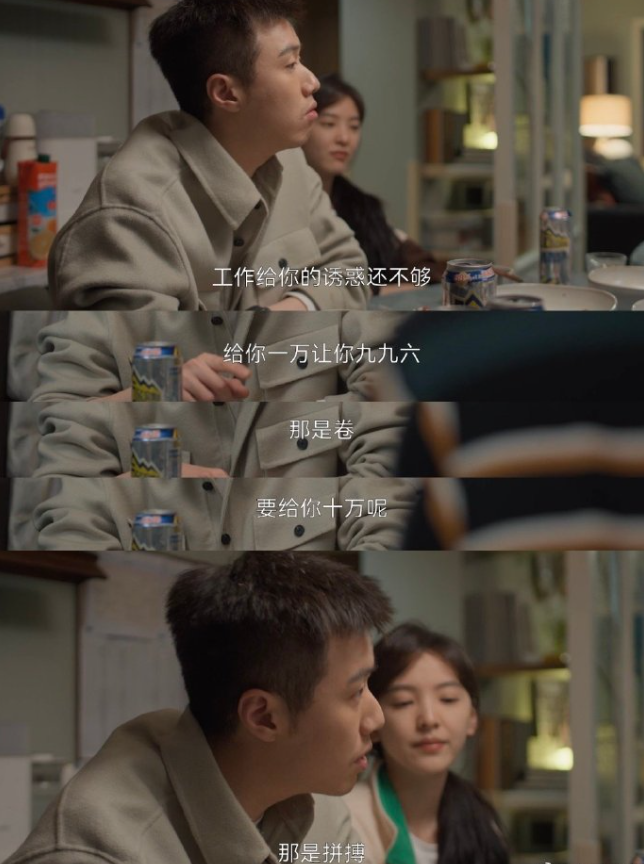
来源:电视剧《凡人歌》
然而,
当代年轻人呼吁「上三休四」时,其实是在发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呐喊:他们渴望的是自驱自主型工作,而不是「牛马式工作」。
你看,我们高考、考研的时候,头悬梁锥刺骨,早六晚十二也可以咬牙坚持,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只要熬过那一小段时光,就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考上心仪的大学、步入更高的学习环境,那种甜头是显而易见的。而工作呢?996也好,007也罢,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永无止境的消耗。日复一日的任务式工作,没有清晰的目标,没有实质的收获,甚至连短暂的正反馈都没有,唯一带来的,是疲惫不堪的内耗。
不仅如此,随着ChatGPT等AI技术的普及,新的荒谬画面正在浮现——AI的确替代了人力,帮助我们完成了许多曾经繁琐的工作。但结果呢?并没有让人类真正「被解脱」,反而带来了新的压榨。我们看似在从机械式劳动中抽身,科技却把我们赶到了更大的田地里劳作——追热点、创爆款、做永无止境的内容。明明是科技解放了牛马,但牛马却被驱赶到更大的田地里不停地耕耘。这本身,不就是一种讽刺吗?
这种矛盾背后,隐藏的是对工作的主体性的进一步侵蚀。当技术能迅速完成任务,老板的期待值只会更高——效率提高了,那就要更多的产出、更快的响应、更大的流量。于是,工作量不降反增,所谓的「被解放」不过是「被重新加码」。最终,AI只是延续了劳动异化的剧本,让「牛马式工作」变得更加隐形,却更加深刻。
所以,对于当下的国人,或者说对于当下的传媒人,
「上几休几」的争议,本质是一场表演。它背后的逻辑,不是时间的多与少,而是对工作意义的质问。
为什么讨厌上班?因为工作已经异化为一种不得不承受的负担,而不是一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是对工作主体性的丧失,更是对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放弃。
这背后,是对工作理想主义的匮乏,是缺乏正激励、正反馈的结果,也是在延时满足感中迷失的表现。传媒行业尤其如此。当工作变成一场永不停歇的生产机器,个人的创意被榨干,灵感无处释放,激情消失殆尽,所谓的「上四休三」或「上五休二」又能改变什么呢?
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休几天,而是在于我们能否重新找到工作的内在驱动力,并借此重塑主体性。
让工作不再是单调的消耗,而是一场能够激发个人潜力、不断发现自我的探索之旅。否则,「上几休几」的争议,只会成为我们对抗无意义工作的遮羞布,而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
1号结语
「上四休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一场关于劳动与价值的深刻实验。对传媒行业来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对时间与意义的错位理解——工作的本质从未被定义清楚,劳动的价值被效率淹没。时间的意义,不在于它被切割得多短,而在于它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质感与价值。
但「上四休三」也可能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重新思考的门:我们为什么而工作?如何从任务的泥潭中解放出来,让工作成为创造意义的途径,而非消耗生命的过程?传媒行业需要这样的契机,去反思,如何让创意不被榨干,灵感不被卷走,时间真正成为价值的承载体。
而在ESG框架下,「上四休三」更提出了一个深远的可能性:它不仅是对个体幸福的调试,更是企业思考劳动可持续性的第一步。真正的变革不在于休几天,而在于如何让时间连接起个人的创造力与社会的长期价值。现在,它还是一场未完成的实验,但正因如此,才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