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里的川滇之界
「从中甸搭班车前往稻城的路途,风物令人沉醉。我这样走时正是深秋,广阔的山脊上,一半的叶子泛了黄,另一半是红色的,就像缤纷的迷宫。
其实跨越省份的旅行特别容易见到美妙的景色,山脉与河水总是出众,人的行踪寥寥,积蓄着沉默的力量。
单身旅行非常适合这种形式,车票可以轻易买到,不必担心缺少交通工具寸步难移。
川滇藏的交界之处,风景都在路上,不会因为无法中途下车而有遗憾。所以在很多年间,我都热衷班车旅行,一次次漫游于西部省份的疆界。
也是在抵达川西边境的那个下午,翻越界山垭口时,我在海水一样澎湃的沉默里,见到了深陷于山林的两间石屋。它们遗世独立,恰似一个人的旅途。
旅行,就是和孤独相遇的时刻。」

一个人,日本猪苗代湖
第一次独自旅行,是久远的事。记得是 2004 年盛夏,列车奔驰于丰饶的北方平原,高大树种连云直上。灰幕低垂的傍晚。越来越浓重的暮色。
刚结束高考,背囊里是最简单的行李,甚至没有带上足够换洗的衣物。那个年纪好像并不在意。那次是偷偷离开。父母一直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同友人出行,去北京爬爬长城就会回来。
但其实一个人去了比北京远得多的地方。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同样的事。十几岁的尾声,孤独好像突然成了症候群。在青春期的岁月中感到最孤独的时刻,就是和父母对话时,因为我们听不懂彼此的话。
学校附近的一所大学,门口有一个贩卖打口 CD 的人,他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守着看上去非常喧闹的塑料盒子。很多等不及想要长大的孩子都是在那些 CD 的封套上见识到孤独的威力。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大概算是青春期关于孤独最文艺的献礼。而与真正的孤独狭路相逢,是在一个人的旅途中。

越过平原的高原,阿尔山
那次旅行的目的地是阿尔山。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变成滑雪胜地,没有人驱车而来,打破这片天地。它只是大兴安岭西麓的一片壮丽地貌。
我从上海出发,要在白城车站换乘列车,友人的父亲就常驻在当地部队,所以提供了一些出游指南。
列车上,独处时光曾一度令我感到狼狈。怎么办?没有人可以说话。被压抑的表达欲望,一遍遍灼伤青春的体肤。
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的成长总是在别人的过度瞩目下完成的。我们匆忙地扮演别人赋予的角色,努力符合那个亲密者的种种期望,从来没有面对自己的时刻。
列车越往北,车厢里的人陆陆续续提了行李下车,渐渐所剩无几。直到一觉醒来,被弄脏的窗帘像一朵乌云,空荡荡的走廊地毯上,几只用旧的拖鞋惨淡地陈列着。桌上好像还有没吃完的食物,和身体残留的复杂气味混和在一起。这时我在一种感觉里沦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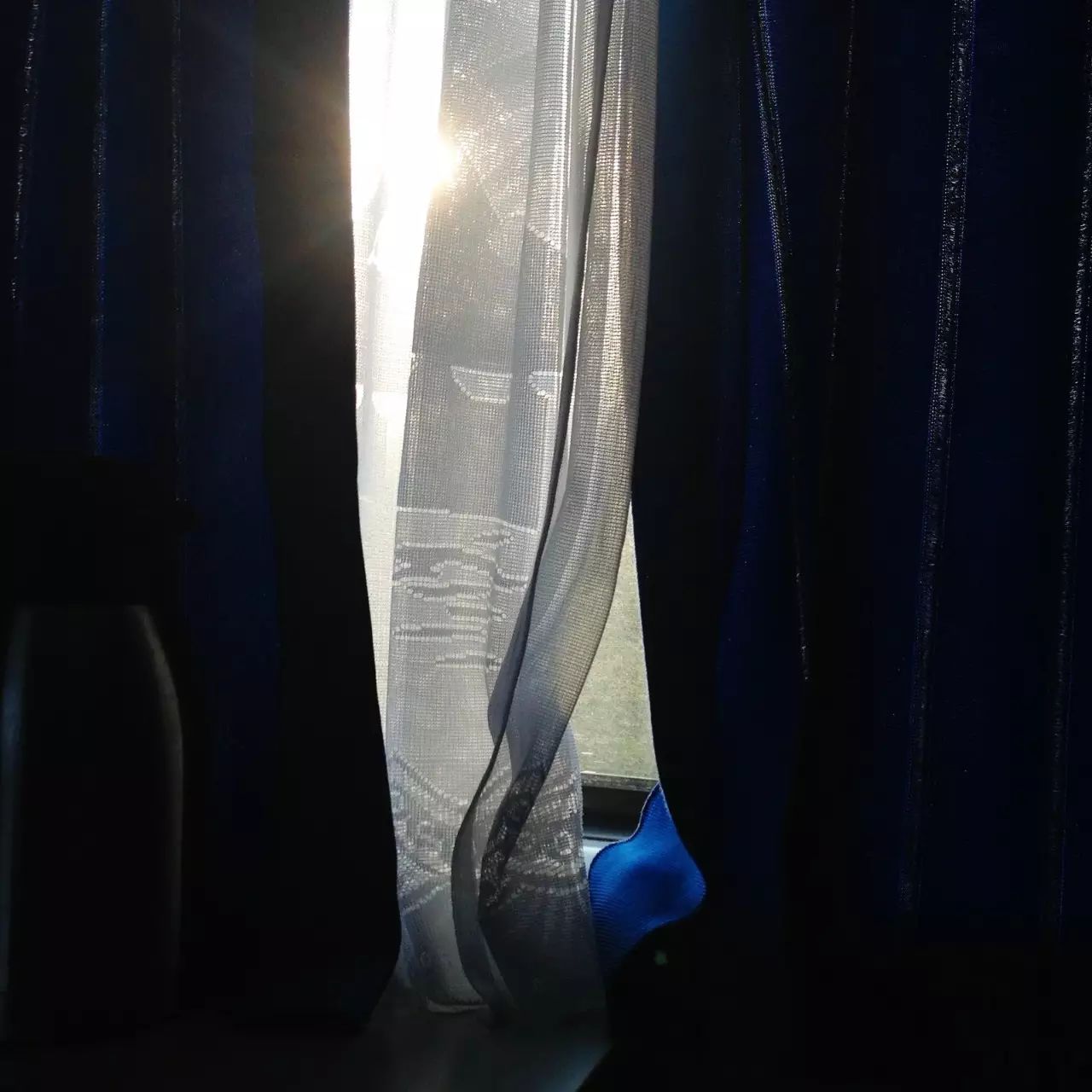
列车以内,去阿尔山
偶尔有一两个表情冷峻、没有交流的人倚在窗边。我也只好靠着窗沿坐下。彼时夜色渐浓。走廊上的灯还没有点起,车厢变得逐渐朦胧。列车穿过一个又一个漆黑的隧道。
直到现在,我好像还能触碰当时那种占领了身体的陌生感觉:车轮与轨道的撞击,汽笛的呜咽,窗外即将坠毁的太阳和狂风,都越来越轰鸣;忽然静默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待回过神,发觉流了眼泪。
后来的日子里,我反复重温过这一天。或者说,那个傍晚我好像被什么击中过,被一种东西吞没了,也变成它的一部分。那种空旷的声响伴我行走更长的路途。
想起来,那是第一次触摸到孤独具象的存在。盛大、悲伤,却有能量。
接下来的许多年,我总是一个人出走,沉湎于和自己的相处。总是在路上,学习正视内心,不造作,做好梦;学习真诚感激生命给予的独行机会。其实这只是与孤独和解的愿望。

一个人,茶卡盐湖
很小的时候,多数人第一次发现自己大概是在镜子里,我们跌跌撞撞地抚摸过镜子里那个张牙舞爪的甜美怪物。但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们却和自己渐行渐远,被别人的声音席卷了。
我们成了父母的孩子、老师的学生,同学的伙伴,接着变成一些人的恋人,共事的人,直到成为孩子的父母。我们脚步匆匆,追逐着别人的肯定,却在回顾往事时感觉虚无。
是谁躺在我身边,我在为谁生活?很少有人能够谅解生命无法改善的孤独感。而我想追逐的,正是独自行走的日子。
真正完成中国环游计划是在数年之后。我对友人说,只需要结实的背囊,一些不多的钱和健康的身体,就能周游四季。
那真是青春磅礴的时节。穿着劣质拖鞋越过滇西北的一条蜿蜒山路,泡沫软底的纹路逐渐磨平。夜晚歇在丙中洛一个小村庄的畜棚之内,楼上全是堆放着玉米的破败木板。收留我的主人送来土豆和柴,踩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又拖着星光消失于夜色。
直到漫长行旅中我屡次扭伤脚踝,在碎石砾上容易失去平衡,或者像刺猬那样笨拙地穿过黑夜的院落,我才承认自己还需要一双好鞋。
但远途与内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等待破译的谜团。「所以那不是周游四季,而是周游了内心。」我默默对自己说。

在丙中洛走过的路
旅途中的孤独,其实就是我想念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寂静感觉。所有发自别人的声音都已退却,让我有时间审视自我。
2004 年的北方之行,转了火车前往阿尔山。友人的父亲为我联系了农家,那里有一片火山区,却没有硫磺的气味。只记得拾到两块长满气泡的火山石,一直收纳在抽屉里。
阿尔山的夜晚,是草原和溪流,还有俄罗斯人冰与火的狂舞,以及许多早早熄灯的贩卖桦树手工制品的店家。买下一只最便宜的桦树皮制作的首饰盒,棕黄皮色,装饰性的细密针脚。只是并没有想过直到多年后搬家时被弄丢,它都没有装入任何饰物。
我最终发现了一个不喜欢修饰的自己。 现在想起来,也是青春来过的踪迹。

阿尔山针叶林
一个人的旅途中,我很多次触碰过孤独。它和寂寞不同,那不是你被世界抛弃,而是你主动撤退,退到了别人看不到你的地方。我很快成为乐于接纳这种孤独感的人。
但与孤独真正和解的过程,却绵延了更长的岁月。我遇到最大的难题是爱。因为我爱上了别人。孤独变得可疑。有一次,我在私人化的笔记里写下:不爱你,我才天下无敌。爱的世界里,总是在下雨,又在雨后折射出令人沉醉的光晕。所以我在恋爱中不断迷失。
那个人为什么不爱我?那个人是不是听懂我在说什么?那个人能不能填补我的孤独?
你看,我无法得到安宁,因为还是想要逃避孤独。
直到阿尔山以后很久。我搭乘颠簸的汽车从中甸前往稻城,满车都是裹着羊皮袄的当地人。经过不清楚名字的山峦,偶尔看到了两座石屋。
光线明暗恰好,枝叶哗然。疾驰的长途车很快经过了这样的景象。对于石屋主人而言,我只是误入的人。

路过石屋,中甸往稻城
后来司机行车歇息,我问他,界山附近有没有村庄。「那个山我们叫大雪山,过了山口要走一个小时才有人烟,哪里会有村庄?」他碾了碾烟灰。
我常想,是不是一对私定终身的恋人,修筑了这样两座独立之屋。他们未知缘由地私奔至此,彼此相爱以外,仍忠实地属于自己。他们之间有一段信步可至的距离,像两座陆路相通的岛屿。他们用相爱缓解孤独,又承认孤独无药可医。
很长时间里,想象素昧平生的石屋主人成为我审视自己情感的载体,我甚至能从这种联系中体会到深刻的慰藉。
不相爱的人是押送彼此至穷途末路,沿途一片荒芜。而相爱,永不能平息孤独的狂澜,却有看尽荒芜后的相视一笑。
在时光的旅程中,我渐渐明白,逐爱就是但愿你的身体也寄居过我所有孤独的总和。爱所能提供的能量,正是在人生孤独旅程中的萤烛之光。
传道书说,万物有定时。跳舞有时,哀恸有时。所以相爱有时,孤独亦有时。学习与孤独和解,才是人生逆旅唯一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