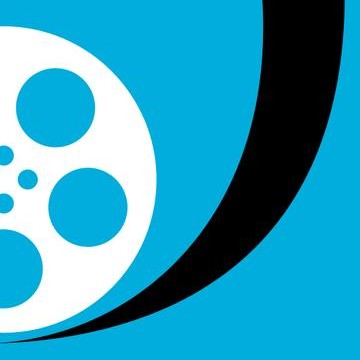本文来自豆瓣用户Huwennie 给《托尼·厄德曼》的影评,
原文标题《一对父女,两个德国》
导演玛伦·阿德快40了,走的是熟女风,她身材不高,五官秀气,眼线画得特别克制,是细长而不露的那种,自然极了,反而引起人注意。《托尼·厄德曼》是她拍的第三部电影,技术上克制自然,风格如她,没有酷炫的镜头和填充的音乐,也没有大制作的场面和华丽的取景,全靠扎实的剧本和极有功力的演员撑起这两小时四十二分钟,不仅在戛纳电影节赢得影评人的全堂彩,8月17日在法国上映时,各大媒体的电影记者同样给足面子,推出专访加影评特版,并打出华丽丽的高分。
德国人幽默起来,能把性命豁出去。《托尼·厄德曼》讲了一个太过乖张、荒诞、神经质、不按常理出牌的故事,与正统的日耳曼精神有点不符。“原来德国人也这么有幽默感,赶紧通知法新社,让它发通稿,广而告之下”,费加罗记者这句话,自有法国人民的挖苦调侃劲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部堪称带有魔性的电影,对他们震撼有多大。

这是一个父女和解的家庭故事。温弗雷德六十来岁,曾当过老师,目前半退休状态,离婚独居,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他保留了六八那代人的自发和颠覆精神,比如他特别喜欢易装,搞个小儿科的玩笑来打趣别人,热衷于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影片第一幕,他便使出浑身解数,做游戏扮演,把邮递员搞得云里雾里,有些尴尬,他也以这种方式进入他女儿的生活。依奈斯三十左右,在布达佩斯的跨国公司做咨询,严肃认真,野心勃勃,特别能拼,每天被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她自私强势,有时显得冷血并缺乏同情心,和父母家庭的关系有些疏远。
温弗雷德的老狗威利去世后,不知是对生死看得更通透,还是出于发泄,他没打招呼,便空降到依奈斯公司。她那井井有条已经模式化的生活被父亲打破,两人关系紧张,温弗雷德不得不离开,但他后来改头换“牙”,以托尼·厄德曼的身份“强势回归”,几经周折,与女儿重新连接在一起。不能说他做的一切对女儿有所改变(女儿后来辞职,但只是换了家咨询公司),但最后依奈斯理解并尊重父亲的一片苦心,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现状,试图活得洒脱一点点。

温弗雷德的假牙是工具,让他在自我和想象角色之间自由转换,他的幽默也是,可借它来逃避现实,或攻击自己的女儿 —— 这是单纯的父亲角色无法允许他做的事情。他的代入角色—— 托尼·厄德曼,在影片演了快一半时才出现,他怪诞不羁,如影随形伴着依奈斯,不仅逗一逗她朋友,也会跟她顶头上司搞恶作剧。父女对话不多,两人的互动都被这种角色扮演占据填充。他们偶尔摘下面具,躲在角落时,神情没落沮丧,逗笑之余,这也是一部特别让人揪心的电影。
说的是两代人,其实是两个德国。温弗雷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依奈斯是个务实主义者,这同两人出生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二战后出生的德国一代,思想方式简单,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有个共同的执念,他们认为纳粹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他们的敌人明确,是上一代人;他们教育孩子时,注重人性和人文,鼓励他们自由选择”。用导演的话来说,“这些人靠幽默解决了不少问题”。温弗雷德捉弄完邮递员后,有些不好意思,给人家几个小费;他跟着女儿在布达佩斯施工现场与当地居民告别时特别嘱咐他,“不要忘了你的幽默感”,有浓浓的人情味。
依奈斯视镜下的德国则不同,它充满自信,主导欧盟政治经济格局,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历史远去,人们生活在当下。当下也是金融资本盛行、自由资本主义当道、世界化大潮汹涌来袭的的当下。如此大环境中,德国不少公司进驻罗马尼亚,改变当地家庭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为了获得更大收益,裁员成了必经工序,人与人之间仿佛只有利益联系,高低尊卑之别也特别清晰。比如依奈斯,她对下锱铢必较且毫无商量的余地;对上则谄媚有加,为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她不喜欢“享受”、“幸福”或“人生”等大词,在乎实实在在的产出和效果。

温弗雷德问她,“你还是人类么?”,代际矛盾以及历史同当下的冲突达到最高峰。
影片近三个小时,导演在刻画人物形象上费尽功夫,为最后出其不意的高潮做了铺垫,女主歇斯底里高歌一曲、临时凑数的裸体生日派对以及父女两人终于心有灵犀相拥在一起,神来之笔来得密集,让人应接不暇。观众记住了最后的好,忘记开头的慢热。
应该如何做,生活才算没白过?父亲抛出的都是些大问题,不讨巧,如果不注意便会陷入“正能量”的圈套,被套上说教的嫌疑。但这些大气象,都被入木三分的细节和近乎真实的桥段隐于无形之中,如同导演的眼线一般,够自然。

- END -
感谢作者为豆瓣贡献优质原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