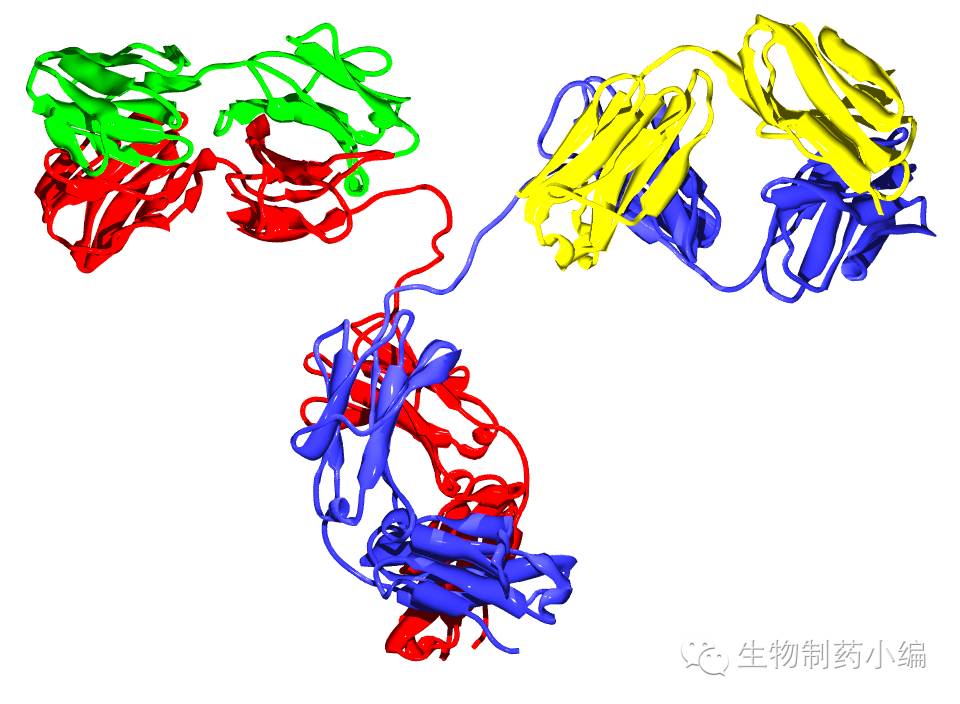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EmileMichel Cioran,1911-1997),罗马尼亚文学家和哲学家,二十世纪怀疑论、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生于罗马尼亚乡村一个东正教神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哲学,1937年获奖学金到巴黎留学;将近60年,一直在巴黎隐居,先住旅馆,后住在阁楼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接受采访。他曾郑重告诫自己:“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局限于一场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显然,他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孤独。
在喧嚣的、充满功利和诱惑的20世纪,齐奥朗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奇迹。在孤独中思想,在孤独中写作,在孤独中同上帝争论,在孤独中打量人生和宇宙——孤独成了他的标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在孤独中,齐奥朗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时间之外”,身处“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这种绝对的孤独必然会留下它的痕迹。《生存的诱惑》《历史与乌托邦》等著作奠定了他哲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要地位。移居法国后,他一直用地道的法语写作,文笔清晰、简洁、优雅,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黑色幽默。在他看来,“写作便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因为“作家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生物,通过言语治疗自己”。他甚至感叹:“假如没有写作本领,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他的文字常葆有剖析和挖掘的力量,准确、无情,直抵本质。对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等作家有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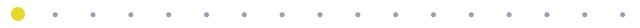
除了古希腊的怀疑论者与古罗马帝国堕落时期的皇帝以外,一切心灵,看来都受役于某种入世的志愿。只有他们从有用而乏味的执着中解放了出来,前者通过怀疑,后者通过疯狂。由于他们将任意性提升到训练有素,或是令人晕眩的高度——这视他们为哲人抑或远古征服者的后裔而定——他们也就不再执着于任何事物了: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令人想到圣人。只是圣人永远也不会坍塌,而他们却在承受自己的游戏后果,因为他们是自己任性的主子兼受害者——他们是些真正的孤独者,因为他们的孤独什么也不孕育。没有人把这种孤独树立成榜样,他们自己也不曾如此自诩;所以他们才会只以嘲讽,或是暴力与他们的“同类”交流……
担当一种哲学或是一大帝国的溶解剂:有什么荣耀比这来得更悲凉、更庄严呢?一头杀掉真理,另一头灭掉伟大,这两大养活精神与城邦的怪癖;挖倒了支撑着思想家与公民傲气的那套骗局结构;拧松思维与欲求的乐趣赖以为继的机关,乃至令它扭曲;借助讥讽与酷刑的微妙,辱没传统的抽象与可敬的风俗,啊!多么精致又野性的生机啊!没有神在我们眼前死掉,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在古罗马,当人们在更换、输入神祗,看着他们憔悴衰败的时候,大谈幽灵该是多么痛快啊!虽说还是会担心这种妙不可言的反复无常,某一天,面对某个严厉而不洁的神灵攻击会弃械投降……而且后来果然就这样发生了。
要摧毁一座偶像并不容易:花费的时间跟宣传景仰它所需要的时间一样多。因为只是毁灭它的物质象征还远远不够,这还算容易办到;要消灭的是它长在灵魂里的根。如何才能将视线转向那些黄昏时代,那些眼看着历史就在一双双只被虚无点亮的眼睛里消逝的时代,而又不在文明之死这一伟大的艺术面前心软呢?
……我便曾如此梦想自己是那些奴隶中的一员,来自某个不可能的国度,哀伤又野蛮,在垂死的罗马,拖着一股淡淡的悲切,上面装点着古希腊的名言警句。在那些塑像空洞的眼中,在被蚀人的迷信摧折过的偶像身上,也许我能忘却我的祖先、我的枷锁和我的遗憾。怀着这些古老象征的哀伤,或许我会获得自由:我会分享遭人遗弃的神灵所拥有的尊严,在居心叵测的十字架面前,在仆人与赴死的圣徒发起的侵略前,捍卫他们,而我的夜晚会在西泽大帝的荒淫与疯癫当中稍事休憩。在一些交际花的身边,或是一些多疑的妓院,或是一些搬演着豪奢与残酷的马戏团里,我这个玩世不恭的专家,将给那些新兴的狂热刺满一种沦丧的智慧全部的利剑,在自己的思索当中注满邪恶与鲜血,使逻辑舒张到它从未想象过的地步,一直达到正在死去的世界才有的境界。
-end-

回复以下关键词,送你一篇歌苓美文:
新作|自由| 戒荤| 跑爱| 婚姻| 善良|
爱| 婚姻| 善良| 萌娘生命| 女郎| 信仰| 建筑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