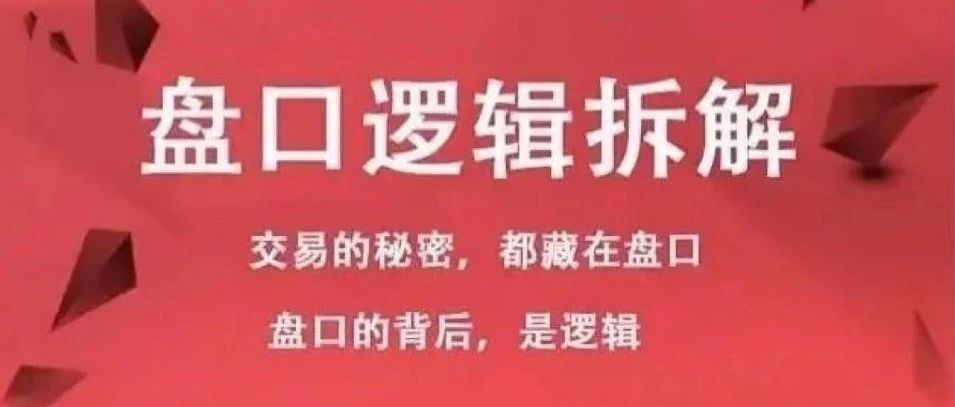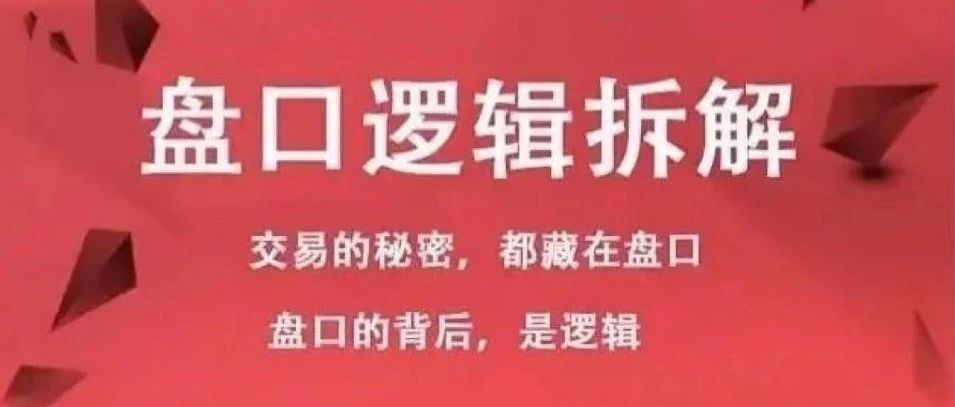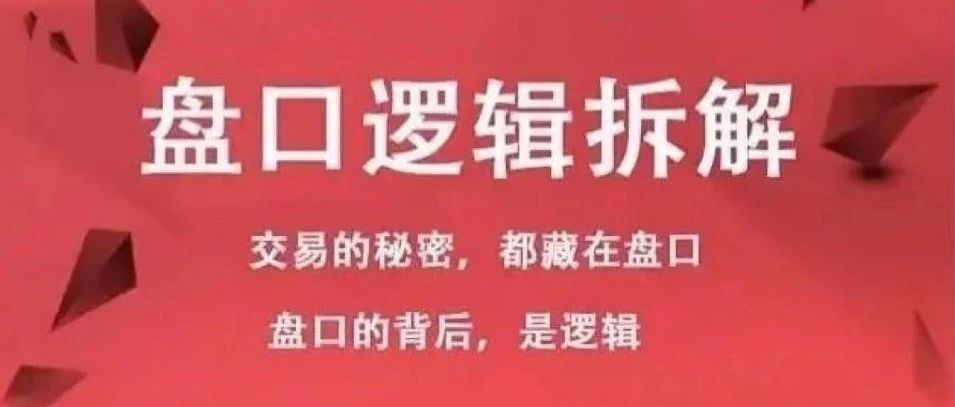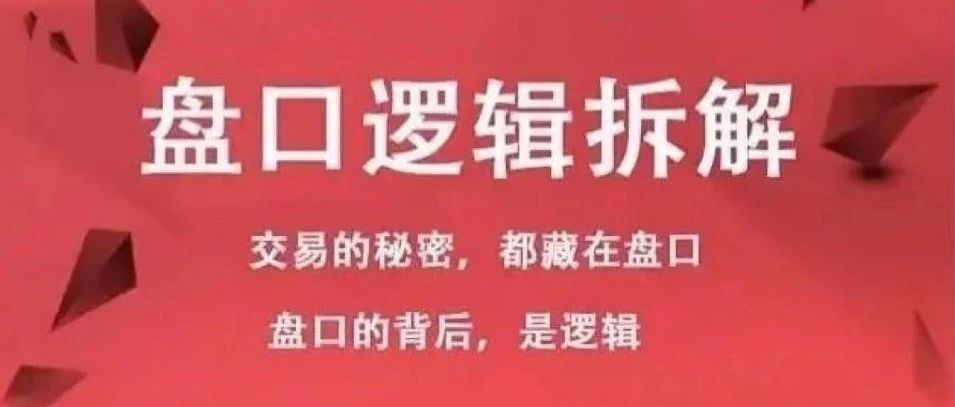9月24日的德国大选对于安格拉·默克尔个人来说是一个胜利,但对于她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乃至素来走中间路线的理性的德国政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这是默克尔为她的难民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默克尔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执政联盟的得票率接近33%,继续高居议会各党派之首,默克尔也将因此迎来她的第四个德国总理任期。
面对投票结果,默克尔试图表现出欣然接受的姿态,称她曾期待“稍微更好一些的结果”——越是面临压力就越显得淡定,这是她作为一名成功政治家的最大特质。但默克尔胸有成竹的样子丝毫不能掩盖这样一个尴尬事实:这是这个中右翼保守政党自二战以后收获的最低支持率。
过去四年在“大联合政府”中扮演执政伙伴的社会民主党(SPD)的境况更加糟糕。尽管请出了在欧洲范围内人气很高的欧洲议会前议长马丁·舒尔茨来与默克尔对阵,但这个拥有150年历史、二战以来曾主宰德国政坛的“百年老店”依然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惨败,仅赢得不到21%的选票。这也是该党80多年来的最低支持率,从这次的得票率来看,它已经流失了一半昔日选民。马丁·舒尔茨在选后沉痛地说,这是“德国社会民主事业遭遇艰难和困苦的一天”。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次德国大选就像是今年春天法国大选的余波——老牌大党的衰落标志着“德国政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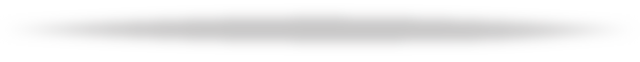
这或许将成为数十年来第一次引人关注的德国大选。
以往的德国选战总是让德国以外的人们昏昏欲睡:它的议题之琐碎沉闷无论如何也配不上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第一强国的身份;竞选对手之间的相互争论更是让那些习惯了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夸夸其谈和人身攻击的看客无趣到惊诧的地步,与其说他们在为了权力而辩论,不如说他们在相互补充对方的观点,他们之间最大的政治分歧通常也只是要不要设立最低工资保障之类;当然,结果也总是不出意料,永远是中间派轮流坐庄,而且选票高度集中地流向中间党派……
这应该被视为政治成功的体现,只有一个繁荣而稳定的国家才有资格让自己的政治角逐如此波澜不惊。
但这次很不一样,今年德国大选的最大看点显然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
高举反欧、反移民大旗的德国新选择党(AfD)赢得了超过13%的得票率,大大超乎选前预期。这个成立不到5年的新政党将一举成为德国联邦议院中的第三大党,拥有90多个席位。它也是第一个进入德国主流政治的强烈疑欧势力。在2013年的大选中,成立才9个月的AfD获得了4.9%的选票,差一点而没能迈过德国法律规定的进入议会所需的5%得票率门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荷兰、奥地利和法国在今年的选举中相继挺过民粹主义浪潮之后,德国这根欧盟的“稳定支柱”上却出现了一道的裂痕。如果加上极左翼政党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得票率略高于9%,在这次联邦议会选举中,总共有超过1/5的德国人把选票投给了反建制的政党。这足以证明,即便是德国,对民粹主义也并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它也提醒人们,在欧洲局势正呈现显著好转之际,民粹主义的幽灵并未远离。
许多人因此将此视为一个巨大的警示,社民党前领导人、德国现任外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称,“自二战结束以来,将头一次有真正的纳粹出现在德国国会大厦中”。
我的一位在慕尼黑安联保险公司总部工作的中学同学告诉我,他的同事用“shamed”来形容AfD这次的胜利。然而AfD的崛起不正代表了一大批对全球化不满的底层民众与这些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的对立情绪吗?这种精英与大众的割裂已经在去年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结果中一览无余。现在看来,德国也不能例外。
两年前默克尔决定德国向中东难民开放国境,一下子接纳超过100万穆斯林,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情绪。
若仔细分析新选择党的得票增长来源,可以看到,它们大幅集中在前东德地区。AfD在东部地区获得的选票比前 4年前的大选增长了15.6%。实际上,那里恰恰是全德国移民最少的地区,中东难民被安置在那里的也很少。今年6月我在莱比锡遇到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她也对这种状况感到十分无奈和难为情。
兴高采烈的AfD候选人亚历山大·高兰在选后誓言,该党在议会中“不会放过”默克尔,将“猎杀”新政府,无论新政府由哪些党组成。他用与唐纳德·特朗普和马琳·勒庞如出一辙的口吻说:“我们将夺回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AfD的巨大成功自然也激励了它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姐妹政党,在今年5月的法国大选中败给埃曼纽尔·马克龙的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在Twitter上难掩兴奋之情:“我们的AfD盟友在这次历史性展示中的表现棒极了!”
悲观的欧洲观察者将此次大选看成是“默克尔时代”走向终结的序幕。
默克尔在胜选后强调:“我们是最强大的政党,拥有建立新政府的使命,不可能会出现与我们对立的联合政府。”但不少人已经在猜测,她在两三年后就会交棒给继任者;布鲁塞尔和巴黎的一些官员私下里已经在担忧所谓“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策走向了,他们认为,欧洲下一场重大改革的决策者中可能不会再有她的身影。
但这些担忧可能有些过头了,与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所获的支持仍然是比较低的。在9月24日的大选中,中右翼和中左翼党派赢得了超过73%的选票,证明中间派在德国依然是绝大多数。
而且,默克尔最擅长的正是调和不同阵营的分歧。
不过,未来几个月里,她的这项工作将会遇到比前几届当选后大得多的困难。
默克尔眼下的当务之急还不是直面新选择党的挑战,而是顺利完成新政府组阁。这似乎颇为不易。
默克尔已连续担任三届总理,每一次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政党看起来都没有捞到任何政治利益。在4年前的大选中,作为默克尔执政伙伴的自由民主党(FDP)得票率竟低于5%,在二战后首次没有被挡在联邦议会之外。如今,社民党(SPD)和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又成为选战中的牺牲品。
因为这个缘故,SPD领导人舒尔茨已经对默克尔明确说“不”,他在获知开票结果后第一时间即表示,社民党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反对党,“以捍卫民主抵御外界的质疑和攻击”。SPD自我检讨认为,加入本届联合政府是一个重大失策,令自己元气大伤,因为这让本党很难与基民盟区隔开来,导致了基本盘选民的流失。
尽管默克尔已经敦促SPD不要仓促关上再次共组“大执政联盟”的大门,但恐怕很难说服后者回心转意,除非基民盟在政策、人事等许多问题上做出异乎寻常的让步。
由于除社民党外其他任何一个政党与基民盟的议席加起来都不足以超过议会半数,所以默克尔只得选择另外两个党,组成三方联合政府。考虑到基民盟(CDU)与左右两个极端的左翼党和AfD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价值分歧,唯一的选项便是与FDP及绿党结盟。这三个党的党旗颜色分别是黑色、黄色与绿色,拼在一起很像牙买加国旗,于是人戏称它为“牙买加”联盟。
但这很可能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脆弱联盟,虽然后两个小党近年都有过参与执政联盟的经历,但它们在国家层面上从未一起合作经受过考验。
其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强调加强政府监管的绿党与亲商业的老派自由主义者FDP政见高度对立,未来可能会在税务、能源、欧盟和移民政策等许多领域发生冲突。
绿党历来将气候变迁、欧洲问题和社会公平作为参加任何联合执政谈判的优先议题,它已经放出风来,称该党的首要任务是打造一个“更强大的欧洲”。
然而FDP反对任何欧洲层面的进一步整合政策,实际上,FDP在关于欧洲问题的某些议题上,意见与AfD有相似之处,尽管两者的理论基础南辕北辙。FDP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洲一体化理念的尖锐批评者,它在竞选中呼吁让欧洲稳定机制(ESM)纾困基金逐步退场,改变欧盟条约以允许个别国家退出欧元区。该党年轻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林德纳曾在竞选期间公开呼吁希腊放弃欧元,恢复使用德拉克马。
一旦FDP加入联合政府,便意味着今后默克尔每一次前往布鲁塞尔或巴黎,都将被自己的执政伙伴牢牢地拽住不妨。
FDP还不是未来联合政府中唯一拖后腿的盟友,更大的麻烦可能来自基民盟的巴伐利亚姊妹党——基社盟(CSU)。受到默克尔的拖累,在本次选举中,CSU的选票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AfD。由于CSU明年将面临地区选举,为了应对AfD的强大压力,它的立场不得不向右倾,这会迫使它在联合政府中摆出与默克尔更加不一致的姿态。
总之,在经历了长达12年与自己高度融洽的一团和气的议会氛围之后,默克尔未来将面对一个崭新的局面。无论如何结盟,下一届德国政府肯定会比之前和现在难以驾驭得多。默克尔现在的处境有点像2012年大选之后的奥巴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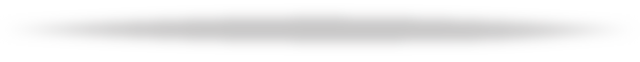
除了默克尔本人以及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些德国老牌政党,受到这次德国大选结果最沉重打击的大概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这位怀有远大抱负的年轻政治家现在正挥舞着欧洲一体化的大旗与民粹主义势力对抗,他在竞选法国总统时曾经承诺,在多年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新的冲击之后,法国将与德国紧密合作,一同“重新启动”欧洲。
9月26日,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进一步呼吁建立更强大的欧盟,并阐述了一系列欧盟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到2020年建立一支“军事干预部队”和共同军费预算;一个处理反恐情报的欧洲机构,以及推动经济“大胆创新”的另一个欧洲机构;引入金融交易税,寻求引入碳定价机制;制定到2024年每个欧盟年轻人至少会说两门欧盟国家外语的计划。
他还打破了法国的传统禁忌,提出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并力争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候选人的泛欧洲化(也就是不再按国别分配欧洲议会名额,而是在全欧洲范围内根据人口实行普选)。
当然,马克龙还重申了之前的多次倡议,设立欧元区财长及共同预算。这被认为是欧洲下一步一体化的重中之重,也得到了默克尔的支持。
马克龙在演讲中含蓄地抨击了来自德国的逆风,称“当前挑战攸关生死,曾保护欧洲蓬勃发展的海堤已经没了。我们需要沿着能确保我们未来的唯一路线前进,即为了一个独立自主、团结和民主的欧洲重新奠基。”在谈到自己的欧洲愿景时,他豪迈地说:“我没有红线,我只有眼界。”
马克龙的这些设想或许有些不切实际,但他设定的大方向没错,如果拥有60年历史的欧盟想要延续下去的话。
肇始于2009年底、2010年初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像一场风暴,吹散了欧洲过去那种团结融合的假象。事实上,这种貌似一天比一天紧密的关系从没有获得过一个可行的制度保障。欧洲人现在意识到,从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2012年的《里斯本条约》,自己所做出的所有制度性安排都是在沙滩之上建造高楼。欧盟一直在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建立统一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至于能够赋予这个财政实体合法性的政治体系更是影子都没见到过。
这个根本矛盾的核心就在于,在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启60年后、决定构建统一货币联盟25年后的今天,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丝毫没有褪色。不仅如此,金融危机还进一步分化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激发起了欧洲新一轮的“再民族国家化”,从而使得不同国家之间变得更加对立。反欧和疑欧的民粹主义势力在各国的崛起,正是这一新趋势的表征。
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加强、而非削弱欧洲一体化”。
过去几年来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已经表明,对有关欧元区治理的许多问题来说,委托政府间政治机构做出决定即便不是完全行不通的,也是效率极低的。欧洲一些高级别的决策程序必须与各国国家政治脱离关系,这就需要建立相应制度的机构来填补这一空白。设立更加不受各国国家利益的左右的欧盟财政部等独立机构、赋予欧洲议会更大的权力,都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现在到了让政治联盟这一概念变得有血有肉的时候了。过去那种经济融合会自动催生政治联盟的想法在危机中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相反,下一步更深层次的经济融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来护佑。但如何把这一新共识变成现实,是眼下欧洲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最艰巨的一个。这类艰难的改革需要修改欧盟条约,而修改欧盟条约则又必须动用大量的政治资本,欧盟最大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的信任与合作是其基石。
有相当一段时间,在默克尔最需要援手的时候,传统的“法德引擎”却几乎熄火。
在前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任内,法国在欧盟问题上几乎毫无作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自身虚弱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奥朗德的无能。
在骄傲的法国人心目中,欧洲应该由法国领导、通过法德合作来推动的观念一向根深蒂固。从现代“欧洲之父”让·莫内到雅克·德洛尔,法国人一直都以向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思想领导而自豪。然而,奥朗德既没能在谈判桌上发出任何强有力的声音,也没有与默克尔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是欧洲议程一度停摆的根源。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国的衰弱其实也是德国的麻烦。
马克龙的异军突起代表了法国的新变化。浪费了许多年时间后,在法国政界和商界,关于欧洲、欧元的未来、经济治理,以及集合各个国家主权、以应对当前共同挑战的必要性等方面,一种新的共识正在逐渐显现。法国精英阶层心照不宣地承认,欧洲再也不会仅仅是法国思想和利益的延伸,需要把更多权力移交给德国。与此同时,法国自身需要通过真正的改革来重获强大的竞争力。
马克龙的成功当选就是法国民众在这方面的共识和授权。
对于德国来说,必须尽力帮助马克龙取得成功,并确保他不会在下次总统大选中被民粹主义击倒,这是保障欧洲稳定和繁荣的关键之役。事实上,默克尔早就认识到,马克龙的成功与欧盟的成功密切相关。这也是生性谨慎的她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例如共同债券、甚至共同财政计划)与马克龙存在严重分歧,但依然对他给予有力支持的出发点。
然而,9月24日的德国大选结果很可能令默克尔响应马克龙,共同重塑欧洲的计划不得不大大放慢脚步。
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跻身联邦议院,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执政联盟,将改变德国的政治基调。一方面,默克尔的政治地位被削弱,她将转而采取更加折中的立场,扮演领导角色以及推动欧洲向前发展的空间已经缩小了;另一方面,德国反欧洲的力量大大增强,使法德之间的这种“大妥协”失去了几个月前近乎理想的条件。
如果一个厌恶风险的、只愿自扫门前雪的德国重又回来,这将是欧洲面临的最大新风险。更何况,未来一年还是英国退欧协商的紧要关头。
危机面前从来就是不进则退,拖延转圜的余地很小。如果德国大步退缩了,那么暂时春风得意的马克龙也会受到拖累。早就有人指出,马克龙之所以胜选是因为欧洲经济转强,而不是因为他提出的欧元区远大计划。博德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Founda-tion)去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仅有41%的法国民众认为欧洲需要更大程度的政经整合,较欧盟平均值低10个百分点。这项调查同时显示,关于马克龙提出的设立欧洲财政部长并编列专属于欧元区的预算,德国和法国民众持高度怀疑态度。仅有31%的法国民众和39%的德国民众与马克龙抱持同样想法,认为欧元区的预算应该用于支持区内经济较为疲弱国家。
如果马克龙不能在关键时刻得到有力支援,并乘势而上,那么他重蹈前两任法国总统覆辙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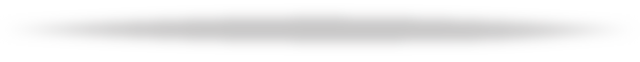
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曾在10年前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都知道欧洲应当改革,以及应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了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当选。”
这就是默克尔当下的真实处境,也很可能是马克龙几年后将会面对的。
最醒目的前车之鉴莫过于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2003年,施罗德政府推出名为“2010年议程”(Agenda 2010)的长期结构性改革计划,使德国避免陷入高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国债危机,也重塑了德国经济竞争力。但施罗德却为此付出了连任败选的代价。
施罗德败给的选举对手正是默克尔,他“虽败犹荣”。默克尔在12年前首次当选德国总理后的首次演讲中曾说,她从个人角度感谢施罗德,“由于他勇敢决断地实施‘2010年议程’,我们的社会系统才能够与新时代相适应。”
今天的默克尔面临着与当年竞争对手相同的局面。
不过,现在肯定不是举白旗的时候。
与5年前甚至1年前相比,如今的欧元区局面已出现了重大改观。
首先是德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失业率连续创下多年新低,这也是默克尔得以连任的根本保证。IMF预计,受德国带动,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年均增长将达到1.8%以上,不仅优于美国和英国的表现,也大大好于先前的预估。其中,多年来一向疲弱的法国经济的快速回升是最大的亮点。
而在年初和春季荷兰和法国大选的政治风险消退后,老大难希腊在停止发债三年之后又成功重返国际债市。这标志着过去几年不断发酵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了重大转折,更凸显了当初的应对是有效的——5年前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欧元区可能形成一场让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小巫见大巫的经济地震,欧盟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区可能会陷入一系列银行破产、债务违约和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
这向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也为默克尔和马克龙的“重塑欧洲”计划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回顾过往几年,欧元区国家在压力临头时更加团结一致采取行动的先例屡见不鲜。这其实也一直是德国人在“教育”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时的观点。
眼前就有一个化危为机的机会。
德国大选前夕,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发表被称为“盟情咨文”年度演讲时称,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复苏以及奥地利、荷兰和法国选举中疑欧势力遭挫败,“欧洲的风帆再次处于顺风状态……让我们借着有利的风向启航。”
这种乐观的口吻与容克在一年前发表的演讲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是在英国举行退欧公投之后,他警告称,欧盟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其背景是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经济处于缓慢不稳定状态,仍在艰难摆脱欧元区债务危机。
容克如今认为,英国退欧对于一些“前卫”国家来说是一个机会,这些国家希望“向前迈进”,“不被那些希望步伐慢一点或小一点——这是它们的权利——的国家拖后腿”。
他有保留地响应了马克龙的宏伟计划,呼吁集中权力,终结过去为了照顾某些成员国的主权担忧而给予妥协的做法,并敦促深化欧盟的预算权力、机构以及在税收和外交政策等领域的权限。
容克在年度咨文讲话中提出一项新愿景:2019年之后欧盟将有约30个国家使用欧元,届时而且欧洲还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中心。
在今年3月欧盟领导人汇聚罗马庆祝欧盟成立60周年的时候,默克尔也曾对媒体说,她并不担心会有更多国家步英国后尘退出欧盟。
但正如容克所言,“现在我们迎来一个机会窗口,但它不会永远开着”。
尽管选举结果很不理想,但毕竟它让默克尔继续置身于欧洲事务的核心地位。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等待她的使命还有很多。
为了有效应对席卷西方和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未来4年,她首先要应付的是本国崛起的民粹势力,赢回那些流向新选择党的选民。
这或许意味着她必须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消化接收100多万难民所产生的后遗症。甚至是在选前,默克尔身边的多位官员都已淡化欧元区改革的迫切性,他们称确保欧洲边境安全以及协调区内难民分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第二轮难民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将会大过第二轮欧元区危机。”
民粹主义在德国的抬头突显了一个事实,许多德国工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标准正受到挤压,这也是作为执政联盟成员的德国社民党在选举中大败的原因。未来,就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防止贫富差距拉大,是摆在默克尔面前的头等大事。
未来德国的民粹主义在政治上会朝哪个方向演化,暂时还很难看得清楚。
有一些迹象表明,AfD正在急速激进化。最近,AfD开始玩弄德国政治中最具煽动性的素材——这个国家的纳粹历史。该党领导人之一高兰说,德国人有权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士兵感到骄傲。在一些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中,代表德国新选择党参加本次大选的另一位首席候选人阿莉塞·魏德尔还将德国政府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傀儡”。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但另一些迹象也表明,AfD内部意见出现分裂迹象。在选举刚过去一天,该党共同主席弗劳克·佩特里就令人疑惑地表示,她不会加入AfD的议会党团,她将以无党派身分担任议员。
总之,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有明确理念和条理的政治力量,它的力量来源于主流政治的失败。
默克尔曾斩钉截铁地说:“欧元失败,就是欧洲失败”。
总体上看,在可见的未来,欧洲这架老马车既不会像民粹主义者希望的或悲观论者预言的那样分崩离析,也不会像马克龙热切期待的那样突然就变成一个强大的联邦。它仍将是一只“混血动物”,沿着自己过去60年里一路走来的那种吵吵嚷嚷的妥协和博弈的路径继续艰难摸索。
而欧元和欧盟的命运将勾勒默克尔第四个德国总理任期的轮廓,并决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