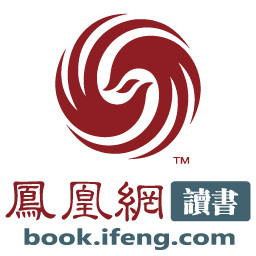海昏侯之后,江西考古再迎大发现!8月28日10点半,江西省文化厅 抚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抚州发现明清时期墓葬42座,目前基本确定汤显祖墓。
根据文献记载,汤显祖逝世后葬在抚州市文昌里灵芝园内。但由于时代变迁,汤显祖墓园渐渐湮没,无迹可寻。目前,位于抚州市人民公园内的汤显祖墓只是其衣冠冢。
幸运的是,去年11月,抚州市在推进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修复、建设过程中,拆除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制冰厂时,陆续发现了被覆盖的汤显祖家族墓园。
据江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徐长青介绍,汤显祖家族墓园共发现明清时期墓葬42座,其中明代墓葬40座,清代墓葬2座,出土了墓志铭6方,另外还发现明清时期的三处附属建筑遗迹。
墓葬大致可分为六排,布局基本清晰。
6方墓志铭行文、体例基本一致,主要包含人物生平、族谱关系、重要的家族活动以及人物评价等内容,具有巨大的历史考古价值。
其一,确认了墓主人的身份、名字、准确的生卒纪年及所属家族分支的脉络,是我们了解他们的生平和在家族谱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依据;
其二,根据酉塘公与祖母魏夫人墓志铭所书,尚质、尚贤二子均出自魏氏,纠正了《文昌汤氏宗谱》所记载的此二子分别为李氏与魏氏所生的谬误,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不足;
其三,铭文中所记生活中的许多细节,是分析当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珍贵资料;
其四,铭文中所蕴含的书法、美术、文学、文字等价值,特别是汤显祖亲自撰文或书写的墓志铭,势必受到相关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研究墓志铭可以明确6座墓主人身份分别为汤显祖高祖汤峻明(汤氏后人称子高公)、汤显祖高祖子高公夫人艾氏、汤显祖祖父汤懋昭(号酉塘,汤氏后人称乔一公)、汤显祖祖母魏夫人、汤显祖原配夫人吴夫人、汤显祖大弟少海公与其夫人潘氏。
在墓园发现刻有 “汤临川玉茗先生墓”、“玉茗公墓”的两块墓顶石盖板和刻有“口口口口口口義(羲?)仍汤公之墓”六字的半截墓碑,结合墓园所葬汤氏家族成员排列规律,初步确定4号墓为汤显祖与其傅氏夫人的双室合葬墓,据左为尊的古制,汤显祖位于4号墓左室。
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川人。是我国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江西抚州临川人,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出来的百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创作的以《牡丹亭》为代表“临川四梦”,是中国古代戏曲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世界戏剧艺术经典。
情的探险:从汤显祖到曹雪芹
————
文| 过常宝、郭英德
汤显祖的困惑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曾经写过一首《江中见月怀达公》的诗,道:
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
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
这首佛家偈语式的诗,表达了汤显祖内心中一种无法解脱的困惑:人们向往追求彻底的“无情”的境界,可是对滔滔汩汩之“情”却实在无可奈何。即使心中之“情”已经极为淡泊了,它果真可以完全消失殆尽吗?月中无影,水中无波,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正从“多情”解悟到“情尽”,不也同样是难以做到的吗?
达公即达观,是十六世纪一位著名的禅僧,汤显祖的好友。他在《皮孟鹿门子问答》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批评程朱理学,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观点,汤显祖称赞这是“一刀两断语”。[1]但是,汤显祖在悟透了“情”与“理”的两不相容以后,并没有斩断情根,彻底地皈依宗教,消极遁世,而是一直任凭现实情感在心中翻滚掀腾。所以他干脆沉浸于梦幻之中,在文学创作里对“情”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作一番寻幽探险,于是《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三部传奇戏曲名著相继问世。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特特地提出一个“情”字,它的表层意思是男女的自由爱情,但它的内涵却决非仅限于此。从杜丽娘的出场到读《诗经》,到游园惊梦,再到寻梦,这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过程,说明了所谓的“情”原来是一种自然人性(即“人欲”),它不受制于外在社会和道德理性,而是主体内部的独立存在。这与传统的人性观念是背道相驰的,因为人的本质历来被认为是受着道德意志的控制,先验存在的“天理”规定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人性自然也不能例外。而杜丽娘这种“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却完全游离于“天理”之外。
它的缘起有着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它把枯燥拘谨的人生引向一个至诚至真的审美境界:“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2]也就是说“情”本身就是目的,它值得人们执着追求,生死不渝。这样,“情”的力量就具有了超越性,亦即它本身也是手段。在《牡丹亭》中,“情”能使杜丽娘出生入死,还能使她起死回生,它毋宁是一种生命力量。“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于画形容传于后世而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3]“情”的这种献身和赎救功能,使我们想起超验的宗教。但它不同于宗教就在于,上帝独立于人寰之外,而“情”却是主体性的存在,是自我意识、抽象本体的具体化,汇集了全部生命力量。
显然,汤显祖之所以标榜“情”,是直接针对着“理”的束缚而来的。《牡丹亭》在确立了“情”的本体地位后,当然也不可能回避“情”与“理”之间惊心动魄的冲突。也许汤显祖并不希望冲突发生,也许他设法要弥合这种冲突。但冲突的实实在在的存在是既无法避免也不能弥合的。于是就有了《牡丹亭》中的梦境和非现实世界。这种梦境和非现实世界决不只是一种戏剧手段,它事实上至少具有三层含意:
首先,它意味着倍受压抑的人欲的觉醒,这种人欲由于具有很多理想特征,不能简单地等同西方心理学中的潜意识或情结,它具有哲学意味,是主体性的象征。
其次,梦境和非现实世界具有鲜明的虚幻性特征。虚幻性在《牡丹亭》中的突出显现,意味着“情”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认同感。它是一种自觉的避让,自觉地保持着一段距离,而这一种境界不属于清醒的理性思维,事实上它是属于审美活动的,它使得戏剧内容,也就是“情”逃避了普遍实用的价值判断,而作为一种强烈的感性体验得以保存。
再次,梦境和非现实世界的出现,是“情”和“理”严峻冲突的必然产物。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理学家的观点来看,世间万物无不体现着符合天理的道德伦理秩序,两性之爱自然也不例外,《关雎》就被称为人伦之始。所以中国正统理性就认为男女之间只有夫妇关系而没有爱情关系,没有两性的自然相悦,这就以伦理观念取消了人性观念。而杜丽娘“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自然是远离名教之外的,那么,它就把整个传统思想和社会习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准确地说,杜丽娘面对的不仅是杜宝、甄夫人、陈最良等封建纲常势力,更有她自己内心与生俱来的伦理意识,所以说,“情”的真正对头正是那无影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理”。与之相比,“情”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但“情”一旦觉醒,就不会轻易退去,它对已经觉醒了的生命负有责任,它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却对个体生命极端重要。于是,“情”只能潜入梦中,潜入阴间,在这些世俗伦理鞭长莫及的地方,顽强而又充沛地表现自己。
就是这样,汤显祖以卓越的梦境和阴间的艺术构思,深化了情理冲突的主题。他认为:“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4]“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灭情。”[5]《牡丹亭》正是以其杰出的艺术感受把情理冲突推至极点,深刻地披示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意识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排斥。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牡丹亭》把“情”作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巨大生命动力,由此而提出“情”和“理”何者更有价值的质问。这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实在不啻是一场春雷。
按照情理冲突的逻辑发展,《牡丹亭》的结局必然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因为“情”作为一种个体力量,与作为社会力量和传统力量的“理”相较,无疑是强弱悬殊的,两者的冲突必然是“情”的毁灭,它不可能在社会上得到现实的认可。但是,“情”的毁灭,对于杜丽娘生生死死的精神追求,对于汤显祖孜孜矻矻的理想企望,未免太残酷了。于是汤显祖不甚情愿地安排了《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让杜丽娘重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奉旨完婚”等封建伦理所规定的老路,以便使“情”得到社会的确认。这一让步事实上是一种自我否定,汤显祖无可奈何地用“鬼可虚情,人须实理”的两分法来调和本来不可调和的情理冲突。
汤显祖毕竟是一个士人,士人的社会价值就在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所以他不能容忍“情”仅仅处在社会生活之外,在梦中和非现实世界中漂荡。“情”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和现存社会政治合流呢?这一念之动,显然低估了或干脆无视了情理冲突的现实基础,但对汤显祖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把“情”投入社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情”的作用,并借此巩固“情”的地位,使之真正足以超越“理”、取代“理”,这是多么诱人的精神探险啊!
《南柯记》和《邯郸记》就是汤显祖进行这一精神探险的产物。在这两部剧作里,“情”已不仅是单纯的儿女之情,它还包括了人对社会价值和对物欲的不懈追求。一般来说,社会个体正是靠这两者来显示自己的价值的。淳于棼也好,卢生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在这纷纷世事中小有所成,首先必须经历一个从“无情而之有情”的过程,它以儿女之情的遂心如意为表征。汤显祖非常强调这一过程,就是为了表示“情”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可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而存在,这是后二梦式的精神探险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
淳于棼在剧情开始时,处于“无情”状态,混混沌沌,终日以酒为事。一切的变化都起于和“情”的偶然遭遇。《情著》一节写淳于棼“痴情妄起”,契玄禅师几番点他不醒,显示了他对“情”的执着品质,正是这一品质才能符合汤显祖的理想。他与瑶芳成婚以后,“情”使他的主观力量得以激发,忠孝都得到强烈的表现,尤其是他任南柯太守期间,竭尽心力,把一个偏远的边疆治成太平盛世。《风谣》、《卧辙》两折是淳于棼事业的顶峰。到此为止,“情”和社会政治似乎结合得非常完美,淳于棼充沛的个体情性和外在事功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这种结合终究抵挡不住物欲的侵袭和社会政治的污染,淳于棼因功被擢升为左丞相后,“君王国母爱宠转深,入殿穿宫,无所不听,以此权门贵戚,无不趋迎,乐以忘忧,夜而继日”;甚至发展到与国嫂、郡主、皇姑淫乱无度的地步。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封建朝廷、封建政治制度的腐朽本质,对人的主观个性有着极大的腐蚀作用。个体的“情”在现实的“理”面前是无比脆弱的,人们一旦涉足社会政治生活,往往不由自主地失去对“情”的把握,而走到“溺情”的地步。“溺情”实际上是“情”的世俗化过程,它通过对“欲”的无休止追求,而违背并毁灭了作为本体力量的“情”。所以无论是“不及情之人”,还是“溺情之人”,[6]都是和汤显祖的初衷相违的。
《邯郸记》也表现了大致相似的主题,但明显的变化是,卢生头上的光芒远比淳于棼更为暗淡,他不可能再创造出南柯式的理想政绩。他自一踏上社会政治的道路时,就走上了“溺情”的轨道。另一方面,他对“情”的态度也不似淳于棼开始时那样真挚。或者是汤显祖已经对南柯事业产生了怀疑,至少,到此为止,他确实感觉到一旦把“情”和现实政治结合,就意味着“情”走向“溺情”,就会产生出荒诞的怪胎。这无疑是正确的,更贴近了“情”的逻辑。
“情”和社会现实不能共存时,应该怎么办?传统中最明快的选择是求佛问题,那就是把“情”连同社会现实一块儿埋葬。后二梦的结尾似乎就是这样。但汤显祖真的同时拒绝了“情”和社会吗?不。汤显祖的求佛问题是专为社会现实而准备的,至于在佛道和“情”之间,他选择的是“情”,他曾经有信寄达观说:“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7]佛道排斥了个体主观情性,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残酷的现实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情”,对社会的厌弃逼迫他把佛道引为同道,但他认为“以‘二梦’破梦,梦竟得破耶?儿女之梦难除”。[8]他对杜丽娘式理想之“情”仍始终不能忘怀。他之所以让淳于棼、卢生最终求佛问道,那是因为佛道比现实社会更好。《邯郸记·合仙》中众仙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你怎么止弄精魂?便做的痴人说梦两难分,毕竟是游仙梦稳。”成佛升天充其量也只是梦罢了,但游仙至少还可以保持自己的部分真情,不至于完全地堕落。可见汤显祖的求佛问道并非是“情”的枯灭死寂,它仍然是一种对抗现实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是梦醒了以后不得已之举,是无路可走而又不得不走的悲哀。有一句诗道是:“厌逢人也懒生天”,[9]正是他迷茫无措的心态的写照。
曹雪芹的辛酸
如果说汤显祖的意义在于认识到“情”的价值以及情理冲突的必然,那么,把“情”发挥到极致,并且毫不后悔地沉湎于无望和痛苦的“情”的探险之中的,便是曹雪芹了。
脂砚斋在评论《红楼梦》时引用了汤显祖那首“无情无尽”的诗,这决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汤显祖的衷情和迷茫再一次被曹雪芹所体验、所重复。但曹雪芹并没有对汤显祖亦步亦趋,他无视强大的现实社会势力,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情”的洪流之中,又把“情”的探险推进了一步。也许脂砚斋正是有见于此,写下了另一首诗:“世上无情空大地,人间少爱景何穷。其中世界其中了,含笑同归造化功。”[10]明明知道“有情原比无情苦”,但却仍然认定“世上无情空大地”,只有情才能拯救这个苍白冷漠的世界。明明知道“有情原比无情苦”但却仍然选择“其中世界其中了”,在这实实在在的人生中把握住“情”,沉迷于“情”,在“含笑同归造化功”的最终解脱之中,我们是不难体会到曹雪芹沉郁悲凉的情怀和执着不懈的精神。其实,曹雪芹何曾“含笑”?他的不朽名著《红楼梦》恰恰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情”的“了”与“未了”之间,曹雪芹又为汤显祖的困恼注入了新的辛酸。
在曹雪芹和汤显祖之间,我们能找到很多相似之处。这首先表现在虚幻化上,他们的文学创作都非常谨慎地和现实世界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但远离现实的目的不是为了否认人生,而是为了逃避现实的价值尺度——所谓“理”。他们所用的虚幻手段也一样:弥漫于作品之中的梦境和佛道意象。
曹雪芹把《红楼梦》看作是一场大梦,这与《南柯梦》、《邯郸梦》是同一旨趣,但在《红楼梦》里,我们发现梦的范围被大大地扩展了。那远离人寰的石头寓言和还泪神话,难分难解的太虚幻境和大观园,还有书中大大小小的数十个梦境,它们都是一层层半明半暗的纱障,阻断着现实世界的价值关怀。不过曹雪芹没有再一次重复后二梦式的实验:企望把“情”和“理”作某些方面的融合。曹雪芹对“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他的“情”是无比纯洁的,因而也是无比脆弱的,它不能片刻脱离那片温馨的梦境,他知道,它一旦脚落实地,就会夭折在浊世之中。这一点正是为汤显祖所证明而又不甘心承认的。而曹雪芹却毫不怀疑这一点,并一直小心翼翼地在现实和虚无之间踩着钢丝,在“了”与“未了”之间培育着果实。
佛道意象也是《红楼梦》中经常出现的,但它的功能却明显比后二梦有了缩小,它并不暗示着“情”的归宿,虽然它是一种可能的归宿一直在威胁着曹雪芹的探险。在《红楼梦》中,佛道由于成为“情”的辅助性意象而赋予了一些积极的意义。我们试看书中的“太虚幻境”,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它应是道家的圣地,但它却“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望之伤情,闻之动心。它首先是作为还泪故事的缘起而存在的,也就是“情”的始源,同时,这里到处弥漫着的悲剧气氛,暗示着情缘的不幸命运。这一切都和清静无为的道教大异其趣。其实,太虚幻境就是大观园,人间天上,二而合一。太虚幻境的作用仅限于它的象征意义。再看那贯穿全书的一僧一道,无故携石下凡,惹起一场风月悲剧,不过是穿针引线,而空空道人读了《石头记》后,竟“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这一改变实是一个大关键,道家在斩断了情缘以后,才能悟空,但曹雪芹并不把道家的“空”当成终极真理,他认为任何终极的东西都不能不包括“情”,道家的“空”因为不受世俗“理”的缠绕,倒是接受“情”的好条件,也才能真正从道德伦理之外去理解“情”,但只有包含着“情”的“空”,才是真正的人的本性。而“色”不过是接受“情”的一个最好手段,是中介。所以空空道人的改名“情僧”,也是曹雪芹的自我写照,并无佛道意趣。
那么,《红楼梦》中的“情”到底有着怎样的内涵呢?曹雪芹借警幻仙姑之口把贾宝玉推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这里的“淫”即是“意淫”。“意淫”是作为“皮肤滥淫”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它摒弃了“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世俗欲望,因之和人的动物性本能有所区分。但“意淫”又不因此而投向社会道德理性的怀抱,落入“好色不淫”、“情而不淫”的窠臼。警幻特特地喝出“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断语,就是说不必强将“情”和肉欲分开。实事上,在曹雪芹看来,“色”是体验“情”的不可或缺的途径,这里也有反传统伦理道德的意味在。而且警幻更强调“意”字,也就是强调“情”的本体性意义。由此看来,所谓“意淫”,就是以人的自然情欲为内容,却本有人的主体意志,它不依赖外在世界,是“天分中生成”的,它的特征正是作为和世俗道德理性相对的人的主体性特征而出现的。贾宝玉的“意淫”和杜丽娘的“情”旨趣相同,其着眼点都在于人的主体性的论证和高扬。但曹雪芹的目标似乎更加明确而清晰。
在曹雪芹看来,“意淫”之说应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它首先是对封建理学的离经叛道,具有对抗“理”的功能;同时,它的本质上也和佛道观念格格不入。贾宝玉之所以为贾政所不容,不外于“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不在经济仕途上用功,也就是不守封建之“理”。但贾宝玉的这层“痴玩”并不是一味放纵,而是以对外在世界的批判为前提的。他指责儒家经典为“一派酸语”,对儒家“文死谏,武死战”的立命信条大加非难。同样,他曾迷惑于但却最终抛弃了佛道观念,他悟到:若归于老庄,则难免要“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这是决不能接受的;苦心参禅的结果,却只能是“自寻苦恼”。由此看来,传统的价值取向,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好,都不是“意淫”之说所能接受的。那么排除了这些现实的和空幻的世界,“意淫”之说得以安身的乐土在哪里呢?在大观园,在“女儿”的世界。虽然大观园和现实及佛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稍一不慎就可倾向其中之一,宝钗和惜春的人生抉择就可作为代表。但是,大观园毕竟是一块干净而充满生机的乐土。其干净,就在于它少受外界的干扰;其充满生机,就在于满园的“女儿”们。秉赋了“意淫”的贾宝玉在大观园找到了逍遥自在的活动天地,也找到了逃避现实的憩栖之所。所以警幻仙姑说:“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对“女儿”的钟情实在是宝玉的先天异秉,他甚至把“女儿”的温情作为自身生死系之的生命之源。他曾这样提出自己的归宿:“比如我此时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在《红楼梦》里,“女儿”本身就是“情”的另一种提法。它首先排斥了男子:“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男子浊臭,就在于他或者奔兢于经济仕途,或者沉湎于酒色财气,能象贾宝玉那样保持着“意淫”本性,成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的,实在是太少了。其次,“女儿”还排斥了已婚妇女,因为她们“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已婚妇女经过社会道德的洗礼和泼染,原有的女儿本性就异化了,就与男子同流合污了。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在《红楼梦》中,“女儿”决不仅止是一个社会群体,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象征,或者就是自然本性自身。这种充满温情的自然人性,与儒家的“德性”、禅家的“佛性”、道家的“真性”迥然而异,分庭抗礼,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的人性价值。正是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女儿”即是“意淫”的表现形态,“意淫”则是“女儿”的内在意蕴,它们都统一于“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统一于人的自然本性。也许正是因为“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所以曹雪芹才借助于大观园的女儿世界,使之形象化、具体化吧?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决不至于把大观园的意义仅仅局限于爱情上面,它实在是蕴含着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对自我本体的肯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贾宝玉一再说:“女儿”二字,“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
相对于汤显祖而言,曹雪芹似乎更是个纯粹的“诗人”,更偏重感性,他的感性也确实表现得更为丰富和细腻,甚至连他对“意淫”的理论阐释也充满了感性色彩。在《红楼梦》第二回里,他借助贾雨村之口,提出了“正邪两赋”的人性理论。这一理论根源于传统的性善恶观念,汤显祖曾在这一点上与传统妥协,把“情”分成善恶两种,说:“性无善恶,情有之”(《复甘义麓》),导致了“情”的真正意义的逐渐模糊和最终丧失。曹雪芹并没有重蹈汤显祖的故辙,他认为“情痴情种”是秉赋了天地之正邪两“气”而生的,“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通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可见,“情”是天生秉赋的,具有原初性、本体性;而且“情”由于同时领有了善恶两个相反的方向的价值评估,因此事实上取消了价值评估,超越了传统的性善恶观念。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逻辑论证,不如说是一种感性的形象表述。
但是,这样一来,曹雪芹在“情”的探险中便会比汤显祖更为成功吗?“情”在“了”与“未了”之间果真就能立住脚了吗?这是值得怀疑的。曹雪芹和汤显祖同样立足在一块肮脏的大地上,曹雪芹的探险也不能比汤显祖的享有更好的命运。《红楼梦》冷峻地展示了兴盛繁茂的大观园是如何变为枝凋叶残的。大观园被抄,晴雯抱屈而死,还有宝黛爱情的“空劳牵挂”:“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即便有如椽巨笔,也不能挽回这一难以接受的结局。《红楼梦》一开始的石头寓言就耐人寻味,赋于一块石头以满腔的温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绝望的希望,一个满怀希望的绝望。石头错过了补天的机会就是失去了原初的意义,如果它再一次被人世间的温情所抛弃,就是连存在的意义也破灭了。后者比前者更使人不能容忍,更令人恐惧。曹雪芹一开始就是冒着这样的风险来为人间“补情”的,那充满悲剧情调的太虚幻境,那“一把辛酸泪”的沉痛自白,无不显示了曹雪芹的心态。
赋予“情”以怎样的结局?是让它随倾翻的大厦一起灰灭烟尽?是让它攀上封建理教的破船,做着《牡丹亭》式的美梦?还是让它象后二梦一样皈依佛道,遁入空门?大观园是被颠覆了,“情”再也没有托身之处了。大观园的荣衰是与贾府相伴的,这一点就显示了大观园赖以存在的土壤是极不坚实的,它的破灭是必然的。可是让“情”也一起破灭吗?曹雪芹决不愿意这样做。
宝玉的结局恐怕是曹雪芹创作中的最大困惑。宝玉的原型是石头,温情决不能把它融化,它迟早要回到大荒山无稽崖下,一任风吹雨打。按照逻辑的发展,甄士隐的结局实际上就隐喻了宝玉的结局。甄士隐在一腔温情撞得粉碎之后,在“了”和“好”之间划上了等号,弃世而去,在他看来,那些脉脉温情不但给人生带来了许多烦恼,成为人生的包袱,而且它终究是不会在这个贫瘠的世界上生根开花的,只有斩断情根,才能逃避迷惘。但在曹雪芹看来,甄士隐以“适意”为目标的温情,在创造性等积极的生命意义上,与贾宝玉的“意淫”境界高下悬殊。《红楼梦》以是否能踏进太虚幻境来分别甄贾的高下,是极有意义的。有此一别,曹雪芹就不能容忍贾宝玉再踏上那条空寂的道路,虽然它也许是贾宝玉唯一可行的道路。走向这样的绝境,正是汤显祖无路可走,而不得不走的悲哀。可是只要一踏上那条绝境,曹雪芹用一生心血建立起来的“情”这个意义世界将付之东流,一个诗人是不能允许意义的消失,况且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荒诞,人被琐碎的礼教勒紧了脖子,那一片温情就是一片绿洲,是他唯一的希望,他怎么能亲手把它埋葬呢?但这一片温情是正在消失的海市蜃楼,一个人能够把它挽留住吗?不能。这是不可得之“情”,而又是非得不可之“情”;是不可忘之“情”,而又非忘不可之“情”。一个文学家要有多大的心理力量才能承受得起这样的压力呢?
曹雪芹弃绝了汤显祖的选择,也拒绝了现实,在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后,终于没有确定下《红楼梦》的结尾,曹雪芹辛酸的痴情注定了《红楼梦》不可能有完美的结尾流传于世。也许结尾曾有过,甚至有过不止一种,但无论怎样的结尾都无法表达曹雪芹对“情”的真切的、深刻的而又辛酸的感受。现存的八十回手抄本《石头记》应该有一层少为人知的意义:它使人们去追寻、体会和理解,对于曹雪芹,清醒和绝望是怎样相互支持又相互否定的;在它们强烈的纠缠之间,曹雪芹的那一份执着的痴情又是何等的顽强!百年以下,曹雪芹那一捧辛酸的泪水不还在我们的心间流淌吗?
非有志者不能至
汤显祖与曹雪芹毕生所作的对“情”的探险,实际上是力图探索一种崭新的人性观念、人性理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观、人性论,一般是论性而不论情的,因为在传统的理论中,性才是人的本体,而情只是性的表现。但是,由于在程朱理学那里,性实在讲得太多太滥了,要创立一种崭新的人性观、人性论,与其纠缠于性的界说、性的内涵的论辩,还不如选择更富于感性色彩,同时也更富于叛逆色彩的情,来作为理论的核心。汤显祖和曹雪芹就是这么做的。
那么,汤显祖和曹雪芹所说的情,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情在传统理论中大致有两种意谓:一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惧之情,如《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一是把欲也算作一种情,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七情。汤显祖和曹雪芹恐怕更倾向于后者,所以汤显祖要区分“真情”与“矫情”,曹雪芹则干脆称贾宝玉为“意淫”。从另一方面来看,传统理论中所说的性,最少有三种不同的意谓,即“生而自然”之性,人之所以为人者之性,和“极本穷原之性”。汤显祖和曹雪芹所说的情,大要是指“生而自然”之性的,如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曹雪芹说:“……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因此,相对于程朱理学分别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主张,汤显祖和曹雪芹大体上是持性一元论的,即认为情就是性,就是人的全部本性,是人的全部生命所系,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坚决反对以理制性,以理节情或者以理取代情,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一种外在的道德理性观念的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也不可能约束、取代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情的。
所以汤显祖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将包含着欲的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加以肯定和倡导,并与作为外在道德理性观念的理相对立、相抗衡,从而寻求一种对人性的更深刻、更圆满的解释,这就是汤显祖和曹雪芹对“情”的探险的主要回答。
汤显祖和曹雪芹对“情”的探险,在明清时期并不是空谷足音,而是一股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王艮讲“爱”;颜山农认为“……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11]何心隐主张“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12]李贽倡导“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13]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4]陈乾初提出“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15]唐甄说:“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舍欲求道,势必不能”;[16]颜元认为“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17]戴震强调:“好货好色,欲也,与百姓同之即理也”[18]……。这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高度肯定,对束缚人性的伦理纲常桎梏的蔑弃和批判,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从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的推进。尽管这一推进是极其缓慢、极其滞重的,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微小的,但这一推进本身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历史意义和无可比拟的文化意义。
汤显祖和曹雪芹正是这股时代潮流中矫健的弄潮儿。作为文学家,他们的生活感受和审美感受是如此的丰富又如此的细腻,使他们超越了思想家、哲学家的理论樊篱,把情的探险深入到一个更为“奇伟、瑰怪、非常”的境地。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也,其孰能讥之乎?”汤显祖和曹雪芹正是这样的有志之士,他们在对情的探险中,“不随以止”,“不随以怠”,汲汲不懈,孜孜不倦,留下了深刻而清晰的脚印,因而展示了前人和时人所未尝展示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虽然由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他们尽其毕生尚未能构筑一个崭新的人性观念和人性理论,但是他们已经尽志尽力了,他们可以无悔了,我们又怎能苛责他们呢?何况,他们以他们的文学杰作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疑问,这本身就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思想、精神领域中,一个疑问甚至比一个结论更有价值、更可珍贵。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然,汤显祖和曹雪芹在情的探险中的困惑、辛酸与失败,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首先,在理论上,我们提出“情”的概念的目的,主要是由于对传统的人性观,尤其是对程朱理学的人性观的不满,因而其斗争性虽强,但建设性不够,而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未曾为他们提供建设新观念、新理论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再加上传统知识分子“述而不作”的传统思想方式的影响,他们缺少在抽象理论上刨根问底的兴趣,而这通常对一个新理论的建立是必要的,新理论的建立不能没有一整套精密完整的演绎程序。因此,汤显祖和曹雪芹对情的探险,主要呈现为一种形象的、审美的文学艺术形态,而未能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这一探索的理论表述往往十分模糊,十分幼稚,甚至矛盾重重,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境地。
其次,不愿对社会现实作彻底的否定,不愿把“情”的观念在理论上推至极端,这大概与传统的中庸思想有关。他们一旦提出“情”的主导观念,立刻又对“情”的绝对价值产生了动摇,企望在某种程度上将情和理、情和无情揉和起来。比如汤显祖曾使“情”让位于儒家所说的“性”,所谓“性乎天机,情乎物际”,“性无善恶,情有之”,使“情”在正反两极中摇摆,立足不稳,则难免被“理”抓住空子,使它为“名教”服务。曹雪芹则更多地沉溺于情与无情,了与未了的矛盾心态中,难以自拔。再次,无论是汤显祖还是曹雪芹,他们在内心深处,都对自己的“士”的身份确定无疑,他们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启发、教育和改造的责任,这是每一个传统知识分子都不愿放弃的立命的原则。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解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尤其是在社会责任感还附属于“教化”传统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就不能不约束了他们对“情”的探索的脚步。
汤显祖在肯定“情”的同时,在理论上并没有弃绝“理”,他在内心中不希望它们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南柯梦》中的《风谣》、《卧辙》两折,汤显祖把王道理想和个体性情揉合在一起,就是这一心态的表现,如果把这一情景当作最高社会理想,就必然要对“情”产生动摇情绪,又怎么能把它坚持到底呢?
同样,在石头神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曹雪芹对“无才可去补苍天”是耿耿于怀的。当然曹雪芹并没有肯定“补天”应该用儒教的方式去进行,相反对之却有不少讥刺,但是曹雪芹的济世理想显然一直在掣肘着“情”。曹雪芹对“情”的探险的目的,决不仅止于自我满足,还负有改造世界的义务。但大观园里的“情”自顾不暇,尚能改造世界吗?如果不能,自我满足对一个封建文人来说,它的意义是不完满的,甚至是值得怀疑的。这样,“情”在贾府中,在曹雪芹心中经过了双重陨落,不然它不会有如此的悲壮色彩。
注释:
[1]《寄达观》。
[2]《牡丹亭·寻梦》。
[3][4]《牡丹亭题词》。
[5]转引自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序》。
[6]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中《明人传奇》。
[7]《汤显祖集》卷四十五。
[8]《答孙俟居》。
[9]《达公来,自从姑过西山》。
[10]见戚序本批注。
[11]《明儒学案》卷三二。
[12]《何心隐集》卷二《寡欲》。
[13]《焚书》卷三《童心说》。
[14]《袁宏道》卷十一《序小修诗》。
[15]《陈确集》下册第四六八页。
[16]《潜书·性功篇》。
[17]《存人编》卷一。
[18]《孟子字义疏证》。
本文选自《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七年第一辑
《牡丹亭·游园惊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