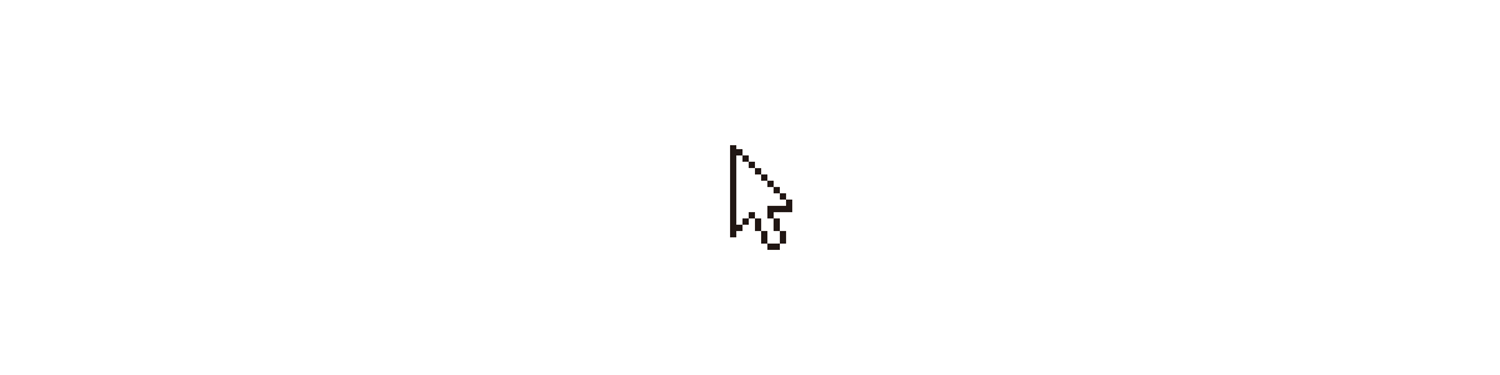老马的人生哲学
14级新闻二班 法子瑶
老马今年四十有七,中等个儿,偏瘦,虽说已快步入知天命的年龄,但是因长着一张圆脸,加之脸上自带“腮红”效果,好像在高原上长大的人或多或少脸上都会有一点高原红,这也算是高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吧,反而显得整张脸上有着脱不了稚气。
老马全名叫马春兰,是家中三个孩子的长姐,我曾问过老马有没有产生过改一个名字的念头,毕竟这个名字在现在看来有点土气,老马不屑的看了我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表达她强烈的不满,才说到:“我们那个时代取我这个名字可是很时髦的,那时候女孩取名字无非是“凤,花,翠,兰,红”,男孩取名也无非就是“龙,杰,雄,英”这几个字罢了,那还像你们现在的孩子取个名字都还要查查字典的。再说了,我还真觉得我这个名字挺好,叫起来又顺口,寓意也好啊。”为此,我表示虽然无法欣赏,但是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打那个时代成长过来的老马同志的审美水平自然是和现在有些不一样的。
似乎是因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缘故,以我来看,总觉得老马同志有些“小家子气”,用一个好听点的词来说叫做“节省”,也算是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是要是用个不好听点的词来形容老马同志,那就叫做“抠儿”,但是老马丝毫“不以为耻”,反而以“抠”作为她人生的原则和信条。
老马是个小气人没错,所以老马对自己那简直是抠的没边了。翻翻老马的衣柜,整整齐齐排列着一衣柜的衣服,可是当你指着每一件衣服问问他们的使用年龄,却总会被老马的回答吓上那么一跳。“这件衣服是3年前,我在小商品百货买的,也就50块吧”,“哦那件啊,去年我在夜市处理的,就花了100吧”。“这件衣服可是5年前,我在地下商场淘的,才花了200块,你看我这身材保持得还是不错的吧,五年前的衣服到现在我还是能穿”,老马的眼睛亮晶晶的望着我,献宝似地说。看看老马的衣柜,你会发现老马衣服的来源都是很统一的,不用想基本上都是在西宁市的中低端小市场。当然老马的衣柜里也不是没有稍微昂贵一点的衣服,1500块,那件还是我高考结束后,决定去大学送我的老马,狠了狠心,咬了咬牙,跺了跺脚大手一挥才买的,可尽管如此那件衣服的年龄算算到现在也有三年了,而且老马也不常穿,买了个透明的塑料衣罩把那件衣服好好的放了起来,也算是“视若珍宝”了。
老马对自己那么抠不说,对别人也一样。从小时候起,老马同志就不许我剩饭,而且秉持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家里某顿饭有吃不完的菜,下一顿一定是剩饭剩菜大杂烩,我虽然一直提出抗议,可老马同志表示抗议无效,幸好老马同志做饭的手艺还算不错,就算是剩菜倒也不难吃,说实话还挺香。老马同志在平常的家庭采购上那才叫一个精明。她一般都去早市场买菜,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则菜便宜,二则吗就是图个新鲜。早市早市,就是趁个早字,一般西宁市的早市早上十点半差不多就收摊了,而我家离早市的距离却是很不乐观的。夏天陪着老马去早市买菜还好,也算是早起锻炼身体。可在西北的冬天,大早上的被老马同志从香甜的梦乡中拽起,还被她美其名曰为早起容易“减肥”,但实际上却是陪她去买菜的滋味可不好受。前往早市场的路上还好,无非就是冷了一点。可等到要回来时,手上拎着那么多的塑料袋,那才叫活受罪。买的菜一多,塑料袋就容易沉,拎着那么多袋子,不一会,整个手就被袋子给勒的紫红紫红的,每次提着袋子,看着老马疾步快走的背影,我总是忍不住内心腹诽“能不能不去早市买菜,又远不说,还累”,但是很明显老马从来没有关注到过我的内心戏。不过好在,老马深谙怀柔政策的绝学,也就是所谓的打一个巴掌再给一个枣的套路,每次拉着我去早市,总是会在早市场买很多我喜欢吃的东西,所以即使我再怎么不愿意早起,还是乖乖陪着老马去买菜,毕竟“枣子”还是挺可口的。
说到老马同志抠,就不得不说一说老马同志在省钱上最牛的一招了,那就是她的必杀绝学,杀价。老马杀价可是有一套,总结起来就是十字箴言,“对半来,在抬高,不行就走”,先把对方开的价杀到一半,看对方的反应,感觉不行就再加上个十几二十几块钱,再看对方的反应,如果还是不行,就装作要走的样子,不回头的大步向前,可实际上到这个时候,商家一般都已经心动,一般不等老马同志向前走上个两三步就会听到后面有声音在喊:哎,大姐,大姐,等一下,等一下。”一般这时候,就都已经谈妥了,老马和对方往往是默契一笑,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于是老马算是凭借着这手绝学,逛遍商场无敌手了。
虽然老马是挺抠,可实际上老马同志也不是没有大方的时候。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作为一名文科生,还是一名偏科的文科生,数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道永恒的难题,更可怕的是这道题还无解。高二下学期那年,眼看着自己整个模拟考成绩都被数学一门拖了后腿,可偏生又没法儿再使劲。老马看不过去了,于是斥了巨资,为我花钱补课,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老马到底花了多少钱,但是老马那年好像没怎么再买过新衣服。而且奇怪的是越上了年纪,老马同志就越觉得我应该打扮的精干一点,成熟一点,所以每次老马同志陪着我去逛街买衣服,总是拉着我往她心目中的精品店跑,每次看到老马给我挑的衣服,先不看喜不喜欢,每次翻过那个标签牌,看看那个价格,倒是能惹得我肉疼一会儿。老马总是这样,只要是我喜欢的,她认为我喜欢的,或者是她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每到这些时候,老马花钱从来不心疼。
老马同志活到现在,她坚信的至理名言也就一句“钱要花在刀刃上”。“其他地方怎么小气都可以,但到了关键时刻,一分钱就有一分钱的作用,平常省下的钱就是要花在刀刃上。”虽然,我和老马同志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在很多方面上都不甚契合,但是对老马的座右铭,我还是持赞同态度的。毕竟老马同志也要比我多吃二十来年的饭,多走二十来年的路。而从前对老马同志的诸多不理解,也终于从上大学开始自己的“理财生涯”后,我才发现了老马同志的智慧。从最初的月光族到后来还能向银行收取部分利息,自从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老马同志的方针,也确实令我获益良多啊。
哦对了,其实平常我从没叫过她老马,反正老妈也是谐音不是。
如果墙会说话
15级新闻1班 杨鑫滢
「人流连这一生多少幅四面墙/围着我这一生多少竞技场/流落这单位这道墙/何时又挂着结婚相/谁和谁这一生厮守於四面墙/维护我这一生安稳岁月长/同在这一扇窗/看山水漂亮/迎接日落陪我幻想」——林若宁
1.引子——失落的年
我上一次回老家,是六个月前的事了;而距离我上一次在这偏僻的闽北小村里过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半年多前的暑假,父母带着我频频回乡,只有一个缘由——高龄患病的奶奶,时日无多了。
2017年的春节,我们这一大家子都有些落寞。在村子里过年,没有什么娱乐可言。年三十的下午,堂哥从老家大厅供奉土地公的桌台的抽屉里寻摸出一张“福”字,我们两个小辈扫起了支付宝“五福”。扫出“敬业福”的那一刹那,我尖叫着跳了起来,余光同桌台右上角的两张遗照撞了个正着。
两张遗照,一张黑白,一张彩色。黑白的那一张,已经在大厅里挂了12年;而彩色的这一张,则是年三十的下午伯伯们张罗着挂上的。爷爷的黑白遗照已经有些泛黄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一张黑白画像;而奶奶的那一张则是簇新的,照片上的她,笑容可掬。
打小时起,我对遗像就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敬畏。少时胆怯,从不敢正视爷爷的遗照,偶尔抬头往照片处望望,只觉照片中的他正注视着我,目光并不敢过多地停留。偏生在老家尤溪县,有太多人家的大厅里都挂着先辈遗像。在遗像带来的战栗感的背后,藏着我对生命终结的深深的恐惧。
再从春节说开去,返城之后,我们这一大家子的日子也不算好过。正月十五才刚过完,去年小中风的外公就受寒着了凉。腿脚本就十分不便的他这一次更是止不住地跑肚拉稀。我们一家子到外公家的时候,外婆正一个人收拾着残局。她一边帮外公擦洗着下身,一边操着闽南话对母亲说:“你们再不来,我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母亲把沾满粪便的毛织拖鞋拿出了房间,嘟囔着“这个怎么洗,干脆扔掉算了。”话音还没落下,外婆就又捋起了袖子,拿着刷子,把拖鞋浸入水盆里刷刷洗洗起来。
外婆是典型的闽南女人——能干而泼辣。在外公去年中风之后,她一个人包揽了外公所有的生活起居。经历了几十年的磕磕绊绊,她的直脾气依然没改——她既会操着闽南话骂狠狠外公“莫清楚(即“不清楚”的意思),连自己的离休证都弄丢”、“这日子怎么过啊,我一个人又要给你外公洗衣服做饭,又要伺候他拉屎拉尿”;也会在每次我返回学校前走上二十分钟的路来捎给我一些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蜜饯和一些私房钱。
这才上了一年半的大学,我却已经实打实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物是人非事事休”。兰州和三明,辗转如斯路迢迢。一年多来,当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在接到父母告知长辈近况的电话时,心中总会翻涌起一阵阵无力感。那是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东南一处,西北一角,就连看上一眼,见上一面,搭上一把手都显得那样的遥不可及。
2.小村旧事——泥砖房,旧院墙
奶奶的手是纤细的,手臂上还常年挂着两个银镯。每当她晃晃悠悠走起路来,镯子间便会轻轻碰撞产生一连串清脆而短促的声响。在奶奶因红包而和小辈们推推搡搡时,在饭桌上她举起杯来庆祝阖家团圆的时,我曾无数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当然,如今是再也听不到了。
在城市出生的我打小对久居乡里的奶奶就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三五岁时第一次挨打,正是因为我顽劣地不愿意接一个奶奶打来的电话。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恍惚地明白原来骨肉亲情,并非咫尺天涯所能隔。
那年春节回家,小辈们都凑在奶奶的房间里,捣鼓着把屏幕上正冒出雪花的电视机调出几个台来。那一年,老家的砖房还很旧,原始的小木屋厕所离家五米远,简易搭设的电路直接地裸露在外墙。我走在二楼,脚踩着木地板发出吱呀声响。“家”并是一个特别能给人安全感的地方。
后来,三伯父靠经营瓷厂赚了点小钱,把自己的那一半房子重新翻修了一遍。整座老屋,呈现出半新半旧的吊诡感来。城市版图的急剧扩张也带动一家子人飞出老家的大笼子。“外面的钱总是比家里的钱好赚。”伯父们笃定地说。几乎所有亲戚都选择了“外地挣钱,市区买房”的办法,来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我眼看着伯父、姑姑、堂哥们签下一张张高额的房屋购买合同。每次坐在乔迁之喜的酒桌上,听着一叠声的“恭喜”,我都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像是被透支的惊喜。
奶奶的城市生活也就此开始。都说人老了脾气像小孩,奶奶的生活总是辗转。三伯父家住几天,姑姑家住几天。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见过她与母亲争执。一边是听不懂家乡话的母亲,一边是不会讲普通话的奶奶。我总觉得这样的“叫板”很滑稽。
再后来,我离家念大学,在电话中和奶奶寒暄的机会越来越少。与次同时,医院给奶奶的病下了一个不明不白的诊断。“听说是恶性肿瘤”母亲说。大家对医生轻率的诊断确有怀疑,但都选择了心照不宣的沉默。毕竟,奶奶真的已经垂垂老矣。相聚时偶有人感叹,“也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这么过年。”
今年春节前,我到大伯父家做客。十岁小侄女的床边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打照片,照片里奶奶很开心地笑着,照片中的光斑也好看得耀眼。我又想起母亲曾告诉我的——病重时,奶奶的神智已经不清了,她甚至赤裸着身体站在老家的房前。想来,竟是如此凄惶。
3.城市即景——新楼房,墙已黄
“我11岁没爸没妈,后来加入共产党,是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一切……”这是一家子人听过无数遍的外公的口头禅。彼时的外公,身体康健,尚能每天到家附近的公园转悠上两三圈,和其他老人们谈天说地下象棋,和外婆因为每天吃什么而拌上三五句嘴。外公脾气耿直且倔强。他甚少到儿女家做客、吃饭,喜欢做的事无非是戴着老花镜翻着我们眼中的“老黄历”——《毛主席语录》。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离休干部,惦记了大半辈子的“毛主席好”。客厅里的毛主席画像挂了十多年,早就落满了灰。孙子孙女们常觉得外公古板,我和表姐也惯于在出门瞎晃悠不巧碰见外公时迅速猫腰,一闪而过。
而我的外婆,是一个典型的闽南女人,能干且精明,勤俭且泼辣。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小学,我在外婆家吃了六年的午饭。外婆家的饭实在是不怎么好吃——现在想起当年的“酱油腌肉”、“白糖拌稀饭”,依然让人哑然失笑。彼时的外公外婆刚刚搬进新房,墙壁粉刷一新,木制的沙发桌椅都是簇新的。那时我常和表弟窝在阳台的一角,扯上几个塑料袋,捎上几个布娃娃,玩起过家家。我常在留下一摊残局之后,把“黑锅”甩给弟弟。外婆总会絮叨着帮忙收拾,却从不生气。
年轮转了又转,步入初高中后,外公对我们的日常叮嘱逐渐变成了“好好学习,要考上一个好大学,给你爸爸妈妈争气”,再加上雷打不动的“我11岁没爸没妈……”。我们把外公的叮咛戏称为“政治课”。舅舅和母亲对外公的“啰嗦”也是一脸的不以为意——“可以啦可以啦老头儿,我们都知道啦”。
高考没能考出一个好成绩。外公外婆娴熟地拿闽南人说惯了的“宿命论”来安慰我。那个夏天,外公一个人吭哧吭哧地走了三公里,一本正经地询问火车站的售票员“同志,兰州在哪里啊?远不远?那兰州大学好不好嘞?”临行前,他不停地说“在大学要学会做人,要放聪明一点;要好好学习,考研究生……”
可还没等我考上研究生,外公就遭遇了一场中风。从前喜聊天、爱散步的他如今最常做的事是坐在椅子上,等着外婆端来午饭和药。外公操着闽南语一字一顿地感叹“生了这个病,感觉整个人都没用了”。这个春节,我去探望风寒初愈的外公,他絮絮地同我说了些陈年旧事,便睡了过去。约是人老了以后便会如这般迟钝而缓慢。
我看着眼前睡着的外公,又想起那个下午,他在幼儿园门口张望着准备接我回家的情景。那是我记忆中他第一次接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向外公要了五角钱,买了一个黑米馒头,很甜很甜。
以上文章为我院“新春采风万里行”活动“春路漫语”系列入围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