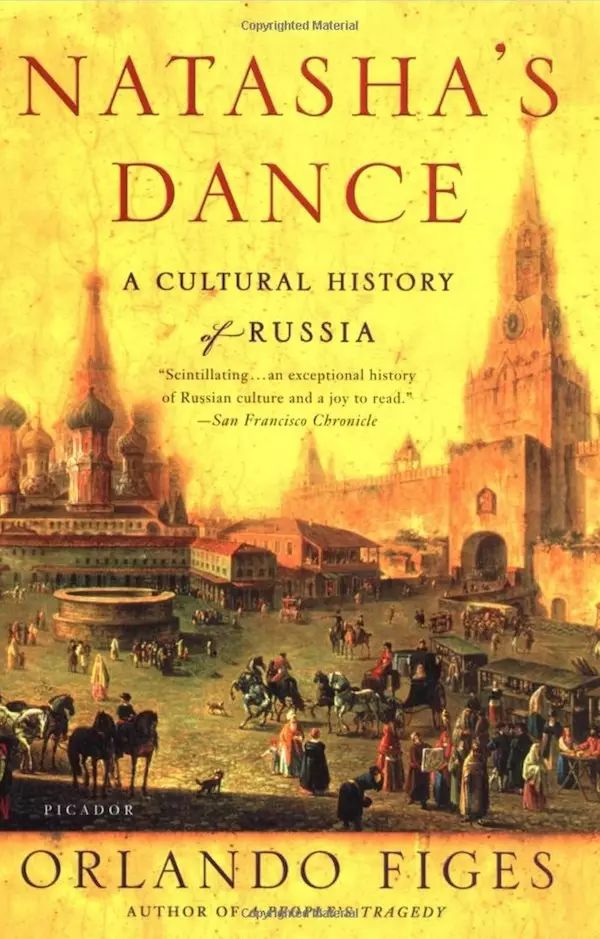
《娜塔莎之舞:俄国文化史》
文︱张建华
“娜塔莎之舞”:从两个俄罗斯到苏维埃文化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之所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其书名无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Whisperers(俄文Шепчущий)意为“窃窃私语的人”,语出自美国恐怖和奇幻小说作家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1930年完成的科幻小说《暗夜耳语》(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费吉斯的《寄给我你的问候: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书名来自俄国和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946年创作的著名诗篇《在梦里》(Во Сне)的英译版In Dream。而这本《娜塔莎之舞:俄国文化史》(Dance of Natasha)的书名同样典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经典片断。

《无名女郎》,克拉姆斯科依画。
“娜塔莎”(Natasha/ Наташа),一个清丽的俄国姑娘的名字,与另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卡秋莎”(katyusha/ Катюша)一样,是极为流行的俄国/苏联女性的名字,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和二十世纪的苏联文学中十分常见。“娜塔莎”是源自拉丁语的“娜塔利亚”(Natalia/Наталия)的爱称,意为“诞生”;“卡秋莎”是源自希腊语的“叶卡捷琳娜”(Catherine/ Екатерина)的爱称,意为“纯洁”。
《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是一个灵魂人物。她出身名门,深受欧洲古典贵族教育,在接受战争洗礼之后,逐渐成熟。她是托尔斯泰道德理想和“新人”的化身。费吉斯在《娜塔莎之舞》中解释说:“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彼得大帝
在彼得大帝以“野蛮”方式治理俄国的“野蛮”,试图强行将俄国这艘航船拖上“欧化”轨道之前,在俄国盛行的是“多神教+拜占庭+蒙古-鞑靼文化”。蒙古-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东方式统治与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未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二十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思潮即源于彼得大帝改革,或者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其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俄国基层组织村社的成员的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文明”俄罗斯是欧化的模式,是彼得大帝苦心打造的理想国,主要存在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它的文化形象是庄园、沙龙、大跳舞会、鼻烟、意大利歌剧,其通用语言是舶来品——法语或德语。
两个俄罗斯对抗的结果是,一个国家里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进而导致俄罗斯社会分裂的悲剧。因此,当含着金钥匙出生、在贵族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娜塔莎” 偶然在“农民大叔”的林中小屋里翩翩起舞,“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俄罗斯文化、身份认同的百年创伤一下子就撕开了。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里感叹:“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类似地,在《娜塔莎之舞》里费吉斯也指出:“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惯习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

十二月党人起义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日耳曼是男人的民族,俄罗斯只能是女人的民族。然而,更有学者称俄罗斯是一个性格刚烈的民族,尚武、善战、扩张是它藏在骨子里的东西。费吉斯用较大的篇幅描写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赞颂了十二月党人背后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妻子。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这些同样出身贵族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还专门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恼羞成怒的沙皇下令凡决定跟随丈夫流放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永世不得返回家乡,永久取消贵族身份与特权。1887年,有位记者找到十二月党人妻子中最后辞世的达夫多娃时,她仅轻声说:“诗人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历史的时钟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敲响,但“娜塔莎之舞”并没有止步,尽管这位旧时代的贵族小姐需要花大力气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新政权致力建立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产生了些许政治与时空的错位。

《布尔什维克》,库斯托季耶夫画。
与其称十月革命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如将其视为长时段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因为与旧制度的政治决裂往往形式剧烈而过程简捷,而与旧文化的决裂乃至新文化的建构,虽然波澜不惊,但背后却涡流暗结且过程复杂。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以贵族精英文化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又不同于泛滥于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全新文化,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人民委员会就建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列宁在晚年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上通用的民族概念。“苏维埃文化”是较短时间形成的、主观的动员型文化,而非长时期渐进形成的、客观的进化型文化,它是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以及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用而形成的。“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非仅限于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过,费吉斯也在本书中写道:“在塑造苏维埃新人的过程中,艺术家也起到核心的作用。是斯大林在1932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著名的短语,把艺术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塑造即是“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冷战时代和反共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费吉斯并没有否定“苏维埃文化”或者将其污名化,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史德与史识将“苏维埃文化”视为俄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其在文学、戏剧、建筑、音乐、电影等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娜塔莎们”在跨入新时代后经历的痛苦与欢乐。费吉斯将其称为“透过苏维埃梭镜看俄罗斯”。
俄国文化史的复兴:在二十世纪末
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叙史体例,曾是俄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帝俄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米留科夫(П. Н. Милюков,1859-1943)著有两卷本《俄国文化史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但在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权的“宏大革命叙事”的背景下,以革命情怀和大众文化为本质的新文化,取代了原来以精英意识和贵族文化为本质的旧文化:文化史在苏联史学体系下也渐渐式微,其地位被政治史和经济史取代。
1993年初,苏联解体尚未完全落幕之时,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毫不客气地将俄罗斯民族、国家和文化列为“顽劣”之列,从而使俄罗斯学术界连发余震,极大地提升了对“文化”、“文明”和“文明史观”的关注。亨廷顿于1995年应邀到俄罗斯学术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发表演讲和辩论。法国学者拉吕埃勒(Marlène Laruelle)评论道:“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们未必赞同亨廷顿提出的世界未来冲突论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即两极化之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文明论’的图解才能解释:西方文化区或曰‘大西洋主义’文化区与‘斯拉夫-东正教’空间相对峙,而‘穆斯林世界’将不得不在与西方或者俄罗斯结盟间做出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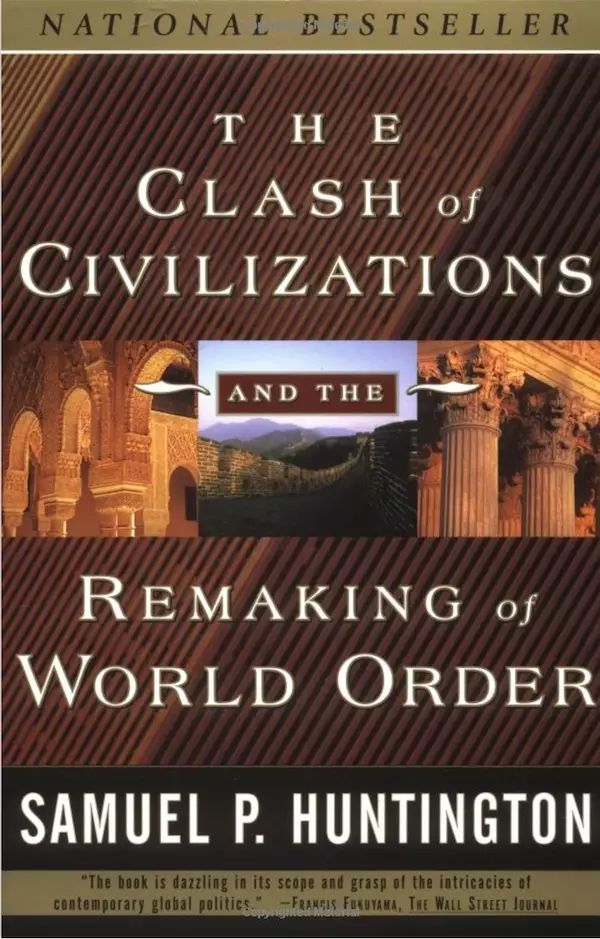
《文明的冲突》
在这样如此现实和紧迫的背景下,古老的文化史在俄罗斯复兴,并且还产生了一个新兴学科: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在史学研究领域,文化史成为当代俄罗斯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学里普遍地设立俄国文化史教研室,开设不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史课程。出版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与文明史的著作。研究领域涉及了许多全新的或从前较少涉及的内容,如贵族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农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别史、城市生活史等。此外,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纷纷设立文化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变身”为“文化学教研室”的突出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学术界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有重点和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欧美学者关于俄罗斯文化与俄国文化史的研究的同时,几乎奥兰多·费吉斯每部著作的出版后都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关注。
费吉斯的毁与誉:历史乎?文学乎?
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一个备受争议和特立独行的职业历史学家。
在费吉斯的个人主页(www.orlandofiges.com)上,罗列了他的全部著作及档案文献,供读者无偿或有偿阅读、使用。他的自我介绍栏目中写道:“奥兰多·费吉斯是伦敦大学伯贝克(Birkbeck)学院历史学教授,1959年生于伦敦。他以‘双星第一’(Double-Starred First)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1984年至1999年,任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历史学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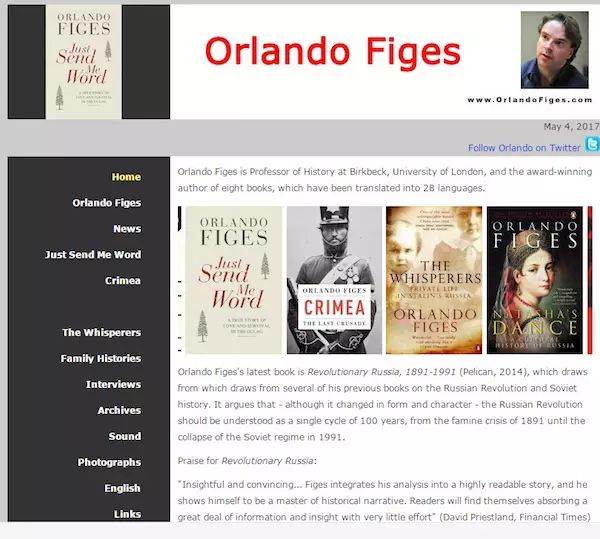
费吉斯的个人主页
在英国这个史学大国里,费吉斯虽然资历尚浅,但与史学前辈和同辈相比,他身上又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专业倾向和叙史风格。与绝大多数英国史学家不同,费吉斯的学术兴趣专注在俄国(苏联),并以俄国史和苏联史的研究为专守志业。而他的研究领域在时间断限上,横跨了俄罗斯帝国、苏联与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时期;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关注俄国(苏联)历史,同时兼及俄国(苏联)文化、文学、艺术、民族、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叙史方式上,他的历史著作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因而收获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和社会影响,但也因此而招致来自历史学界同行的批评和非议。

奥兰多·费吉斯
比如令他获得国际声誉的《耳语者》,虽然在欧美获得了众多奖项,但也引来了一片批评之声。美国老资格苏联问题专家、《布哈林政治传记》(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的作者斯蒂芬·F. 科恩(Stephen F. Cohen)认真地将书中引用的俄文原始档案与“纪念协会”的档案加以对照,认为《耳语者》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存在着“令人吃惊”的错误。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耳语者》的叙述过于文学化,内容方面过于追求情节化,许多文学化描写让专业读者对史实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无独有偶,《娜塔莎之舞》出版后同样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反响,但对该书的批评之声也随之响起。剑桥大学教授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除对书中征引资料的来源提出疑问之外,也对该书的写作风格提出了疑义:《娜塔莎之舞》究竟是史著还是小说?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另一位重量级的美国历史学家宾尼恩(T. J. Binyon)也对《娜塔莎之舞》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书中俯拾即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
于是,一个惊人的现象呼之欲出: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结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他几乎每本著作都获得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还收获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这正是由于它们的可读性和文学性。而来自欧美史学界同行的激烈批评和屡屡声讨,指责的也正是他著作的资料真实性和历史写作的文学性。
费吉斯的叙史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母亲——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埃娃·于尔根·费吉斯(Eva Unger Figes)的影响。埃娃的创作风格便是历史写实和非虚构化,她的第一部小说《界线》(Equinox)就是根据自己的犹太家族在纳粹德国时代在柏林的恐怖生活史,以及她本人随家族于1939年移居英国之后的个人情感史而创作的。她描写了一个从纳粹德国移居英国的犹太人马丁,在童年时代来到了伦敦,但直至成年后仍感觉自己与英国格格不入,继而,他与英国妻子、不得意的诗人和编辑伊丽莎白的夫妻生活也变得纷乱不堪,最后不得不开始漫长的离婚历程。

奥兰多·费吉斯
此外,费吉斯在大学读书,以及随后成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年代,恰好是由美国历史学家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起并主导的“语言与文化学转向”的时代。尽管从此国际史学的主阵地就由欧洲转向美国,但英国仍然以其老牌史学帝国之余勇,在冠之以新文化史、新思想史、新社会史的新史学领域分得一席重要之地。这种新的历史学潮流不可能不对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史学家费吉斯产生深刻的影响。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俄国文化本身的特质。自十九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娜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在一个多世纪里,培育了俄国文化的绚丽之花,也养育了俄国文化的特质——文学中心主义。
俄国曾是偏安于欧洲一隅的穷乡僻壤,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出世甚晚,但负有强烈的使命感——无论是批评家、史学家,抑或是小说家、诗人、艺术家皆是如此。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震撼下,沙皇政府强化了国家机器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导致进步人士自由表达思想和愿望的公共空间的丧失。于是,他们寓情于诗画,寄志于小说,以春秋笔法隐晦曲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通过“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奥勃洛莫夫性格”、“新人”、“旧人”、“美妇人”、“泼留希金”等一系列文学形象抨击时政,呼唤新时代。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幕戏剧,每一幅绘画,每一曲音乐的背后都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宗教和社会批评的元素,所有的新思想都是通过“文学”这个“中心枢纽”展现的。
专注于十九到二十世纪俄国文化史研究的费吉斯不能不受此“文学中心主义”的影响,因此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更多地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新思想史”主张的“语境”、“修辞”、“隐喻”和“反讽”,他的史著带有了传统史学中并不常见的“虚构”和“想象”等文学色彩。在这一点上,费吉斯不仅顺应了国际史学发展趋势,体现了俄国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特质,而且大大地强化了其史学著作的大众阅读性,完成了从专业史学向公共史学的转化。
在《战争与和平》里,贵族小姐娜塔莎在“农民大叔”的小木屋里,伴着大叔演奏的巴拉莱卡琴声和灰眼睛的阿尼西娅轻声唱起的民歌《在大街上》,突然忘记了身份,放下了矜持,“双手叉腰,动了动肩膀”,愉快地闻歌起舞了。在《娜塔莎之舞》中,“娜塔莎们”将在何种乐曲或民歌中翩翩起舞呢?我愿选择俄国最著名的一首民歌《卡林卡》(Калинка,又译《雪球花》):它历经帝俄——苏联——俄罗斯三个时代,而没有被历史和政治湮灭。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苏联东欧学会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