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斯泰尔·伦弗鲁
/
文
田延
/
译
巴赫金的主体在世界中遇到的不仅有“客体”,即他必须为之强加一种秩序和意义的物质现实,还有
其他主体
——即其他那些体验着自身独特而唯一的存在,并且是具体的、活生生而又只有暂时确定性的、负责任的人们。巴赫金后来会继续阐发抽象的科学思维(从物理学到经济学)和人文学科思维之间的区别,并使它成为某种更为根本的区别,甚至可以说,这种区别完全源自于同样要“发声”的人文(社会)科学对象的特性。这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把他所谓的“审美观察”和理论思维的各种例子归为一类,它们同样都不能理解作为事件的存在,尽管其原因彼此对立。为了克服这种无能,审美观察必须成为参与性思维的一种更特殊、更明确的形式,这次的参与,不仅仅是对它自身存在的在场的接受(它的责任),也是对除它以外的一切事物进行移情的特定方式。这是通过巴赫金所说的“审美观照”而被表现出来的,他提出这个东西,把它作为对不能理解存在事件的纯唯美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审美观照[……]的一个重要时刻是对观看的对象进行移情——即从它的内部,看它自身的本质。在这个移情的时刻之后,总是紧跟着客观化,即观照者把通过移情所理解的个体置于自身
之外
,与自身相分离,然后再
返回
自身。只有这个返回自身的意识,才能从自己的位置出发,赋予从外部理解的个体以形式,即以审美的方式为它赋形。
(
TPA 15
)
巴赫金非常明确地认为
移情可以实现某种东西,它既不存在于移情的对象中,也不存在于先于移情行为的我自身当中,通过这种被实现了的东西,作为存在的事件得到了丰富(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它本身的那个样子了)。
(
TPA 15
)
“纯粹的移情”——让自我消失在他者当中——并不能实现这种神奇的“丰富”;重要的是要前往个体性他者的那个位置上,然后
返回
自身。为了获得巴赫金所说的“整体”或“统一”,任何主体都需要另一个位于
外部的
主体;主体、个人、个体性只有通过一个巨大的悖论,只有在他人的凝视下才能变成他或她所是的样子。
在他下一部重要的(但也是不完整的)著作,即《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巴赫金重申并发展了这些关于存在和他者性的态度,特别是证实了他者在自我构成中的关键作用。主体
必须成为和他自己[
原文如此
]相关的他人,必须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观看自己。[……]在通过他人观看我们自己之后,我们总是再次通过生活返回我们自身,而最终的,或者可以说,可总结的事件就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范畴而发生在我们自身内部。
(
AH 15
,
17
)
他人相对于我有一种“超视”(
excess of seeing
),一种“盈余”(
surplus
)。他人从某个视角,或者某种背景中来观察我,而我在这种视角和背景下永远也看不到我自己:“我们尤其不能或不足以依靠我们自己来理解我们的个性的特定整体”(
AH 5
)。
通过采用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把我们已经讨论的所有方面都集中在了一起——巴赫金把他的自我—他者关系模式和意义与理解模式的连锁结构描述为:“对表现出来的行为的现实世界的[……]具体
建构
”(
TPA
,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下面这些话描述了这一具体建构的基本坐标,这个坐标通过一次移动,使巴赫金绝对明确地拒绝了封闭的个人主义:
现实生活和文化的一切价值,都是围绕着被表现出来的现实行为或行动世界中基本的建构点来配置的: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政治价值(包括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最终的宗教价值。一切时空价值和一切内容—涵义的价值都被引向并聚合在这些情感—意志的核心因素上:我、他人和他人眼中的我。
(
TPA 54
)
这个三合一组合中的头两项可以按照下面这样加以完善:“我”(无论何时他都不是“他人眼中的我”)被巴赫金描述为“我眼中的我”(
I
-
for
-
myself
),而“他人”则必须总是成为“我眼中的他人”(
the
-
other
-
for
-
me
)。巴赫金的模式之所以是“建构的”,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不是永不变化的点或实体;相反它是一种流动的模式和动态的关系,只能以现实的人类主体无法摆脱的确定性为根据,并居于这个确定性的核心——即居于他或她唯一的存在事件之中。一切意义和理解都不能消解这个模式;实际上,它是根据同样的建构原则而被构造起来的:它是自我—他者关系建构的一个效果,也完全依赖于这个建构。
通过对现实互动过程中活生生的、确定的主体的描绘,这种自我—他者关系模式实际的,而且几乎是继之而起的性质证明,它和抽象的、均质化的他者是不同的,这种他者已经开始支配各种后现代思想中关于他者性的大多数观念了。他者不仅仅是主体意识所理解的外部存在——它们以一系列对种族、社会及性别的普遍化为特征,更糟的是,它们令人费解地和主体的“无意识”连在一起:这些恰恰是那种“理论主义的”抽象,它们是通过设想一种与其明确的事件性相隔绝的行动或陈述而被制造出来的。巴赫金的他者总是我眼中的他者,它总是隐含着它在主体间彼此联系的事件中的交叠。这种对事件的建构在后来形成的对话主义这个首要概念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巴赫金的他者和那个在自我中被持续寻找并压制的东西毫无关系,正如伏罗希洛夫和/或巴赫金后来在1927年的《弗洛伊德主义》一书中将要辩称的那样,这个东西不过是把一个外部的、被抽象地建构起来的“幻影”重新迁移到内部的心理空间之中。尽管被一位著名的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鼓吹者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生于1941年)贬斥为“倒退的”,但《弗洛伊德主义》仍然是对弗洛伊德著作及影响的哲学基础所做的一次十分具有先见之明且十分大胆的驳斥,它通过强调其社会及历史涵义,充分论述了相互建构过程中的自我与他者这一核心概念。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弗洛伊德主义是19世纪中期以来,统治着“资产阶级”(伏罗希洛夫在通过一种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写作)哲学的那种“历史恐惧”(fear of history)的最重要的范例。对于伏罗希洛夫而言,“无意识”是一种虚构,是由“对历史
特有的
(sui generis)恐惧所驱动的一项发明,是把世界置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一种野心”(F 14)。实际上,对于
有意识
的思想来说,一切事物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流行的意识形态却要阻止它的对手寻找自己的外部表现形式;这就变成了一种“非官方”的意识,主体意识到,它存在于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紧张及斗争关系当中。作为压制欲望的一种方式而被建构起来的无意识仅仅是一种手段,主体以此而受邀——或者被强制着——去欺骗自己。它是一幅用抽象方式变幻出的面纱,从主体角度观之,它不仅从主体那里遮蔽了面对主体的他者的现实性,而且,通过不断加深主体在与他者互动过程中的自我构成所隐含的悲剧性,遮蔽了它自身状态的本质。意义产生于现实的唯一的存在事件并且以事件性的建构为条件——伏罗希洛夫后来把这明确地称为“社会的”。巴赫金只是呼吁“通过他人的眼睛”(AH 17)看我们自己,但对于伏罗希洛夫而言,他人——我通过他的眼睛才可能观看——是伴随着他或她自己的意识形态视野,作为“我的社会群体、我的阶级的一个代表”(F 87)——或者不是,这要视情况而定——而出现的。伏罗希洛夫也谈到了作为一种“交流事件”的事件,强调语言的作用,而语言最初在巴赫金的建构中是(几乎)缺失的。(这种关于语言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的概念会在第5章进一步阐述。)吊诡的是,或许正是语言的作用形成了雅克·拉康(1901—1981)著作中对弗洛伊德思想进行后结构主义革新的基础:然而对于伏罗希洛夫来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首先就拒斥语言,因为语言(话语)最终是社会的,而对拉康来说,无意识则是大他者(Other)的话语。
○●
文章选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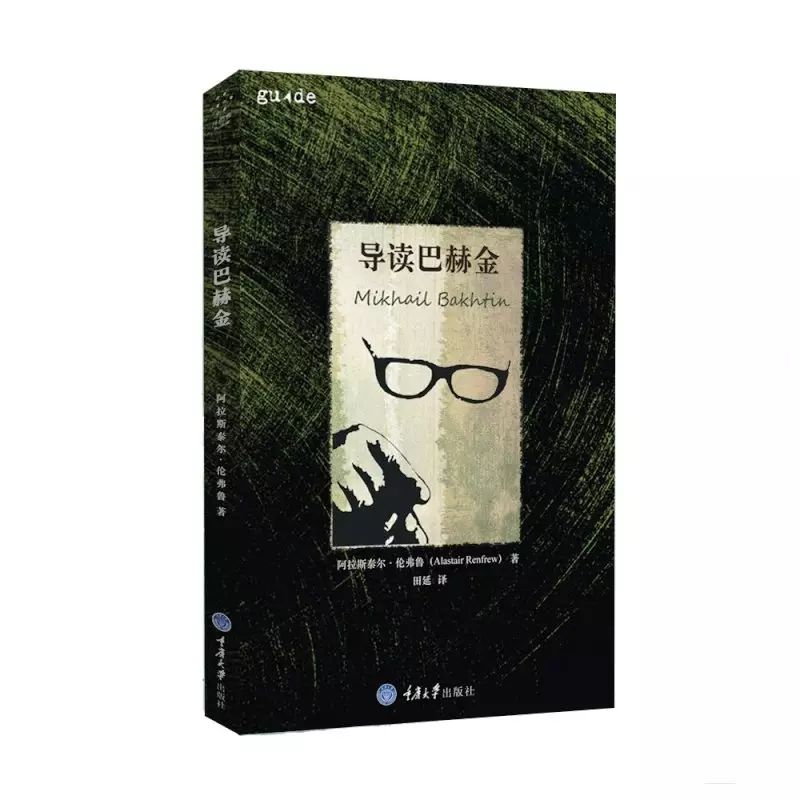
导读巴赫金
阿拉斯泰尔·伦弗鲁 |著
田延 |译

















